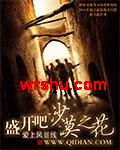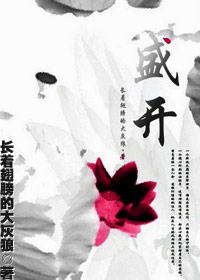隐秘盛开-第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平年代不做一个文学社团的领袖岂不是暴殄天物?
“红钟”敲响了,在这个尚还沉闷的、摸不着头脑、等待着什么的校园里,有点石破天惊。那份他们创刊的同名的油印刊物,在这学校上千名学子们的手中传来传去,还有人抄下那上面的文章。甚至,它不胫而走,传到了社会上,还有,李提摩太的学校。那学校里的许多学生都在谈论一个名字:回忆。人们互相询问说,回忆是谁?当然没有人知道他的来历,但是人们都在说,我们也有了一个卢新华,我们这城市,也有了一个卢新华。
现在,我们终于知道了,刊登在那上面、被人们传抄的文章,是什么了。那是一篇小说,伤痕小说,作者叫“回忆”,一望而知这是一个笔名,而且,是一个成心要让人家看出是笔名的笔名,小说的题目倒很朴实,《落日》,写一个下乡知青在插队的地方,亲眼目睹了一个富农的女儿,在受尽凌辱之后投井自杀的故事。他写人们是怎样以正义和真理的名义杀人。他还写那青年的矛盾和痛苦。那当然不会是一个很成熟和完美的作品,可是充满激情,而且,真诚——后来有人评价它,说那是灵魂的呐喊。总之,它感动了许多人,这个“回忆”,以他的惨烈激情搅动了这个沉闷的城市。
七七级和河边的学校(3)
那么,这个“回忆”是谁呢?“红钟社”的人当然人人都知道,可是他们秘而不宣。他们知道这不会是一个长久的秘密,可这个秘密在他们手中一天他们就有一种与众不同的亲密无间的快乐。无论别人怎样追问他们,他们总是口径一致地回答说,到时候就知道了。到什么时候呢?终于,这个时候到了,南方一家文学期刊在头条发表了这篇《落日》,还配了评论。这一次,正式发表的这一次,作者放弃了“回忆”这笔名,使用了真名实姓,刘思扬。
这已经是1979年的春天,“伤痕文学”的潮头就要过去了,那是刘思扬所不能挽回的。可是在潘红霞的城市,我们的城市,这个内陆的小城,它的发表还是引起了不小的波澜。人们惊愕、感动,甚至激动,当然也有人持完全相反的意见,认为它阴暗和灰色,有着方向性的问题。许多家媒体纷纷采访了作者本人,有保留地发表了采访记,本地广播电台在非黄金时间播送了这小说。现在,没有人不知道潘红霞的学校了,这新兴的学校,成了我们城市的话题。
还有什么快乐能比得上这样的快乐呢?这一天,潘红霞们,红钟社全体又在河边聚会了,他们总是喜欢在河边聚会。是啊,他们这样一群浪漫的青年怎么可能轻易放过河流这样的美景?他们翻过坝堰来到河滩,席地而坐,把报纸铺在草地上,上面放一些吃的东西:熏肠、肚片、酱肉、珍贵的五香花生米,当然还有啤酒。男生们用牙齿咬开啤酒瓶盖,对着酒瓶吹喇叭,女生们则毫不客气地用手拈肉吃。他们唱歌,念诗,念自己的,也念别人的,一会儿顾城一会儿北岛,念了一首又一首。他们还嚷嚷着让“回忆”宣读新作。可是,“回忆”没有新作出笼,却说,“等着我吧!”大家期待地望着他,他又说,“等着我吧!”原来他在朗诵,那是西蒙诺夫的诗歌,卫国战争时期的诗歌:“等着我吧——我会回来的,只是你要苦苦地等待,等到那愁煞人的阴雨,勾起你忧伤满怀,等到那大雪纷飞,等到那酷暑难捱,等到别人都不再把亲人盼望,可是你,你要等待——”他念完了,大家笑起来,说,“好吧,我们等着你,等着你成为文学巨匠。”有人举起酒瓶,对着河流,夸张地喊道,“亲爱的,你为我们作证。”这一下人们都举起了酒瓶,朝着河流放声大喊。只有一个人,没有喊叫,可是谁也没有注意这个人,这个小小的细节,在红钟社的历史上,可以忽略不计。
可是,只有这个人,在那一刻,在那个春光明媚的下午,听到了一个谶语。只有她听到了它。它如风一样掠过波光粼粼的河面,那谶语说,你要苦苦地等待啊。
那时,多少青年像投身革命一样投身文学,突然间,有一天,在与他们这城市相邻的一个更小的城市更小的大学里,一个学生,奇迹般地,成了万众瞩目的“文学新星”。他的光芒迅速掩盖了刘思扬的光芒,因为,他的那篇小说,发表在中国最重要的一张报纸上。那报纸,至少,拥有着几千万的读者。
在那所大学里,也有一个文学社团,那社团的名字非常严肃:五四。文学新星自然是属于“五四”的。
他们决定去和“五四”会师。“红钟”会师“五四”。于是,在一个早晨,他们骑着自行车,出发了。事先,也没有和人家联系,而那又是一个星期六的早晨。从他们的城市,到文学新星的大学,大约有九十华里的路程,他们十几辆自行车,浩浩荡荡,大呼小叫地上了国道。初夏的风,吹拂着他们,他们很快乐,一人一只军用水壶,斜挎在肩上,里面装着清水。他们还在书包里装了面包、馒头,是准备充饥用的。那是一个晴好的日子,天很蓝,白云很柔软,满眼都是绿意,庄稼长得肥头大耳,无论是贫贱的高粱还是玉米,还有树们,绿得也正新鲜,是北方最常见的杨柳还有在春天开白花的槐树。一路都是这样的景色,平凡,毫不出奇,可是生气勃勃。太阳越升越高,也越来越热,他们喊叫的声音弱了一些,速度也慢了下来,可心里仍然是快乐的。有人忽然高声唱起歌来,“横断山,路难行,天如火来水似银,天如火来水似银哪啊啊——”是耳熟能详的《长征组歌》。于是,他们齐声应和,“战士双脚走天下,四渡赤水出奇兵,乌江天险重飞渡,兵临贵阳逼昆明——”他们在平坦的公路上,一览无余毫无阻碍的公路上,唱着山路和水路的艰辛,为自己壮行。要说,他们这些人哪,哪一个是害怕长途跋涉的?哪一个人没有经历过走长路的锻炼?九十华里的坦途,还有自行车,说来是不在话下的。他们原计划在中午之前能够赶到目的地,可事实上,九十里路,他们竟然骑了六个多小时,在午后一点多钟才来到人家的校园,比原计划晚了一个半小时,这样,他们就和“五四”错过了。
这一个半小时的耽搁,都是因为一个人,这个人,我们先不去说她,只记住她叫“小玲珑”就是了。因为“小玲珑”,他们才晚到了这一个半小时,结果,他们就撞上了一个空校园。
这个学校,说来奇怪,它建在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离那座它冠名的小城,还有三十多里的路程。此刻,它陷落在就要起来的青纱帐中,一片静谧。它身后也有一条河,叫作潇河,这学校艺术系里的学生,就总是在潇河边写生,画它的蜿蜒、草滩和芦苇,或者,去那里挖雕塑用的胶泥。
七七级和河边的学校(4)
只有一条公路,一个汽车站,将这旷野中的学校和那座小城连接起来,城里开出的汽车,一天中,有几班从这里经过,其中一班就是中午十二点半左右。这学校,周六下午是没有课的,所以,这学校的学生们,在周六的中午,午饭前就纷纷离校了,或是赶那班汽车,或是骑自行车,或是随便搭一辆顺风车。等他们赶到时,晚了,这学校已是一座寂静的空巢。
当然,不会是杳无一人,不会是一座鬼城,总还会有一些不回家的人留守,可那有什么用呢?不会有一个他们期待的、热烈的、戏剧化的“会师”场面了。他们兴冲冲地,赶了九十里路,却扑了空。他们站在人家的校门外,有一点茫然和失落,还有一点点抱怨。他们又累又饿又渴,可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旷野,连个打尖的地方都没有。他们只好找了个树阴处坐下,沉默地,吃他们带来的面包和干馒头,喝着水壶里最后的一点清水。午后的太阳,晒得庄稼叶子蜷起来,静静地听,似乎,能听到咝咝的神秘的响声,那是水分在阳光下蒸发的声音,袅袅升腾,像万物的灵魂。他们吃得无精打采,可地上一群大蚂蚁却兴奋不已,呼男唤女地,忙着来搬运那些掉在地上的面包屑。潘红霞低着头,看着那些忙碌的渺小的生命,一只蚂蚁,坚韧地,磕磕绊绊地,挪动着远比它庞大的一块面包屑,它几乎是在拖着一座山脉爬行,身子一歪,翻倒了,向着天空祈祷一样拼命蹬腿挣扎,又翻过来,再爬。真是愚公移山哪。她看得出了神,心里慢慢慢慢涌上来说不出的感动。
其实,这一天,并不是一无所获的。这一天最终还是有了一个戏剧性的结尾。他们是谁呀?他们怎么会一筹莫展呢?他们最终还是把他——文学新星找到了。就在他们回去的路上,途经那座小城时,他们闯进了人家的家里。其实,他们只有他一个大概的地址,是从那学校留守人员那里打听来的,知道他住在那小城,一个很大的厂矿区。他们想,好了,就是海底捞针,我们也要把他捞出来。他们真把他捞出来了,从一个有着万余名职工,大得本身就像座小城一样的厂子里找到了他的家。那样的工厂,只有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在苏联专家的手里,才可能诞生,辽阔得简直奢侈。到处是树,建筑却朴素,结实笨重,在标志性的地方,比如,一座俱乐部的屋顶,往往有一颗克里姆林宫式的孤独的红星。
文学新星正在院子里和煤。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在文学新星的小城,甚至,在我们的省城,都还没有煤气。我们还在用最古老的方法:生火做饭。在我们这个盛产煤炭的地方,煤自然是主要的燃料,“和煤泥”是家家户户的男人,身强力壮的小伙子们最平常的一项家务劳动。
他挽着肥大的裤腿,穿一双拖鞋,夹脚趾的,类似日本木屐的那种,他穿拖鞋劳动这一点让姑娘们印象深刻。还有,就是他娴熟舞动铁锹的双臂,非常健壮、结实,是劳动者的双臂。这时,太阳已经西斜了,这个到处是树的大院子,凉爽下来。煤堆旁,一只小板凳上,坐着一个非常小的小孩儿,一岁,也许是一岁半,扁扁的小鼻子,双手捧着装了橘子水的奶瓶,喝两口,举起来,冲着那个劳动者,爸爸爸爸一阵喊叫,快活地说着谁也听不懂的肺腑之言。那一刻,他们看到的,就是这样一个平凡的劳动者,一家之主,和父亲。
当然,他们来了,呼啦啦一群,他们向他走来,在那一刻他们忽然觉得这是史诗的一天,奥德修记的一天。奔波、坎坷、挫折,然后是,家园和美景。他们走向夕阳中劳动的他,他很惊愕,直起了身。他们中为首的那一个,向劳动者伸出了右手,叹息一样地说道:
“我是刘思扬。”
“哦——”他扔下了铁锹,用沾满煤灰的手握住了那只手。他们会意地、惺惺相惜地、感动地握在了一起:相逢何必曾相识啊。
在后来的岁月中,一个七七级的人,无论走到哪里,和另一个七七级邂逅相逢,只要彼此说一句:“七七级的吗?”仍然,会有一种亲近感:相逢何必曾相识啊。无论生活使他们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得意还是失意,贫穷还是富贵,堕落还是高尚,也不管他们从事什么职业,一句“七七级的吗?”就是一句重返青春时光的符咒,一句意味无穷的暗语。七七级,这是一个共同的名字,一个共同维护的回忆:他们创造了共和国校园历史上短暂的、也许是绝无仅有的一段浪漫时光:自由和诗情的时光。那是他们每一个卑微者涓滴成河聚沙成塔的合力创造。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去,再看看那所学校吧,河边的学校,潘红霞刘思扬的学校,没有任何值得炫耀的历史,也没有一座上年纪的建筑,春天,沙尘暴袭击这城市的时候,它总是首当其冲,一无阻挡。沙尘暴把在操场上上体育课的学生们吹得像枯草一样拼命摇晃。没有关紧的玻璃窗乒乓乱响,有时还会有玻璃被打碎的尖利惨烈的声音。即使所有的门窗都关得严严实实,你看吧,要不了一会儿工夫,那些原本干干净净的课桌上讲台上就会蒙上一层细密的黄尘,像被筛子筛过的一般。可就在这样昏天黑地令人绝望的天气里,也仍然会有阻挡不住的清新蓬勃的笑声。
假如是在一个晴好的天气,这样的好天气毕竟还是有的,你爬上四楼,在朝西的随便任何一个窗口,向外面眺望,你都会看到我们的河流。它曾经壮阔,年轻丰满,脾气很大,可现在它衰老得厉害,几乎就要流不动了。泥沙使它的流水又浑浊又黏稠,这学校的学生,曾试图在那里游泳,可失败了,河水浅得已经浮不起人来,更别提船了。但他们仍然爱它,爱它平凡却意味深长的景致,像爱一个有神秘经历的老人。
七七级和河边的学校(5)
他们并不知道这河流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