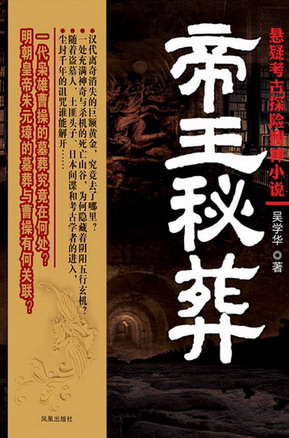���º�.����ϵ��(ȫ��txt)-��824��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ط�G�����Ȼ���ݣ�����������ȥ����ϥ����������ֻ�ǿ�ϧ���㡣��
�����������ǵ����ɡ�����˼�����������ģ�����һ�������ֵ���������Ȼ����С�ţ�ȴ����ıΪ�塣������������������¹�����������Ǽɣ�����������ۡ�ɶ�ʮ���꣬�����̴ӣ�����֮�ԣ�����֮�ƣ��������κ���֮�������龫���Ǻľ�������Ʃ���Ѿ������˵�ҩ��������ο����ã�����������˼�����겻��֮�ģ��ų���ɽ����ԡʥ��֮�У������ƽ֮����������Ϊȫʼȫ��֮�����ڳ�Ϊ����֪��֮������֮��������Ϊһ�η��Ƽʻ�ѻ������������ʳ�֮���룬����ҹ����ҩ�Ծ�������ʥ��֪��֮����˵�ţ���ˮ�������ӹ��������
����ط�GҲ������Ȼ������ҹҪ�¶�����ڣ�ԭ�������ľ��ľ��棬����ʶT�������֣����ֲ��ȣ��������ó�һ���������ã��պ�Ӻۡ���¶����������ø��ʶT�����Ʋ����������Դ���Ⱦ�֮���°�ҹ����ȫ������������˼���ⷬ�����ʵ�ѱ�����������������й�ܣ�����ʮ����֪��֮������Ϧ���壬��ʫ���ģ���Щ���Ҳ��һ���Զ�����������ţ�̾Ϣһ��������������Ҷ�֪���ˡ���֪��������ʲô���㣿����˼����ʱ�������ģ�����˵������Ӻ������������й�����������گ���죬�������̽��Ѿ�����һ��լ�ӡ������Ȼ�ʳ�֮�룬����һ����������У����⼸��̵��������Ҳ�����죬��Ͱ��ȥ��������½·�������ϼҡ����Ѿ���ʮ����û�Թ���ˮ�ˡ���
�������ã����㡣��ط�G������������DZߣ������ڰ������д�˸����������е��������������һ�������ֻ�ȥ���������ġ���������绹ծ����������ʮ�����ӡ��ͻ����أ�Ҫ��ҥ�ԣ����Բ������ˡ��������ڳ������������У�С������Ұ���㲻Ҫ������Ҳ��ҪС��������ȥ�����������鿴���㣬�����Ҹ�����ס�Ĺ٣���ȥ��ʦү��������Ѳ������������ܼ�������
������л���꣡�������¡������������Dz����Ա���һ����
����������˵�ˡ���ط�G�ڰ��֣��н�һ��̫�࣬�Ը���������������ͣ���С�ΰ��������ͳ�ȥ�������ְ̽��úã������ػ�����
������������̫���Ӧһ������������˼����˵���������������������ߡ�����
������˼������ס�����̽����Ŀ�ջ�������������˺þõ�һ��լԺ��������������ӣ�ԭ�벻֪�Ǹ�ʲô���ˣ����ռ��ţ�ȴ�ǹ�����һ���з��ˣ��ּ���̫�����ͣ�Խ����֪��ͷ����ˮ�跹�̺���æ����ͣ����˼��ȴҪ�������������ȥ��������ֻʣ������һ���ˣ���ĬĬ���ţ����붨�����������˻�ϰ����Ҳ�����������ӿ�����ʮ�������뾩����������ʮ����롣����һ�˽����������������һ����ҵ�������ʣ�¹���һ�ˣ�����һ�����½����Σ�һĻĻ����ӿ������ѹ��ȥ��ѹ��ȥ�ַ�����Ҳ����ƽ����
����������֪������Σ���ҹ���������ˡ�������˼����������һ������ǿ��յù��ȣ������������ͣ�ګګ�������������ܹ����ų������������һ�����£��ҵ��ؽ������������������ϡ�Ժ�ӽ����ѩ��Ĩ��ˮ���Ƶģ����ķ�����ֻ���庮Ϯ�ˡ�����Ժ��֩�����ã���Ҫ�ط�������֮�У���Ȼ��ǽ���������Ӷ����������Ǹ�Ů������������ʷ����ʵ��ϰ壺��ʲô������ͷ�ޣ���
������������Ů�ˡ������ϰ�����ν��Ц������������һ�����Ǿ����ˣ���ס�꣬��û��Ӧ��������ү���µ������˼��������˵�������ۿ���ʱ���ˣ���̫�䣬�����ǽ����ɣ������ϰ������һЦ����Ӧ�ſ����ţ�˵���������ǽ����ɣ�˭������������ô�õĿ����أ���
������˼�����ۿ�ʱ���������ˣ�����Ů�ˣ�����һ��ʮ�������С���ӣ�������������л����ȹ�����ů��һ�£����ϰ���ʰ�˷����ٹ�ȥ������������Ҳ��������һ·��������������������ȥ����������ô˵�����ǡ�����
��������˼�����һ������Ҫ������������ǣ�����Ů�˶���̧��ͷ������Ȼ����������һ���ǽ��ã�һ�������ݶ������Ȼ���������ã��ڳԵ��ʵ��������ݶ����㲻�ǡ�����
��������û�������������ݶ�������⣬���ʵ����������ǽ�ʶ�����ġ�������˼���ְ�Ŀ�������ã����ã�̾��������ҵ������Ѿ���˵�ˡ�������õ���ͷ��С���������ҳ��ˣ��Ҹպû��ţ����Ҳ���ˡ�����
������˼������������ã�����˵��������̾������ëͷС����ͦ�Ų��Ӵ������������ˣ�������ԩ�����裡������������ű��Ŷ�������ͷ���ijɻ��ˡ����ݶ�������ҹ���£��������ͨ�죬���Ƿ���Ƶ�ס��˵���������ܣ�ԩ��ͷծ���������Ҳ��á�������Ҷ����ˣ���ij�Ҳ���ˣ��Һ����������ã�Ҫ���ҡ�ֻ�⺢��С�������£�������ô����������˵�ţ���������ֱҪ��������
���������㡭�������ݶ����۶��ǿ�����ɫ��������˼������ɫ������Ļ���û��˵��������˼�����ͷ��������˵����
���������ȽŲ��㣬���������ˣ����ӣ��������������������������������˼���̾Ϣһ�����ֵ��������Ǿþ������ˣ������·����ţ������Ƕ���ԹԹ��ö�ľ��˲�֪���١���Щ�£����Ҷ��ԣ������������̲��������ƽϣ���ͳ��������ˡ���������䲻���У�Ҳ�����У��䲻���ң�Ҳ�dz��ҡ��ô����Ǹ����Ұɣ�����һ�ڷ��Եġ�����
���������������˰�Ъ�ˣ���˼��Խ��û��˯�⡣Ϩ�˵ƣ�������ů���Ŀ��ϡ��¹���ϴ������Ĺ������ԡ������ȫ�����þõ�һ����������ȻԶ�������������Ƶ����ڣ��ѵ���ҹʱ�֡���˼����������ĺ��ǣ���ʱ����������������������أ���˼������ȥ�����ˣ�����̫��Ϥ�ʵ��ˡ�
������������ꡡ����
��
�ڶ�������������
����
��һ�ء�̫�е�ѩ�����ӹء�ɽ�������˾�ƶŮ
��
����������ʮһ��Ķ���������ʪ������������ѩ������ûͣ�����Ծ�ʦֱ��Ϊ���ģ�������죬�����Ⱥӣ���ɽ����������������ֱ��ɽ�����µȵأ�ʱ�������ң�ʱ������ҡ�ۣ���ƬƬƮ������ڶ������װ�������ãã��ûͷû��ֻ�Ǹ��¡�Զ����������ֶ������£�쮷��������ѩ�����ڲ�筵��Ʋ��·��������ţ��Ѹ�����������ͷף����g�g�������еĹ�������������һ�ĵ�ƽ�������ڶ����������ʵʵ��ż��ѩס���ҵ���̫����һ���������ڶ����л������ƶ�����ɫ�⣬�ƺ�Ҫ�����ˣ����������գ�������Ǧ�����Ʋ���ѹ������һ�б��ָ��ɹۣ����ǻ������ѩ���硣
��������ʱ�֣�һ����ʮ������ɽ�����ӹ�һ����ѩ������ɽ����ǰפ��������ʮ����˷�ɫ��һ��ʮ����������������Ʒ��ٴ�������ɫ���������ӣ�������צѩ�㲹����ͷ���Ű���ë��Ƥ��멡�����������Ʒ����ʽ��ȴ������磬���Ŷ�ʮ���ױ������ڶӺ�Ϊ��ȴ��һ����ʮ�����µ����꣬����õ���Ϲ���������ͼ³���ģ����������Ƥ��������Ĺ�����������Ũ�صĽ�ü���𣬽����ŵ�˫��������µ����·���ʱ���˱�ʾ�Լ��ĸ߰������
������ǰͷ����ͣ��������������ס���������ְ���һ�±���Ľ�����һ��������������һ���Աߵ���������ĮȻ��Ŀ�������Ż谵������������һ������һ������æ��������Լ��Ҫ�����ɣ�ū�Ź�ȥ���������������䣬���ſڵ������Ѿ���̤�������������깫����ǰѩ�����ǧ����������ʮ��ү�����Ǹ���ɽ��������û���������ѩ��ǰͷ����ʮ��������վҲû�У���үʾ�£�����Ҫ����Ъ������ɣ���
������������������ף�ת��ͷ������������ʽ������Ǯ�̶����̻�����������Ӻ����������Ѻ�һؾ��ģ����dz����³̣���ط�_Ϥ����������
�����Ǹ���Ǯ�̶��ı���ʽ������ѹ�������ȵ�ͷҲ����̧��æ����Ц�������ǧ������˵��������ү�⻰ū����ô������û���۾���ū�ŵIJ��ϣ�ү˵�У����Ǿ��ߣ�ү˵ס�����Ǿ�ͣ������үֻ˵��ū���Ǻ����̺�ʮ��ү�����������ȵ�ү��ɥ����û�������ӡ�ū����ʮ��ү��������ط�_��Цһ�����ͷ������һ�������������£�ط�_�������ı����������һ���Ƚţ����Ŷ���ͨ�����˵���������������ĸ磬����һĸͬ�����������飬���������㣬�������֣�����ȴ�Ǿ��������Ƿ�ʥ������������Ҳ������мӣ���һ·Ҫ��Ҫͣ�������ס��ݣ���������˵����ġ����ס���Ҳ������˵���㣬�Ҳ�ϣ������װ���ˣ�����ط���ǰ���ʹ�͵꣬��Ҫ����ı�����������ˣ��������ǵĸ�ϵ����
����Ǯ�̶��Ͳ̻���ֻ����Ц����������Ӧ��ֱ��ط�_�����꣬Ǯ�̶��ŵ�����үʥ����ū����ֻ�Ƿ����£������������DZ���ʽ����ͷ��˾���������ࡢ�������ڴ�����ϻ�����ʮ�˲�����أ��ô�ү�����ŵ�ū�ţ�ƽ��������ū���������̺�ү��մү�Ĺ��ʱ�������أ���
��������Ǿ��˻�����ط�_����һ����ת�������Ը�����������Ȫ�����͵�¹��ȡ�����������������ֵ��ǣ���˵�ţ�¹Ƥ��ѥ�ȵ�֨֨�������ţ��������˽���ɽ������
��������һ���������õ����������Ĵ�Ժ�����˳������ѩ������ɽ�ƣ����������������������������ݣ����´��Ŷ����߳����������ɵķ����Ŵ��ţ���ֽ��û���ƣ�����ϵ������ƤҲû�а��䣬�ɶ��ѣ�ֻ�е�Ժһ���˸ߵĴ�������ͷ���ع���һ��ѩ�����������ش���ѩ����·���������˵��ʲô����һȺ�˴������ֻ����������һ���������⾪��һ��Ⱥ�ڵ��б�ѩ����ʯ������ѻ��ɽ��������һֻ���ӳ����ӳ���⧲������䣬Ǯ�̶��ŵ�һƨ������ѩ������Dz̻����ۼ��ֿ죬һ������һ������ʱȴ����ֻҰ����Ц����˵������ʮ��ү�ÿڸ�����
�������š���ط�_��������һ˿Ц�ݣ��漴�����ˣ���̤���Ͻף�һ�߶��Ž��ϵ�ѩ���Ը���������Ժ�����ѩ��һ�壬�����µ����˲�����������λ����ʽ����ס����ҵ�����ס��������Ӫ���ֵ���ס������˵�գ����˶���ݸ����˶����߽�������������б���Ѭ���ںڵ�ɽ�����һ������������߶�˼���ʲô����ͷ��Ǯ�̶��������ⲻ����ư��˵�������ôû����𣬸����ǵ�ʿ����ף�������������ˣ���Ǯ�̶�Ц�������ǣ�ū��Ҳ�������Ρ����̻������Ե��Ż�˵������ү��֪����ɽ��ȥ�����ݲ��������Xʮ�ﶼ�������̣�����Ϊ�����³��ţ������е���ú�����Ƕ������ˣ����������Ȼ����ס�����ﻹ������𣿡�ط�_��δ������Ժ��衱��һ����У����ű���һƬ�����������������ʬŪ��ȥ����
����������������
������������������
����ط�_���֪�����ױ����������䷢���˶��衣���л�����ţ����������������������⣬���������һȺ����˵�����۵����ڰ���ʬ�壬���������������ʲô����һ���ױ�æ�������������������и�ʬ�壬�Ѿ������ˣ��Ǹ�Ů�ġ�����ط�_û֨���������������䷿������һ����Ů�ӣ���Լʮ���������£�ͷ����ɢ�ţ���һ�����ߵ�������������������ֻС�ţ��ù��Ų�����ֻЬ��ǰ�������ţ��������Ŀ�ǽ�����ţ���ɫ���࣬��ȼ���˵����һ���ѿ��������Ʋ�Ӫ�ı�ʿ�������ţ���Լ���»������࣬ȴû�˶��ְ�ʬ��ط�_����˵����������Ҳ������ӵܣ���Ϊ������������ͨ����������̹��һ������ʬ����ɽѪ���ɺӣ����Dz�����ҵı���Ь�����������ҵĻ����أ���
�������ڣ���
�����������ϳ������⣡��
������������
����һ��������Ӧһ����˫������Ů��Ҹ�²������߶�ʮһ���˾��ߣ��յ��ſڣ���Ȼվס�ˣ�˵������ʮ��ү����Ҹ�»����µģ���
�������H����ط�_����һ�£���ǰ������Ů�����ֱۣ��������������ã�˵��������û�о������죡Ū���������ůһů���������ܻ��
���������������ְ˽ţ������Ůʬ̧��������ԣ���æ�����Ȼƾƣ��̿���ҧ�����ع�����ȥ�������������Ѿ��������ƣ��ƽ��������������dz�һ��һ�⣬��ɫҲ������ת����ֻ�Ǽ��ף�������˿�����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