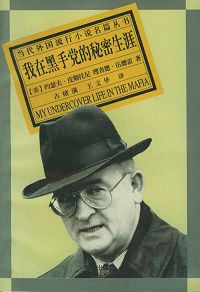地下党-第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中枪那件事当时闹得很大吗?”大姐问。
非常轰动,据说是日本浪人跟地方当局勾结干的。五个人在一个房间里开会,其中三个台湾仔。一伙人突然闯进门开枪打,全部打倒在地,三人当场身亡,两人重伤。重伤的两人中,有一个伤到右胸,抬到教会医院时还能说话,比父亲情况好很多。父亲脑门上中了一枪,脑浆都出来了,人已经濒临死亡,只剩一口气。医生让母亲准备棺材,断定父亲活不过当晚。结果伤轻的人死了,父亲却醒了过来。“他命大。”大舅说,“就像猫。”
本地俗话称猫有九命,大舅说父亲也有九命。大姐觉得不全是命,有时候一个人活下来而另一个人死了,只因为求生意愿有别。一个人拼命想活下去,应当会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活下去的理由。
看过大舅,问过事情,大姐匆匆起身告辞。表姐夫在村里是个富户,宅子相当大,门口有一口池塘,塘边种着龙眼树。那天有风,龙眼树上的树叶让风刮得哗哗响,还有狗在门外汪汪叫,让大姐坐卧不宁。
出门前大姐问:“大舅知道四月二十有什么来历吗?”
大舅茫然,他不知道这一天有什么特别。
从大舅家出来后,大姐快步穿过村巷往村后小庙走。村子里很安静,农人们还在田间劳作,一些人家的屋顶烟囱升起炊烟,有小孩在巷子里窜来窜去,偶尔停下来,好奇地打量陌生人。大姐走过一个拐弯口,一旁突然闪出一个农人打扮的青年男子,扛一把锄头,大步流星,挡在前头堵住道路。大姐心觉有异,急忙收住脚步,左右观察,后边又闪出一个人,居然端着一支步枪。
“别吭声。”端枪的这位低声下令,“往前走。”
“你是谁?”大姐站住不动。
“别问。跟上。”
男子手中是一支旧式汉阳造,走在前头的男子持农具,只能在近距离内发挥作用。大姐身上没有武器,以一个弱女子之力,很难与两个强壮男子相搏,无法硬拼。
她没出声,在枪口的逼迫下跟着前边那人快步走,几分钟后他们走到村后小庙旁。吉普车还停在原地,有两个小男孩爬在车头玩,司机小陈却不见了。大姐被押进庙里,庙门关上,大姐这才看到小陈坐在天井边,已经给捆绑起来。
这里另有两个人,一个矮个儿年轻人持步枪,另一个个子高,年纪大点,拿着一把驳壳枪。大姐瞄了一眼,应当是小陈那支手枪,被他们缴了。大姐到溪尾村找大舅,穿的是便服,小陈却是一身军装,敢把国军军人抓住缴械,会是什么人呢?
大姐没待对方发问,突然主动出击,向高个子发问:“这里你负责?”
高个子不动声色:“你们什么人?”
“自己人。”大姐说,“同志。”
那几个人面面相觑,非常意外。
“我们有任务。”大姐说。
大姐知道溪尾村靠近闽南游击区,有共产党游击队在这一带活动。今天她让小陈开车送她过来,说是走亲戚,其实还想跟游击队接上头。她告诉他们有重要事情需要跟游击队的上级领导联系,比较紧急,请这位负责同志赶紧帮助联络。“什么事情?”对方问。
大姐表示她不能多说,见到上级领导才能讲。
那几人交换眼色。大姐指着小陈,让他们解开绳子,自己的同志怎么能这样捆起来?哪怕不是自己同志,解放军优待俘虏,游击队也一样。司机只是士兵,不是军官,不是反动派,何况他还是自己的同志。
矮个子年轻人分辩:“让他缴枪,他不听。”
“他不知道是自己人。”
“你说是就是?”高个子比较警惕。
“带我们去见你们上级。”大姐说。
尽管对大姐的话不一定相信,他们还是把小陈的绳子解了。毕竟他们人多,而且有武器,大姐小陈两个人赤手空拳,不构成威胁。
大姐问高个子可以带他们去见上级吗?高个子说他们要先报告一下。大姐说情况紧急,迟了只怕会出事。
“到底是什么事?”
大姐问小陈:“车上东西在吗?”
小陈语焉不详:“他们搜过车了。”
高个子追问:“什么东西?”
“情报。哎哟,你们不要搞掉了!”
情报很要紧,牵涉到反动派下一阶段“清剿”的新部署。为这份情报已经牺牲了同志,可不敢在这里搞丢。几位陌生同志不清楚情况,搜查时是不是漏了?不会以为没用,随便扔了吧?会不会让小孩拾走了?赶紧去看一看,也许还能找回来。
高个子说:“走。”
他们俩被押出那座庙,回到吉普车边。两个爬在车头上玩的小孩看到大人来了,跳下车站在一旁看热闹。两个孩子都小,其中一个还穿着开裆裤。大姐打开驾驶室门上车找情报,小陈留在车下,被对方的枪口死死看着。他们并没有轻信大姐的言辞。
大姐在驾驶座没找到东西,她跳下车,绕过车头,打开另一侧助手位车门。站在一旁看热闹的小孩好奇,也跟了过来。大姐把后排车门打开,招呼孩子上车玩。她自己则站在车下,用力推开助手位的椅子。
椅子下边有一个储物柜,储物柜里放着一支小手枪,装在一个精巧的牛皮手枪套里。大姐通常不把枪带在身上,今天到村里找大舅,她把手枪放在座椅下储物柜中。不懂车的人很难想到座椅下边暗藏柜子,通常不会搜查那里。
大姐把手枪取出来。对方几个人一见她从车上下来,手上忽然有枪,顿感吃惊,几支枪口一起对准她。
“别误会。”大姐说,“枪给你们。”
矮个子年轻人接过枪,几个人一起伸头去看。手枪是银白色的,不像武器,倒像玩具,几位估计都没见过,一见不免好奇,啧啧有声。大姐则在一旁追问小陈:“档案袋呢?放哪里了?”
“我不知道啊。”
两个孩子突然“哇”地大哭起来:那吉普车居然自己顺着山坡悄无声息地开始滑动。车上孩子慌张,大呼小叫,车下玩小手枪的大人们这才注意到异常。
只有大姐知道即将发生什么,因为是她一手制造的。军用吉普停在山坡上,面对下坡路,小陈停车后关了刹车闸,找了一块破砖垫在车轮下,车辆不会自行滑动。大姐上驾驶室找东西时有意打开刹车闸,下车时又悄悄抬脚,把垫在吉普车前轮下的破砖踢掉,撤去保险手段。小孩在车上一晃,吉普车就给推动起来,顺坡而下,越滑越快。坡下有一个拐弯,道路左拐而去,不受控制的吉普车直冲而下,将坠入溪流。
意外突起,其他人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大姐心里有数,她大喝:“车上有孩子!小陈快去刹车!”
小陈立刻向前冲去追赶吉普车,大姐跟上,对方几个人发怔,耽搁片刻,才不约而同开步追赶。吉普车尚未滑远,速度还不够快,可以追上。只一眨眼间,小陈冲到吉普车驾驶室旁,拉开车门蹿上车,随后大姐也赶到,上了后排,跟那两个小孩坐在一起,他们一起把车门关上了。
小陈没踩刹车,他开油门,发动机器,开足马力逃命。
对方在车后大喊,以开枪威胁,却没有射击,可能因为车上有村里的小孩。眨眼间吉普车转过山坡,大姐让小陈停车,把孩子放下车,再继续逃跑。
这时大姐才告诉小陈,昨天他们从厦门动身后,她心里一直感觉异样,一切似乎都很正常,却总觉得有哪里不对。她脑子里总有一个人在晃,就是几天前小陈送她回家时在巷子口缠住他们的那个特务头头,姓柯的特派员。
“刚才这几个是他的人吗?”小陈疑惑。
“这几个倒可能真是游击队的。”大姐说。
赶回旅店时正好是中午,主任刚刚起床。
“猪圈修好了?”主任追问。
大姐笑笑,说大舅已经不养母猪,皮箱里的金砖不知往哪里送。
“发愁啥,拿来给我。”主任哈哈,“下午干什么?”
大姐报告,当天下午继续看货,晚上供货商还有饭局孝敬长官。
“没什么事吧?”主任问。
“平安无事。”
“今天这个日子不错。”主任说。
第一章 步步深陷
大姐。30岁。厦门警备司令部军需处参谋,上尉军官。
隐秘暗号
大姐是什么人?除了我熟悉的大姐头,她肯定另有一个面目,于我非常陌生。
我们家里,我最依赖大姐,大姐比我大十岁,我出世之后基本是在大姐的背上长大的。当年大姐自己也是一个女童,母亲把她当做童工使唤,让她成为我的专职保姆。母亲靠自己一双手打水洗衣,维持一家大小生活,从早到晚团团转,没有时间照料我,我这个小不点女孩被全权托付给大姐。大姐拖着两行鼻涕,承担起别人家母亲才承担的职责,给小不点喂米糊,换尿布,抱着哄着,出门把我绑在背上,睡觉时让我蜷在身边。从我懂事时起,大姐在我心中不只是大姐头,她有如母亲。
大姐还是我的老师。抗战初期,大姐在附近一所乡村小学教书,日本占领军横行霸道,学校内外都乱,大姐怕我荒废学业,特地把我从原先就读的小学转到她那里,跳一级插到她的年级,亲自教我。那几年我在学校里得管她叫“钱姓”,也就是“钱先生”“钱老师”,回家才能叫她大姐。在此之前我书读得稀里糊涂,直到成了大姐的学生才忽然开窍,被她调教出来。而后成绩一路上去,成了班上的尖子。
若干年后角色倒了过来,大姐的儿子亚明轮我抱着长大,从一岁直到三岁。大姐生下亚明是在抗战最后一年,当时她和姐夫还在永安。抗战胜利后她和姐夫回来了,一个肉团子一般带着股奶香的小男婴被她塞到我的手里:“澳妹你抱。”
我心甘情愿照料小外甥。大姐曾是我的全职保姆,此刻我只能算是兼职,在课余时间帮工。母亲年纪大了,不再做工,只在家里做家务。亚明是我们家头一个第三代的孩子,虽然姓吴不姓钱,却是男孩,得到母亲极大的看重和宠爱。只是她身体不好,手臂无力,已经不太抱得动孩子,通常是动嘴不动手,指挥我为亚明办这办那。抗战胜利之初大姐很忙。她是市政府雇员,而后进警备司令部穿上制服,天天要去上班,事情没完没了,早已不是当小学老师时的样子。不变的是她依然“紧性”,风风火火,说一不二。她回家后,我们家的主导权又从母亲手里转移到她手中,包括亚明的监护权。大姐总是想把他交到我的手里,不放心让母亲围着转。
“阿姆不要老是死啊活啊骂,小孩学粗了。”她说。
母亲很生气。
那一年冬天厦门特别冷,感冒大流行。亚明生病了,病相凶险,头天喉咙痛,第二天发高烧,接连三天不退,全家人急坏了。孩子送到医院住院,医生诊断是患了肺炎,狠下重手,开了最厉害的药,却未见有效,高烧稍微压下一点,转眼又冲上去,比用药前还高。小不点男孩受不了折腾,几天下来,整个人烧迷糊了,吃什么吐什么,从早到晚昏睡,奄奄一息。医生通知孩子病危,只怕不行了,家长要有心理准备。
那几天我请了假,天天守在医院里照顾小外甥。看着孩子饱受折磨,一点一点蔫下去,真是心如刀割,无法忍受。大姐更是焦虑万分,她在医院里跑来跑去,竭尽全力帮助儿子与病魔相搏,渡过难关。
有一件事让我匪夷所思:姐夫突然离开了厦门。
姐夫吴春河当时在厦门一家报馆做事,住在我们家里。姐夫有一副好脾气,他比大姐大不少岁,在家里却是个受气包。大姐什么时候不痛快了,动不动会朝他喊叫——这种秉性估计出自遗传,大姐跟我母亲最像。吴春河对大姐的喊叫从不当回事,你喊你的,他做他的,既不回嘴,也不误事,等大姐自己偃旗息鼓。姐夫这种本事让我很佩服,我思忖他要比我父亲能忍,父亲会不会是因为受不了母亲的脾气,这才离家不归?我知道大姐常对姐夫使性子,家里唯一能够管她的却还是姐夫,她其实很听姐夫的话,只不过不高兴了要吼几声而已。
亚明住院那几天,姐夫没少往医院跑,一来就摸亚明的额头,一张脸万分沉重,除此之外他帮不上什么忙。亚明病危的前一天黄昏,他匆匆赶到医院,看过孩子后,把大姐叫到外头去说话,我留在病房里。
我听到他们在外头吵了起来,隐隐约约,我听到姐夫提到了什么“任务”。大姐朝姐夫喊:“你去死!”
大姐不光脾气得自母亲,骂人也得自母亲真传。她把我吓坏了。
一会儿大姐走进病房,一言不发坐在亚明床边。姐夫跟了进来,什么话都没说,伸手摸摸亚明的额头,把他的小被子捂好,转身离开。出门前他把身上的皮衣脱下来,披在大姐身上,大姐负气一摇身子,皮衣滑落于地,他拾起来再披上去。
那天很冷。
姐夫就这么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