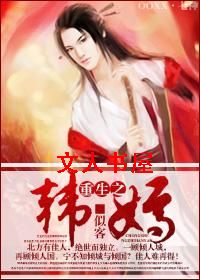山南水北_韩少功-第1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好兵帅克》里的滑稽。
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捷克作家不也就是实话实说吗?
我想起另一个作家阿城。阿城杂学颇丰,对国粹遗产尤多独见。他认为中国古代艺术都是集体性和宗教性的,因而也就是依赖催眠幻觉的。那时的艺术源于祭祀,艺术家源于巫师,即一些跳大神的催眠师,一些白日梦的职业高手。他们要打通人神两界,不能不采用很多催眠致幻的手段。米酒,麻叶,致幻蘑菇,一直是他们常用的药物,有点相当于现代人的毒品——阿城曾目睹湖北乡下一些巫婆神汉,在神灵附体之前进食这些古代摇头丸。这样,他们所折腾的楚文化,如果说有点胡乱摇头的味道,有些浪漫和诡谲甚至疯狂,那再自然不过。先秦时期青铜器、漆器、织品上的那些奇异纹样,还有宋代定名的饕餮纹,那些又像牛脸又像猪脸又像鳄鱼头的造型,还值得后人费解吗?它们漂浮升降,自由组合,忽儿狂扭,忽儿拉长,忽儿炸裂,发出尖啸或雷鸣,其实都是催眠成功后的真实幻象。
在亚洲、美洲、非洲、大洋洲等地,各种古代器物上的夸张造型比比皆是。照阿城的说法,我们大可不必把它们看成什么风格追求的产物——世界各地的人们不约而同来一个追求,其实也不可思议。它们不过是萨满催眠的产物,甚至不过是古代诸多“毒品”的正常药效。与其说它们是神秘主义的,或者浪漫主义的,或者抽象主义的,或者表现主义的,或者超现实主义的(现代人喜欢制定很多主义),不如说它们更像是致幻药物发作时的视觉变形。
从这个角度看,这些古代艺术其实也就是如实写真。
我在大学里背记过一大堆文艺学概念,得知现实主义的特点是“写实白描”,而夸张、变形、奇幻、诡异一定属于其它什么主义,必是文艺家们异想天开的虚构之物。我现在相信,这些概念的制定者们一定不了解捷克警察,不了解古代巫师,同样也没有见识过我家的窗口——推开这扇窗子,一方清润的山水扑面而来,刹那间把观望者呛得有点发晕,灌得有点半醉,定有五腑六脏融化之感。清墨是最远的山,淡墨是次远的山,重墨是较近的山,浓墨和焦墨则是更近的山。它们构成了层次重叠和妖娆曲线,在即将下雨的这一刻,晕化在阴冷烟波里。天地难分,有无莫辨,浓云薄雾的汹涌和流走,形成了水墨相破之势和藏露相济之态。一行白鹭在山腰横切而过,没有留下任何声音。再往下看,一列陡岩应是画笔下的提按和顿挫。一叶扁舟,一位静静的钓翁,不知是何人轻笔点染。
这不是什么山水画,而是我家窗外的真实图景。站在这里,哪怕是一个最大的笨蛋,也该知道中国山水写意的来处。
这种山水写意的简约和奇妙曾震住了很多画家,甚至深深吸引过西方的毕加索。它们是古代画师们天才的技术发明吗?也许是。不过这话只说对了一半,或者只说对了一小半。只有那些从未亲眼见过真山实水的理论家们,才会把这些话太当回事,并随后培养出很多刻意求奇的主义发明家。他们把艺术才子培养成一些狂徒,又是一些苦命人,老是皱着眉头,目光发呆,奇装异服,胡言乱语。如果他们无能把艺术搞得怪怪的,至少能先一步把自己搞得怪怪的;如果无能把自己的内心搞得特立独行,至少能先一步把自己的外貌搞得惊世骇俗。他们永远的焦虑,就是不知道那个救赎自己的“风格”和“主义”到底在哪里,常常在大海捞针的毕生苦刑中耗尽心血。
如果换一个角度,比如站在我家窗口来看,写意其实是平易的,简单的,朴素的,差不多就是写实,甚至是老老实实的照相。一个画家,只要他见识过中国南方的山水,尤其是见识过多云多雾的雨季山水,见识过涌入大门和停驻手中的一团团白雾,见识过挂在叶尖和绕在阶前的一缕缕暗云,不大悟于前人的笔墨(比如晕化和破墨),倒是不正常的。
最大的主义其实是诚实的主义,与放辟邪侈无缘。一切我们颇感新异的艺术样式,无论经过了多少艺术家有心营造,不论受益于多少工具发明和技术改进,就其根本而言,可能都有一个最为现实主义(如果可以称之为现实主义的话)——的经验源点,只是不为后人所知罢了。
这种生长着想象的源点,隐匿在中国人不曾感受的捷克,正常人不曾体会的巫师,都市人不曾见识的乡间山水那里。如此而已。
墙那边的前苏联
我家院墙那边是学校操场,再远处,是时静时喧的教学楼,还有不时冒出鸡鸣鸭叫的教工宿舍。这是一所九年制学校,全乡唯一的学校。
很多山区的孩子上学太远,没有办法,只好从小学一年级就寄宿。我从校区走过的时候,常看到一些孩子在保姆的指导之下洗脸,洗手,洗碗,乃至解裤带拉屎。稍大一些的学生,把扫地当作狂欢,用扫把搅出满天黄尘,搅出咯咯咯的欢天喜地。还有一些学生在那里排练仪仗,只是少先队礼行得不大规范,不但缩头缩脑,而且小小手臂弯曲如钩,钩住自己小脑袋,一付闯祸以后防备毒打的畏缩模样。
不知什么时候,墙那边有前苏联时期的歌声飘来:
当年我的母亲,
通夜没有合上眼睛,
伴我走遍家乡,
辞别父老乡邻。
当时天色刚黎明,
她送我踏上遥远的路程。
给了我一条毛巾,
她祝我一路顺风……
这是一首著名的俄罗斯歌曲,正在由一位女教师教唱。我很好奇,一首在耳际消失了数十年的歌曲,为何出现在这个老山角落,撞入了我的黄昏?更有意思的是,从这一首歌开始,院墙那边简直成了前苏联,《喀秋莎》,《三套车》,《小路》、《红莓花儿开》,《伏尔加船夫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等,一曲曲全成了清脆童声,经常使我恍若隔世,恍若入梦,差一点想翻上墙头,看看墙那边的白桦林和冰雪草原,向红色少年的骑兵军挥手致敬。
一天,我终于忍不住,到学校里去打听教歌的女老师,打听她为什么对这些老歌情有独钟——这些怎么听都有些忧伤和沉重的歌。我得到的消息是:教唱者是一位小姑娘,在这里的四个月的代课已经结束,刚回县城去了。
正当梨花开遍了原野,
河上飘着柔漫的轻纱……
小姑娘留下的歌声不时在校园里飞旋,如零散的薄公英随风飘飞不知所往。它们带去的种籽,也许会发芽,也许会枯灭,在血色残阳下的黄昏。
当年的镜子
庆爹一进门就说:“你说这事怪不怪?波黑还在打来打去的。这联合国怎么就喊不住呢?”
我说:“要你不去买码(私彩),你还在买。乡政府喊了这么多回,喊住了你么?”
他不好意思地笑笑,哼哼嘿嘿,换了个话题:“你说成思危怎么这样会讲呵?好学问,真是好学问。讲一两个时辰,不打一下顿,也不喝口水!”
我不大熟悉成思危,更不知道这位北京的大人物最近说了什么。说实话,每次见庆爹上门,我总是会从他嘴里得知许多重要大消息,弥补自己的孤陋寡闻。
说到姓成的,庆爹说成姓人很少见,八溪峒以前倒是有过一位。这就引出了一个故事。据说还是在民国时期,峒里办新学,有了第一所新学堂。一位姓成的女子从安徽逃难而来,在学堂里临时教书,教学生唱很多洋歌,人也长得漂亮,几乎招引全峒的年轻女子前来学堂偷看,看她的明眸皓齿,还有小旗袍和洋口琴。
日军攻打长沙的时候,常有一批批日军飞机飞来,大概是借汩罗江为地面路标,前去轰炸国军。当地政府接上峰指示,下令收缴所有的镜子,称镜子可以给日本飞机打信号,指方向,因此凡私藏镜子者一律按汉奸论处。安微来的女教师常常梳头,舍不得交镜子,后来被人告发,入了县衙大牢。据说告发者是本地一地痞,曾经拿光洋铺满一茶盘,请女教师去陪酒贺寿。女教师不从,撕碎了请柬。
地痞恼羞成怒,一状告到县衙门,说女教师教的歌是日本歌,吹的口琴是日本货,有时上山去根本不是为了采什么花,而是拿镜子给日本飞机打信号。这些说法越传越邪。县衙的主审官派人来搜查,果真搜出了女教师的镜子,再加上一顿杖刑,逼对方屈打成招,最后把她当汉奸毙了。
狗官事后还夸耀:那婆娘太乖致了,照得我眼花。我若不重判,人家一定会说我好色——我一世清名岂不坏在她手里?
这就是流传很久的一件汉奸案。多少年后,女子的家人从安微前来寻尸,掘开女子的坟墓,发现棺木和尸骨都已化成腐泥,只有一颗心脏完整如初,甚至鲜活血色犹存,让人们大吃一惊。山里人传说:那女子太冤了,所以一颗心怎么也不死。
诬告者不久就患下大病,肚子胀得像面鼓。家人请来师爷抄写佛经,以图还愿消灾。没料到第一个师爷刚提笔,手里叭啦一声巨响,毛笔逢中破裂,成了一把篾条,没法用来往下写。第二个师爷倒是有所准备,带来一支结结实实的铜笔。这支笔破倒是没有破,但明明蘸的是墨,一落纸上就便成了红色,如源源鲜血自毫端涌出,吓得执笔者当场跌倒,话都说不出来,得由脚夫抬回家去。
诬告者几个月后终于一命呜呼。
知情人
一位后生在镇上做二手车生意,夜里来我家玩玩,说到了电脑上网。我当即拨号上网,搜索了一下桑塔纳二手车的供求信息,打印出来交给他,前后花了十来分钟。他看着那几页纸,大为惊异,说这家伙太神了。
他骑着摩托没入夜色,回镇上去。第二天早上我妻子去买豆腐,路过熟人家,受邀喝了一杯茶。她身边有一位陌生老汉守着自己的提袋和两捆烟叶,看样子是在等候班车的。他也在喝茶,不知什么时候冷不防问:“你们昨天上了网?”
我妻子开始没听明白。
“你们家昨晚没有上网么?”老汉又问。
“你是说……”我妻子没想到对方问的是因特网。
“上网呵。在网上找汽车呵。”
她这才慌慌地说:“是……是……吧?我不大知道。你怎么知道?”
老汉笑了笑,说他是听秀木匠说的——此木匠是山那边的人,刚才赶着牛从这里路过。
我妻子不认识秀木匠。更重要的问题是:秀木匠又是听谁说的?
我与妻子后来都大感惊奇。从昨天深夜到今天早上,也就不到六七个钟头,而且是在夜晚,一个陌生老头怎么这样快就得知上网一事?昨夜来访的后生,与这个路边的老汉,与什么秀木匠,与我们可能尚无所知的张三或者李四,并不住在一处。他们分散在山南岭北,桥头坝尾,互相八竿子打不着,怎么刹那间全都成了知情人?从山这边到山那边,又从山那边到山这边,他们组成了怎样的信息链和信息网?要是在城市,我们常常连邻居姓甚名谁都不知道。倒是在居住分散的乡村,似乎任何房子都成了玻璃房子,任何人都成了玻璃人,以至所有事情都被公众了若指掌。
从此,我在乡村里对任何陌生人都不敢怠慢和小视。我怀疑这些老人、后生、女子都是重要的知情者。他们一定知道我每天说过什么,做过什么,写过什么,甚至有过什么不可告人的勾当。他们互为眼线,互通机密,装作不认识我的样子,只是不愿意说破罢了。
他们似乎有一种通过风声和鸟语来洞察世界每个角落的能力。
隐者之城
在山村里住久了,我有时会向往都市。倒不仅仅是怀念都市里的舒适和方便,因为做到那一点并不太难,在乡下实现那一切的日子也不会太远罢。
在我看来,都市生活最大的诱人之处,是人们互为隐者的一份轻松。我们有同事但可能从不知道同事家里发生过什么,有邻居但可能从不知道邻居房门后是何景象。至于更多的客户、乘客、路人、售货员、水管工、邮递员、保险推销人等等,在每个日子里拥挤而来,但因为太密集而被我们视而不见,过目即忘。他们是一些着衣的影子,一些游动的布景或飘忽的面具,其姓名如同假名,其言语如同台词,其服装如同伪装。他们让我们难以辨识也无须辨识,无法深交也不需深交。
我们真正的同事和邻居是影视片里的知名演员、流行报刊里的新闻人物、网上聊天室里的匿名网友。如果我们顺着电缆一类线索查下去,追查到繁忙媒体的车
![[韩超] 毁灭封面](http://www.34gc.net/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