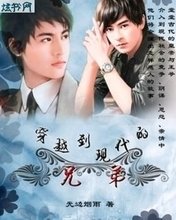极端的年代-第8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压倒了原有“老布尔什维克”的声音,也盖过了1917年前加入他们合作的其他社会主义人士,如托洛茨基。他们与传统左翼原有的政治文化毫不相通,他们只知道党永远正确,只知道上级的决定务必执行。因为唯有如此,革命的果实方能得以保存。
革命之前,不论党内外对于民主、对于言论自由、对于人民自由、对于宽容异己,对以上种种事项的态度看法为何,1917…1921年间的政治社会氛围,却使得任何一个意欲挽救苏维埃政权于挣扎脆弱的政党,都不得不陷于愈发走向权威统治模式的境地。其实一开始,苏联并非马上便成为一党政府,它也不排斥反对力量的存在。可是它却以一党独裁的姿态,靠着强大情报安全工作,以及全力打击反革命的恐怖,赢得了一场内战。同样地,它也放弃了党内民主的原则,于1921年宣布,禁止党内对其他可行的政策进行集体讨论。在理论上指导它的“民主集中制”精神,如今“民主”不存,只剩下“中央集权”。它甚至不再遵照自己的党纲行事,原定每年举行的代表大会愈来愈时有时无,到斯大林时代,更变成毫无准期,偶而为之的稀奇大事。“新经济政策”年代虽然缓和了非政治层面的气氛,然而就党的形象而言,却没有多大好处。一般的感觉认为,党已成为了饱受攻击的少数分子,虽然也许有历史站在它的一边,可是眼前的行事方向,却不合俄国现状及民众的心意。从上而下发布的全面工业化革命号令,遂使整个系统愈发走向强制权威,比起内战年代,其残忍无情,也许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这套连续实行权力的机制,如今更具规模。于是在“权限分离”之中剩下的最后一项成分,即“党”“国”之间的分野,苏联“政府”最后留下的运作空间日益缩小,这个卑微存在的狭小空间,最终也全部消失。只见一党垄断,定于一尊的领导高高在上,绝对的权力在握,其他所有的一切,都屈从在他的号令之下。
就在这个时候,苏联体系在斯大林手中变成了一个独断专制政权。这个政权,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不但要全面整体地控制其人民生活、思想的各个层面。人的存在,人的价值,但凡可以之处,也完全受制于整体制度的目标与成就。至于目标为何,成就何在,则由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界定指令。这样一个世界自然绝非马克思恩格斯两人设想的未来,也非发展自马克思路线的“第二国际”(second international)及其旗帜下的众多党派所期。因此与卢森堡同任德国共产党领袖,并与她同于1919年被反动军官暗杀的李卜克内西,虽然其父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之一,却从不认为自己属于马克思派。而奥地利马克思派(austro…marxists)虽然名列马克思的门下,并且也戮力于马克思的学说,可是却毫不犹疑地别出心裁,另辟蹊径。甚至连被共产党官方正式视为异端者,也依然被人视为理所当然,合乎法统的社会民主派人士——如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即因其“修正理论”(revisonism)而被戴上这项异端帽子(事实上,伯恩斯坦也始终是马恩著作的正宗编辑人)。所谓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强制每个人思想统一的主张,这种论调,若回到1917年前,根本不可能在任何社会主义者的脑海中出现,更别说其领导们圣袍加身,称其“集体智慧”,拥有如教皇制服绝对无误的圣质(虽然单让任何一人拥有这种天才英明,毕竟仍属不可想象之事)。
就马克思派社会主义的信徒来说,它在根本上便属于一种激情的个人承诺,它是一组希望,一组信仰,具有某种世俗宗教的特点——不过论其宗教性,并不见得多于那些非社会主义群体的意识形态。更重要的是,马克思社会主义一旦变成一股洪流,成为广大的群众运动,原本微言大义的精幽理论就难免变形。最佳,也只不过流于僵化独断的教条;最糟,则幻化成人人须敬而礼之、认同效忠的旗帜象征。这一类的群众运动,正如某些深具真知灼见的中欧社会主义人士早已指出,往往具有敬仰甚至崇拜领袖的倾向。不过大家都知道,左翼党派内部素来喜欢争辩,因此个人崇拜的程序多少受到抑制。在莫斯科红场上兴建列宁陵墓,将这位伟大领袖的遗体防腐处理,永存于此以供瞻仰。这番举动,与革命、甚至与俄国本身的革命传统都毫无关系,显然是为了苏联政权,意欲在俄罗斯落后的农民大众之中,激发出类似对基督教圣者及遗骨遗物的崇拜热情。我们也可以说,在列宁一手创建的布尔什维克党中,所谓正统性的思想,以及对异己的不容忍,多少是以实用性的理由出发,而不仅是作为基本的价值观。列宁就如同一名杰出的将领——其人基本上属于计划行动的好手——他可不要部队里人人有意见,个个议论不休,因而造成实际效率的损失。更有甚者,正如所有讲求实际的天才们一般,他也深信,唯有他自己的意见最对最好,因此哪有多余的工夫去听他人纠缠。就理论上而言,列宁属正统派,甚至可说是一名原教旨主义的马克思门徒。因为他很清楚,像这样一个以革命为基本要义的理论,若对其教义文字有任何瞎搞胡掰,都可以鼓励“妥协修正”意见的出现。但是在实际上,他却毫不迟疑,着手修改马克思的观点,并任意增添内容;同时却为自己辩称,实质上始终忠于伟大教师的教诲不变。在1917年前的岁月里,列宁不但一直领导着俄罗斯左翼路线内(甚至在俄国社会民主圈内)饱受攻击的少数,而且更是这一支力量的代表,因此获得了一个不容异己的名声。可是一旦情况改变,他却毫不踌躇,一如他往年坚决地排除反对者一般,立刻便伸出手来欢迎他们。即使在十月革命成功之后,他也从不倚仗自己在党内的权势压人,反而一直以立论为出发点来说服众人——我们甚至看见,虽然他位高权重,却也不是从来不曾面临挑战。要是列宁后来没有早死;相信他一定会继续激烈抨击反对者,就像在当年内战时期一样,他那以实际为用不容异己的作风,必将没有止境。不过尽管如此,却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列宁预想到——甚或能够容忍——自己身后竟会发展出那一种无孔不入、全面性、强制性的国家暨个人全民信仰的共产宗教。斯大林也许并不是自觉地创设出这个宗教,他可能只是懵懂地跟随着当时自己所见的主流现象:一个由落后农民组成的俄罗斯,一个权威独裁、讲求正统教理的巨大传统。但是若无斯大林,这个极权新宗教很可能不会出现;若无斯大林,这个新宗教模式绝对不会强加于其他社会主义政权,或为它们沿袭模仿。
一个资产阶级的政权,也许可以接受保守政府下台,由自由分子接班的念头。因为后者纵使上台,仍将不改社会上的资产阶级本质,可是资产阶级政权,却绝对不能容忍共产党接手。同样地,一个共产党政权,也同样不能忍受被一个必定动手恢复旧秩序的力量所推翻。可是这个假定,却不意味着苏联一定会出现定于一人的独裁,是斯大林其人,一手将共产党的政治制度,转换成非世袭的专制君主制。
就许多方面而言,这个矮小、谨慎、缺乏安全感、永远疑心重重的斯大林,活脱脱就是罗马传记大家苏埃托尼乌斯(suetonius)笔下《历代罗马皇帝传》(lives of the caesars)中帝王的再现,而不是一名现代政治世界的现代人物。他外貌平凡,一般不易给人产生深刻印象,斯大林一直使用八面玲珑的斡旋手段,一直到他升至顶层为止。当然,即使在革命之前,他就已经凭着这项了不起的天赋,进入党的高层;在临时政府垮台之后的首任政府里,斯大林就出任民族部部长。然而在他最后过关斩将,终于登上顶峰,成为无人挑战的党内领袖(事实上也是国家领袖)之后,则一概使用令人恐惧的手段,来处理党务或其他任何他个人权力所及之事。
同样地,他将“马列主义”简化为简单绝对的教义问答、教条式口号的做法,也不失为将新观念灌输给第一代识字人的上乘方式。而他的恐怖作风,也不可仅视为暴君个人无限度权力的支持。诚然,斯大林本人一定颇享受那种大权在握,得以呼风唤雨的乐趣,那种令人恐惧,定人生死的权力感;但是他对本身地位所可带来的物质收获,却漫不经心。而且,不管心理上精神上,斯大林到底有什么乖僻怪诞之处,他的恐怖手段其实和他的谨慎作风一样,都是他在面对难以控制的局面时,一种同样理性的对付策略。不论是恐怖还是谨慎,都是基于他避免风险的原则考虑。两者分别反射出他的缺乏自信,不能肯定自己的“评估状况”能力(套用布尔什维克的术语,即对状况“进行马克思主义分析”的能力)。这一点,却正是列宁的极大优点,两个人的个性气质可谓大相径庭。斯大林恐怖“立业”的唯一意义,只能表示他终身不悔,顽固追求那想象中的乌托邦的世界。甚至在他死前数月,在他最后出版的书中仍致力于这一目标的再坚持、再主张。
统治苏联的政治权力,是布尔什维克党人在十月革命中取得的唯一收获,而权力,也是他们可以用来改变社会的工具。但是这项权力,却不时遭逢来自不止一方,并且不断再现的困难夹击。斯大林曾有一套理论,他认为在“无产阶级取得权力的数十年后”,阶级斗争反而会变得愈加激烈。他这套说法的真正意义即在于此,否则换作其他任何角度,都是讲不通的。只有前后一贯地、残忍无情地、坚持地使用权力,才能除去各种可能的障碍,走上最后成功的阳关大道。
基于这套假设而决定的政策,其中有三项因素促成其走向无比凶残的荒谬境地。
其一,斯大林相信,只有他才知道前途如何,而且一心一意、全力为之。诚然,无数的政治家及将领们,都有这种“舍我其谁,少我不得”的心态,可是只有那些真正绝对权力在握之人,才能迫使众人也一起相信只有他才最行。因此在30年代掀起的大清算高潮,与此前的恐怖捕杀不同,这一回清洗的对象,是针对党内而言,尤其是它的领导阶层。原因在于许多原来支持斯大林的强硬派党员开始后悔(包括那些20年代全力支持他对付反对人士,并且真心拥护集体大跃进及五年计划的人)。他们如今发现,当时手段的无情,造成牺牲的惨重,已经超过他们所愿接受的程度。这些人当中,相信有许多人都还记得,当年列宁便不肯为斯大林撑腰,不愿让他接班,理由就在他行事作风太过残暴。苏联共产党第十七届大会揭幕,会中形势,即显示党对斯大林有着相当的反对力量存在。这股反对势力,对他的威胁究竟几何,我们永远都无从得知。因为从1934…1939年,有四五百万党员及干部因政治理由被捕,其中约四五十万未经审判即遭处决。到1939年春天,十八届党代表大会召开,当初1934年参加第十七届会议的1827名代表中,只有37名侥幸仍得以再度出席(kerblay1983,p.245)。
这种难以形容的恐怖,不是出于什么“为求伟大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信念,也非基于“这一代的牺牲再大,与未来世代因此得受的福祉相比,却又算得什么”的理想。它是一种无论时空、永远全面作战的原则的体现。列宁主义,基本上是从军事角度思考——就算布尔什维克所有的政治词汇均不能证实此点,仅看列宁本人对普鲁士兵法家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的崇敬,即可证明这是不争的事实。也许正因为列宁思想中带有着强烈的“唯意志论”气息,使得其他马克思人士极不信任列宁,将其斥为布朗基派(blanquist)或“雅各宾”之流。“谁胜谁负?”是列宁的处世箴言:这场斗争,是一场不是全输就是全赢的战争,胜者赢得全部,输家倾其所有。我们知道,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际,即使连自由国家也采取这种心态作战,准备不择手段,对敌方人民毫无保留地施以任何苦难折磨(回到第一次大战时,无尽苦难的对象甚至在自己的部队内)。于是没有事实基础,毫无理由地便将整批人送去牺牲的做法,也的确成为战争行为的一部分:比方二战期间,美国政府将所有日裔美国公民,英国将境内所有德奥籍居民,一律关入拘留营内即为例。美英两国的理由,乃是基于这些人当中可能潜有敌方奸细。这场不幸的变调,是在19世纪以来文明进步之下忽然有野蛮复萌的悲剧。此情此景,却像一股黑暗势力的漫漫长线,一直贯穿着本书涵盖的悠悠岁月。
所幸在其他实施宪政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