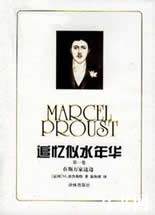追忆似水年华[美]-第12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外部效果来判断,只能说圣卢努力做到诚恳和外露是非常了不起的,但也容许人们庆幸德·夏吕斯先生恰恰缺乏这二者。夏吕斯先生叫人将盖尔芒特公馆一大部分精美的木器运到了他外甥家里,而不是象他的外甥那样拿这批家具换了一套时髦款式的家具和一些勒布①和纽约曼②的画。
……………………
①勒布(1849—1928),法国画家,早期自由发展,1877年他与莫奈、毕沙罗、德加结识。深受印象派影响。
②纪约曼(1841—1927),法国画家,与印象派画家关系密切,自觉与塞尚和毕沙罗最接近,其作品已显示出表现主义与野兽派的某些特点,但总的来说他是自然主义的。
德·夏吕斯先生的理想非常做作,这也是真的,如果“做作”这个修饰语可以与理想这个词联系起来的话,也就是说,既有社交气又有艺术性。几个姿色倾城又有罕见文化素养的女性,两个世纪以前,她们的祖先就已与君主制度全部的荣光与风雅结为一体。他从这样的几个女性身上找到了出众超群的东西,使他能够和她们在一起才感到快乐。诚然,他对这些女性的钦佩是诚心诚意的,但是她们的名字所唤起的许多历史与艺术上的模糊回忆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恰如贺拉斯的一首颂歌说不定比如今的一些诗歌逊色,但是一个文人读起前者来会感到快乐,对后者却无动于衷,对古代的回忆是他感到快乐的原因之一。这些女性中的每一个,与一个漂亮的布尔乔亚女子相比,对他来说,犹如那些古画之于当代一幅画着一条路或一次婚礼的油画。对那些古画,知道它们的历史,从定购这些画的教皇或国王开始,中间又经过什么大人物,这些画,通过馈赠,购买,取得或继承遗产,又唤起我们对某一重大事件的回忆,至少也唤起我们某一有历史意义的联想,因此我们获得的知识便赋予这些作品以一种全新的用处,增强了我们头脑中或我们博学中拥有财富的感觉。如果与德·夏吕斯先生的偏见相似的偏见妨碍这几位贵妇人去与血统不那么纯正的女性为伍,而将她们未起任何变化的崇高完整地奉献到他的祭坛上,就象某一十八世纪建筑的门面,由玫瑰色大理石平滑的廊柱支撑着,新朝代来到并未丝毫改变这门面一样,他是很为此庆幸的。
德·夏吕斯先生赞赏这些女性真正精神崇高,心地高尚①,就这样用模棱两可来搞文字游戏,这模棱两可欺偏了他自己,其中也有这一含混概念、这种将贵族、心地高尚与艺术混为一谈所造成的虚假表象,同时也有夏吕斯先生诱人的一面。对于我外祖母这样的人,这种引诱是非常危险的。一个贵族,只看到自己的营盘,对其余的则不闻不问,他的偏见更荒唐,但也更无害人之心。对我外祖母来说,她似乎觉得这种偏见过于可笑,但是一旦某种东西在超人智慧的外表下出现,她就无还手之力了,以至她以为王子所有的人都出众超群,令人艳羡,因为他们得以有拉布吕耶尔②和费纳龙③这样的人作私人教师。
……………………
①在法文中,这里用的“崇高”和“高尚”字眼与“贵族”为同一个词——ńoblesse。
②拉布吕耶尔1684年被指定为波旁公爵(1668—1710)的历史、地理、法国各机构、哲学教师。
③国王路易十四于1684年任命费纳龙为其孙子勃艮第公爵(1682—1712)的私人教师。
在大旅社门前,三位盖尔芒特家人离开了我们。他们到卢森堡亲王夫人家用午餐去了。就在外祖母向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道再见,圣卢向外祖母道再见的时候,直到此刻没有与我讲过话的德·夏吕斯先生向后走了几步,来到我身边。
“今天晚上晚饭后,我要在维尔巴里西斯婶母房内喝茶,”他对我说,“我希望你能赏光与你外祖母前来。”说完他追侯爵夫人去了。
这天虽是星期天,旅馆门前的出租马车并没有度假季节开始时多。尤其是公证人的妻子,她觉得因为不去康布尔梅家而每次租一辆马车实在太破费,干脆待在自己房间里。
“布朗代太太身体不适吗?”人们问公证人,“今天没见她呀!”
“她有点头疼,天这么热,又下雷阵雨。有一点事她就要……我想今天晚上你们能看见她。我已经劝她下楼了。这会对她有好处。”
我以为德·夏吕斯先生邀请我们去他婶母那里,是想弥补上午散步时他对我表现出的无礼,我也不怀疑他肯定通知了他的婶母。但是,当我走进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客厅,想向她的侄子问好时,我在他周围转来转去,一点搭不上话。他正用尖细的嗓门,针对他们的某个亲戚讲一个相当不怀好意的故事。我无法捕捉他的目光。
我下定决心向他问好,而且声音相当大,为的是提醒他注意我的存在。可是我明白他早已注意了我的存在。因为就在我躬身施礼而从我的双唇还没有发出一个字音的时候,我看到他伸出两根手指叫我握,而眼睛却没有转过来,亦未中断他的谈话。显然,他看见了我,只是不露声色。这时我发现他的双眼从来都不定睛望着谈话对方,而是不停地四面转动,就象某些受惊野兽的眼睛,或者露天小贩的眼睛。这些露天小贩,他们一面大吹特吹,展示他们那违法的商品,一面头虽不转,却眼观四路,窥视着警察会出现在地平线上的各点。
我看出,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看见我们来了很高兴,但是她似乎没有料到我们会到来。我有点惊异。德·夏吕斯先生对我外祖母说:“啊,你们来了,这个主意真不错。婶婶,这真好,是不是?”
我听到这话,更惊诧莫名。显然他发现他婶母见我们进来大吃一惊,作为惯于定调子的人,他想只要指出他本人感到很高兴,就足以将这惊讶变成快乐了,而且我们前来也确实应该激起快乐的情绪。
这件事他算计对了,因为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对她侄子看得很重,而且知道要讨他开心是多么困难。她似乎突然发现我外祖母有什么新的优秀品质,不断地殷勤招待她。
我无法理解,德·夏吕斯先生在几小时之内便将当天早上向我发出的邀请忘得一干二净。这邀请虽然很简短,但表面上看是那样有意为之,那样经过考虑,他竟然将这个完全是他自己的主意,称作我外祖母的“好主意”。我那时还是“丁是丁,卯是卯”的,直到后来长大了,才明白:对于一个人的意图到底如何,不是向他本人询问就能得知真相的;宁愿冒产生误会的危险,误会说不定未引人注意就过去了,这种风险远远小于天真地认死理。
“先生,”我怀着非要弄个一清二楚的心情对他说,“您可记得,不是您向我要求,请我们今晚来的吗?”
没有一个动作,没有一点声音能透露出德·夏吕斯先生听到了我的问题。看到这种情景,我又重复了一遍我的问题,就像外交家或那些闹了别扭的年轻人一样,他们不厌其烦地要得到对方的澄清,但是毫无用处,对方就是下定决心不予以澄清。德·夏吕斯先生并不给我进一步的答复。我仿佛看见他的双唇上掠过一丝冷笑,那是居高临下品评别人的性格和所受教育的人发出的冷笑。
既然他拒绝给予任何解释,我便尝试自己作出解释,结果我在数种解释之间犹疑不决,哪一种解释都不能算是合情合理。可能他想不起来了,或者是我将他今天上午对我说的话理解错了……更可能的是,由于傲慢,他不愿意显出自己曾极力吸引他蔑视的人的样子,而宁愿将他们到来的主动推到他们自己头上。如果是这样,既然他蔑视我们,那为什么他又非要我们来不可呢,或者更正确地说,他非要我外祖母来不可呢?因为整个晚上,他只跟我外祖母一个人讲话,而没有跟我讲过一次话。他藏身在外祖母和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身后,好像他在包厢里头一样,他与她们极其热烈地谈着,只是有时将他那洞察一切的双眼,探究的目光,停驻在我的脸上。看他那一本正经和专心致志的劲头,似乎我的脸是一部难以辨识的手稿。
显然,如果没有这双眼睛,德·夏吕斯先生的面庞与许多美男子的面庞会十分相像。圣卢后来与我谈起其他的盖尔芒特家人时,对我说:“当然,我舅舅巴拉麦德那种从头到脚、直到指甲尖的大老爷派头,家族派头,他们是没有的!”他这么说也就肯定了,贵族的家族派头和贵族特点,毫无神秘和新鲜之处,而是由这些成分组成的。我能够毫无困难地分辨出这些因素,而且不感到有什么特别感想,我应该感到我的某一幻想破灭了。
但是这张面孔,薄薄的一层粉赋予它舞台上面孔的某些外表,德·夏吕斯先生将其表情封闭得再严实也没有用。双眼好比一条缝隙,好比一处枪眼,只有这个他无法堵上。别人从与他所占据的不同角度出发,通过这条缝隙和这处枪眼,感到骤然被某种内部装置的交叉反光映住了。看来这内部装置丝毫不能令人放心,甚至对于虽然并非这装置的绝对主人却自身携带着它的那个人也是如此。他本人处于不稳定平衡状态,随时有垮台的危险。这双眼睛的表情谨慎而又时刻惴惴不安,带着全部倦意,对面部造成的后果,便是眼睛周围形成一个下缘很低的大黑眼圈。不论组合、修饰得如何好,都会使你想到这是一个隐姓埋名的人,是一个有钱有势的人身处险境的化装,或者根本不是什么有钱有势的人,而只是一个危险而又悲剧性的人物。当我上午在游乐场附近见到德·夏吕斯先生时,对我来说,一桩秘密已将他的目光变成了谜,而其它男子身上是没有这种秘密的。我真想渗透这桩秘密。但是依我现在所知的他的亲属关系,我再也无法相信这是偷儿的目光;依我所听到的他之谈话,我再也无法相信这是疯子的目光。他之所以对我那样冷淡,而对我外祖母那样和蔼可亲,大概并非来自个人的好恶,而是一般说来,他对女人怀着多少好意,谈论女人的缺点时一般也带着极大的宽容,他对男人,尤其是年轻人,就怀着多大的深仇大恨,这种仇恨使人想到某些厌恶女人的男人对女性的仇恨,他们家族中抑或圣卢的亲密好友中有两、三个小白脸,圣卢偶然提到他们的名字时,德·夏吕斯先生便说道:
“这些坏蛋!”表情凶猛,与他惯常的冷淡形成鲜明对照。我明白了,他特别谴责今日之青年人的,便是他们太女人腔。
“这是地地道道的婆婆妈妈!”他常常怀着轻蔑说。
但是与他希望的一个男子应该过的日子相比,还有什么样的生活不会显得女人气呢?他一向认为这种生活劲头不足,男子气概不足(他本人在徒步旅行中,疾走了几小时之后,身上热呼呼地便跳进冰冷的河水中)。他甚至不能容忍一个男子戴戒指。
但这种对大丈夫气概的固有之见并不妨碍他具有非常细腻敏感的长处。
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请他给我外祖母描写一个德·维尼夫人住过的一座城堡,同时加上一句话,说与那个令人厌烦的德·格里尼昂夫人分离,塞维尼夫人那么伤心,她本人觉得这无非是文学上的夸张而已。
“相反,我觉得没有比这个更真实的了,”他回答道,“再说,那个时代,这种情感人们是很能理解的。拉封丹笔下莫诺莫塔帕的居民梦中看见自己的朋友有些悲伤,便奔至他的家中。一只鸽子最大的痛苦就是另一只鸽子不在自己身边①。婶婶,您大概会觉得这也和塞维尼夫人迫不及待要与她女儿单独相聚一样是夸张吧!她离开自己女儿时,说的那些话多好啊!——‘这次分别使我内心痛苦,我像肉体痛苦一样感觉到它。在分别中,人们对时间很大方,人们在渴望的时间中前进。’”②
……………………
①(前)见拉封丹寓言《两个朋友》和《两只鸽子》。
②普氏在这里将塞维尼夫人致格里尼昂夫人的两封信混在一起了。1671年2月18日函为:“这次分别使我内心痛苦,我像感觉到肉体痛苦一样感觉到它。”1689年1月10日函为:“在分别中再不是这样,人们丝毫不考虑这些,有时甚至向前推,人们希望:在渴望中时间过得快。人们对一天长的时光很大方,谁愿意要就送给谁。”
我外祖母听到别人用与她自己完全相同的方式谈到这些书信,真是心花怒放。一个男子能够对这些书信理解得如此之妙,她惊讶不已。她觉得德·夏吕斯先生真像女性一样情感高尚而细腻。后来我们两人单独在一起谈起他的时候,我们说他肯定受过一位女子深刻的影响,或者他的母亲,或是晚些时候他的女儿,如果他有子女的话。我想起圣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