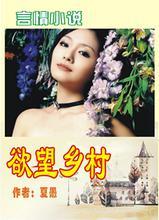望乡-第1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下岛最北端的二江,隔着早崎海峡与岛原半岛距离最近。如果去那儿看看,说不定会有些收获。即使没线索,至少看看木下邦的家乡也好嘛。
这种愿望一天比一天迫切,数日后的一天我又外出旅行了。我早已忘记上次旅行回来时下的决心,向二江出发了。
我不想途经大江,于是从崎津乘公共汽车经过基督教传教时代天草学林所在地的一町田向本波市方向进发,途经下田温泉又北上到二江。由于对当地的公共汽车不大熟悉,我换错了车,到富冈已是黄昏了。
听说还有去二江的公共汽车,可是到那里肯定是夜里了,又不知要找的人在哪里,我决定在富同这数得着的观光地住一夜。在汽车站的礼品店我拜托店主告诉我比较老的旅馆,他介绍给我一家冈野屋旅馆,我偶然发现那里林芙美子在昭和二十五年住过,她把在那里的见闻写到《天草滩》这篇小说里,因此富冈建有林芙美子的文学碑。
在冈野旅馆住下,吃过晚饭后《天草滩》里提到过的盲女——女店主前来聊天,她说我现在住的这间屋是林芙美子住过的,还保持着原样,还絮絮叨叨地表达了给林芙美子建文学碑的苦心,断断续续地讲林芙美子来此地的旧事。等她的话告一段落之后,她拿出一本纪念册和砚台箱,她说凡来她旅馆住宿的人她都让留言,写什么,画什么都随便。
我不好推辞,只好拿起笔。反正旅店女主人看不见,我写了一句话,记得好像是“来到满是石块的天草岛,不由得想到这石块像是南洋姐的泪凝结成的”。她把纪念册收起来拿走了。过了一会儿又来到我的房间给我续茶,问我:“您是研究南洋姐的学者吧!”可能她把那本纪念册拿到楼下,请人念了我写的题词。
我说我不懂什么研究不研究的,我亲戚中有这种人,所以我对这事很关心。然后我若无其事地问如果当地有这样的人我倒想见见,于是女店主一屁股坐下来又说了一阵子海外妓女的事儿,当她知道我第二天要到二江去找阿邦的亲属时就说:“我妹夫原来在二江小学教书,说过他教过的女孩子有去南洋的。后来他改行在富冈村公所观光科干活,尽挖掘一些老年间的追事奇闻,可能会知道阿邦,明早问问他吧!”她是如此地热情,这几年在东京我好久没遇见这种热心人了。我心里一高兴就睡着了。第二天醒来时,她的妹夫已经来到旅馆等我了。
我感到很不安,早早地吃罢饭,跟着女店主介绍的佐野光雄老人向二江出发了。在二江佐野一下公共汽车就进了一家被褥商店,那里的老板曾是他的学生。经过多方询问,我们打听到了木炭铺的水上良太和渔民山口猪吉以前在北婆罗洲种过马尼拉麻。
我们赶紧去访问水上良太。我一提起木下邦的名字,他便说:“阿邦比亲生父母还关照我,我去山打根也是阿邦劝我去的,说那地方好。”脸上露出了非同一般的表情,像见了什么稀罕物件似的。我问他是否“阿邦有一个养女”,他表示记不起名字来了,我提醒他说:“她养女叫阿作,现在她住在哪里?”水上良太佩服地说:“你知道得可真多啊!”然后他说:“阿作二十年前就死了,她还有个女儿,但是不知现在在哪里。”我们接着访问了山口猪吉,他也讲不出更多的事。
佐野听了两个人的回答后,觉得得不到更好的消息会有损他这个带路人的信誉,就带我继续走访,又打听了两家去过南洋的人,但只能得到与前边几家差不多的消息。离开富同时是早晨八点,现在已是下午三点了,时候不早了,该回去了。
阿崎婆曾说过,一般在南洋生活的日本人都愿意回日本,但阿邦却始终没这个打算。正因为如此。不打算死后在故乡造墓,早在生前在山打根就修建了自己的墓,她这种行为的原因是不是潜藏在故乡的村子里呢?如果想象一下的话,阿邦年轻时在二江村是不是有过改变她一生的事件,这件事也影响了她赴山打根后决定经营妓院?决定了她对妓女的态度与男老板不同?他们是那么苛刻薄情,而她则富于人情味。过去我曾想,如果访问二江村的话,或许能解开这个疑团——我内心是这么希冀的。可是不用说外来的我,连天草当地人的佐野尽全力询问,还是找不到阿邦亲属的下落,可能她的亲属没有人住在二江了。如果那样的话,正如我出门时所想的一样,看看阿邦的老家就不错了。
我把这想法告诉佐野,说我想回富冈了,佐野点了点头,说:“真遗憾,只能这么办了。”然后说在汽车没来之前,他想顺便去看一位老熟人,问我能否跟他一起去。我当然同意。为了抄近道,我们从海边沙滩上走,半路上遇见一个到海边倒垃圾的五十岁上下的主妇,她叫住了佐野:“您是老师吧?”
佐野一下子窘住了,注视了那妇女好半天,好像想起来她幼小时的样子,说:“你是当班长的公子吧?”那妇人高兴地说:“几十年了,老师您还记得我呀!”她好容易见到老师,邀请我们到她家喝口茶。佐野欣然接受了,我也随着去了。他们谈的话题全是佐野的学生,我一个也不认识,自然不感兴趣。
他们的交谈告一段落后,那女人问:“先生,您来二江干什么来啦?”佐野介绍了我的事,说我在找木下作和她女儿岭生,可是听说两人都死了,只好空手而归。她“噗哧”一声笑了出来。我们迷惑不解地盯着她看,她更觉可笑了,边笑边说:“谁说阿作和岭生死了,阿作八十多岁了,身体硬朗着呢!岭生身体也挺好的。”
我一下子没有马上理解她的话,过了一会儿待我明白过来不禁浑身发热。找富美那会儿认为富美活着是板上钉钉的事,结果却那么不好,这次正相反,那么多人都说阿作、岭生不在了,却又听说她们都活着。
佐野也像是不相信她的话,说:“问谁谁都说她们死了,无论你怎么说她们活着,我也不能马上相信。”他边说边瞧我,像是征求我同意似的。于是那女人又自信地笑了笑:“那我带你们去她家吧!阿作和岭生住的离这里很近,也就隔两条街。”。她穿上草鞋,给我们带路,一路走得飞快。
正像佐野先生的学生——那位主妇所言,木下阿作与她的女儿岭生均健在;她的家就在我们下车的公共汽车站附近,是个大农舍,这家人姓木村,是岭生的婆家,母亲阿作也跟着来这里生活。
在大门口的名牌上写着木村一郎的名字,佐野一个人自言自语地说:“呀,这是木村老师的家呀!”随着主妇的叫门声,从里边出来了一个六十岁的老人,他一眼看见佐野就大声地说:“欢迎欢迎,少见啊!”一郎从前在中学长期担任社会课的老师,与佐野老师是旧知,退休后务农。
我的访问变成了佐野和木村的叙旧,一会儿啤酒就端上了桌,对我来说这种相会让我更安心。佐野向他家人介绍了我,我对一郎的夫人岭生说,我是山川崎的亲戚,阿崎婆本人晕车来不了,我只能替她来了。这么一说,她就把住在另一处的阿作请过来了。
阿作只是腰有些弯,连拐杖都不用,一个人走过来的。她个头矮小,人也干练。岭生介绍说她已经八十六岁,几个月前耳朵忽然不好使了,其它都还好。她向我问候,遣词用句都很恰如其分,显得十分有教养,我感到她是一个小心谨慎、十分懂礼貌的人。
啊,这个老太太就是阿作吗?这个人的母亲就是在南洋善待妓女的木下邦,虽说是养女,她也是这个人世上木下邦的唯一亲人了。除了这位八十六岁的老妪外,世上再没有人了解木下邦的生平和为人了。我曾一度死了心,认为再也遇不见她了,然而却相逢了。对于佐野先生等引我们相见的天草人,我怀着无限感激的心情。
我想从阿作那里把阿邦的事打听得一清二楚,可是在一旁与佐野聊天的一郎是天草的知识分子,阿作本人也有一定教养,不好直截了当地问阿邦开妓院的事。于是,我对这一点问得很委婉,只是请阿作谈谈木下邦的生平。我把她谈的归纳如下。在读这段回忆文字之前,想提醒读者注意的是,阿作对阿邦在山打根经营的八号馆绝对不使用妓院这个称呼,而始终把它叫作“咖啡屋”。
听到阿崎这名字好让我怀念她啊!她对我母亲照顾得可真周到啊,都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啦。你来我家看我,真谢谢啦。我早就想有朝一日当面道谢,你这一来,了却了我一桩心事。从前听我母亲说她老家是崎津的,但是我知道得不确切,知道她名字叫阿崎,姓什么不知道。这件事一直作为一件没完成的事沉甸甸地压在我心上,你是她亲戚代替她来看我,我的心情就像是拨开乌云见太阳一般。
你知道我母亲?——不会吧?我妈在婆罗洲去世了,我知道你不会直接地见过她的面,你太年轻了。阿崎那儿可能有我母亲照片,你看见过。
你说阿崎二战结束返回祖国时什么东西都没带回来?她自己年轻时的照片、我母亲的照片全丢了?是吗?——那么,您就看看那门上挂的照片吧!是不是像个男人,那就是我母亲木下邦。
记不清拍这照片是哪年了,可能是明治末年吧!那是她六十大寿,日本人叫“还历”。妈妈说:“再不愿当女人了,我更年期也过了,今后做个男人吧!”她把头发一下子剪成男式,穿男装照了个纪念照以表决心。你看她穿着和服外褂和男式裙裤、白袜子、桌上放着丝帽子,怎么看怎么像个男人,我母亲就是这么一个决断的人。
我母亲的事阿崎知道得更清楚,阿崎和你讲过吧,我不是她亲生女儿,是养女,她晚年的时候我们分着过的。伺候她养老送终的是阿崎。——可是,我母亲去山打根之前的事我知道得倒不少。
我小时候听我妈说她是嘉永二年生人。她家住在二江村,离海很远,是一个贫穷农民家庭。我母亲出生前一年,天草的农民抵抗地方官发起了暴动,长崎港美国、英国的军舰首次进港,是动荡的年代。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不知道,母亲十几岁的时候一个人去了东京,那时还叫江户。出走到东京去是什么原因,我不知道,到了东京干什么活儿我也不知道。十五岁时回二江一次,以后又去东京了,这次去是受到住在横滨的英国人的照顾了。这个英国人是来日本教日本人浦铁路的,每月从政府领好几千日元的工资,生活可好呢。明治十七、八年结束工作离开日本回国。忘记他叫什么名字了。
我母亲受这英国人的关照,不愁吃,不愁穿,有女佣人,有厨子,家务活儿有下人干。为了打发时光,开始学日本画,我父亲就是教她画画儿的老师。
我父亲叫宫田,原先是幕府的侍臣,明治维新以后武士阶层取消了俸禄,家里一大群孩子日子过不下去了,为养家糊口把当侍臣时学会的日本画技术拿出来,当个教画先生。不知是什么缘故,他的学生不是日本人而是租界的英美人。可是,教画需要铺开画布,我们家地方狭窄,孩子多,于是我父亲就上门去教。
我是明治十五年生的,虚岁四岁的时候是明治十八年吧,不知是阴历七月十五还是年根上,我养母带礼物访问了我家。不知是她看我宫田家穷、孩子多同情我们,还是她指靠的英国人回国了,她太孤单,或许因她三十五、六岁还没有孩子,总之她收我做了养女。宫田家我爸给我起的名字叫阿密,养母叫我阿作、阿作的。现在只有亲戚才知道我的本名。
我和养母一起在横滨生活到我九岁那年。小时候的生活我还记得。在横滨的时候生活可好了,浑身上下穿的都是丝绸和服,用茶色底子带白色斑点的友禅丝织品裁和服,她像打扮洋娃娃似地打扮我。英国人离开日本的时候给养母留下好多钱,我们才能过上那样的生活。
我九岁的时候,养母把我寄养在她二江的娘家,一个人上南洋去了。那是明治二十二年,我母亲已经过四十岁了。她为什么决心上南洋去,我不知道。后来我想想养母所做所为,推测因她长期与英国人生活在横滨有关。横滨是贸易港,她觉得和南洋人做买卖有意思吧。
母亲先购一批和服去了新加坡,那里已有不少日本人,他们开杂货铺,开技院。母亲没有立足之地。后来母亲听说山打根几乎还没去日本人,将来肯定会开发,就立即赶到山打根。
在去山打根的船上母亲认识了一个广东长大的中国人,他穷得光着膀子。母亲对他说:“我到了山打根把和服卖出去,用那钱经营咖啡屋。”母亲长期和英国人一起生活,英语很流利,那中国人也懂英语,这样才能交流。于是那个中国人说他在山打根有朋友,到时候让那朋友给我母亲批发些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