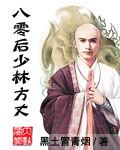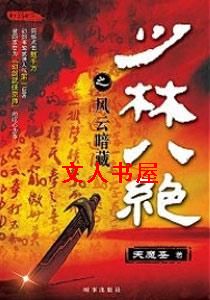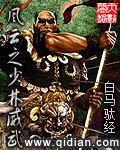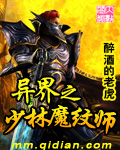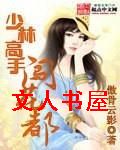少林方丈-第7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杨坚眼下虽远在东南戍守,却很快便闻知了朝中齐王一门被诛的消息。
这是他意料之中的事。
当他接到朝廷晋他为大司马之职并召他回京的诏敕后,并未感到太大的惊喜。因为,他早已预感到:新帝登基之后,除了要诛杀一大帮子当年的异己之外,接下来,恐怕还会相继换掉一大帮子的朝中大臣。
自己,郑译和于智的晋拔,仅仅只是开始。
然而,此时的满朝文武,包括皇室诸王要臣,恐怕却是人人自危、个个惶恐。
杨坚略估算了一番:时下之大周,内有自太祖以下宇文氏皇族宗亲数十位的诸王和国公;外有尉迟、长孙、达奚、韦孝宽、李虎、李弼、于翼等几大家族的柱国将军,只怕这个新帝会统统过滤一遍往日的恩恩怨怨。
要紧的是,新帝当年的敌党,恰好多是杨坚的敌党。自己此时回京并担当军国要职,宣帝近期所有的杀伐惩处或是升迁削减,他人定然会认定一切皆是自己在背后操纵的结果。
如此下去,过不了多久,群臣对新帝奈何不得,而他杨坚却会成为群臣们一致嫉恨和攻击的靶子。
既要奉诏回京,又要避过眼下的政事风潮,不致引火烧身,还不能让宣帝心生疑惑,这实在是难坏了他。
当载着当朝皇后之父、新任大司马、上柱国大将军杨坚的车辇隆隆行至京城隋公府时,已经是月上柳梢时分了。
当晚,杨坚与夫人迦罗通宵未眠,窃窃私议直到天快亮时,终于商定出一样既可避开一时嫌疑,又足以自救的一计来……
*吕梁——北周地名,在今江苏一带。
第十五部分
少林方丈(第三十三章)(1)
宣帝闻说半晌无语:看来,这个王轨果然忠心耿直不同于齐王,齐王是恨怒而死;而王轨直到临死之前,仍旧平静谢恩、甘心受死……
仇敌尽除,宣帝望着外面空寂的廊庑台阁,惚惚然竟若有所失……
杨坚第二天便入宫觐见宣帝。
君臣二人互道了辛苦并寒喧过后,穿戴甚厚的杨坚强抑不住地不时吼吼咳喘一阵。宣帝见杨坚脸色腊黄、鼻塞涕流的模样,忙问是不是路上着了凉?便催他先回府休息,又令宫监去传御医,命到隋公府诊治,又反复嘱咐杨坚回府后先安心养病,待身子康复后再上朝复命。
杨坚赶忙谢恩出宫。
孰知回府后,竟一头病倒在床,再起不来身了。
因杨坚此番回京后更不比往日,既为后父、又是新晋的朝廷大司马,赫赫新贵,分明是宣帝的首要辅臣。此时满朝文武都得知他回京途中患了重伤风,眼下在府中卧床不起的实情。
众人闻讯争先恐后地一齐前来探看,一时间车马盈门,弄得隋公府比前年娶小儿子媳妇那会儿还热闹。
独孤氏和往日一样谦和亲切,一面忙着令下人上果点、泡茶,一面却以杨坚发热畏寒、病症转重为由,也不让人近前与杨坚说话,只让前来探访的客人蹑手蹑脚地隔着幔子往里打量:众人见杨坚蒙着厚厚的被子,屋内拢着旺旺的大火盆子。一旁有一个小炭炉内正煎着汤药,满屋子都飘着浓浓的药香气。里面只有一个丫头一声不响地守在药锅旁。
众人虽不得与杨坚搭话问候,却清知独孤氏在隋公府是大当家的,便纷纷嘱咐了一番,说了会儿请独孤氏好好照顾病人等闲话,然后才依依不舍地先后离去。
如此,总算过了一段清静悠闲的日子。
宣帝当初下山时,慧忍就曾事先交待,宣帝遇毒后内伤尚未痊愈,因而一是不可过度操劳,二是要潜心修复;如今,宣帝万不料忽遭父皇崩殁,悲痛之外,又加上继位以来军国诸事的万机繁劳,遂骤然引发了五内迸乱。往日郁积在内的一些余毒竟致重新侵入血脉。如此,因内热过盛而灼伤了肝脾,致使性情也一反往日的温软,为人处事竟是一天比一天急躁易怒起来。
有时冷静下来,宣帝念及齐王一家老少数口之死时,毕竟同为宇文氏骨肉,便会有些不安袭上心来;然而再忆及当年所受的诸般屈辱,一时又咬牙切齿起来。遂连想到齐王虽除,然而齐王的头号死党郯国公王轨眼下却仍旧拥兵驻守一方,但又觉得忧恐不安起来。
郑译道:“陛下,莫非还有什么不得排解的烦忧么?”
宣帝叹气道:“往日,乌丸轨虽屡屡加害于朕,可他毕竟为大周国家朝廷屡建奇功。朕若为私仇杀他,着实顾虑他毕竟是高祖多年的忠臣,恐因此遭致物议。可是,当年他极尽陷害朕之诸事,朕即令不杀他,他也未必会感念朕的宽厚。只怕终究还会怨而生变,故此烦恼。”
郑译道:“陛下,臣也一向佩服郯国公的雄才奇略。可是若说他是大周的忠臣良弼和百战功勋,臣却不以为然。”
“哦?此话怎讲?”宣帝疑惑地望着郑译。
“陛下,当年乌丸轨与南陈八万水陆大军彭城之战中,广贴露布,收购民间千具铁轮万丈铁索,贯锁沉水、截断清流,以奇谋陷南朝常胜将军吴明彻数万兵马尽没清水,何其奇才大略啊!可是遥想吐谷浑之战中,有着如此雄才奇略的乌丸大将军,宇文孝伯同受先皇之命,总理一切兵事的进退,怎么近万大军在大漠延耽数月,为何竟会不见敌国吐族一兵一骑而落个无功返国的?”郑译说。
宣帝道:“吐谷浑之挫,怪朕初出茅庐,既不知轻重,也不谙将兵之策。”
郑译道:“若说陛下不知将兵,时日不久后,陛下再次西北征讨,闻听身边的左右辅将也不过是根本就不曾知名的微职将军,为何竟能屡屡大捷?陛下,当年西吐之辱,果然因郑某在营中演练阵曲,才导致的西伐大军不得胜敌吗?”
宣帝挥挥手:“与郑大夫无关,是朕阵前轻敌之故。”
“陛下,非也!当年吐谷浑一战无功而返,臣等虽有轻敌之责,但乌丸轨他们却把臣与他个人之间的恩怨冲突,转怒于陛下。当年之事,乌丸轨不止有辱圣命,更是误国欺君!忠良之臣,怎么会做有意使战事无功而返,且加罪幼主,并不惜以个人挟私之轻,延误社稷江山之重,有愧先祖重托期望之事来?”
郑译的话骤然惊醒了武帝!
往日宣帝也时常思量此事:自己率大军西讨,军驻数月无功而返,自己被父皇当众罚杖、身受屈辱其实也算不得什么。要紧的是,乌丸轨和孝伯二人身为朝廷重臣、高祖左右亲腹,受高祖重托和朝廷大任,身兼国家江山和辅佐幼主之要命,辅佐自己第一次临敌国、历兵事、历武功,末了竟因与郑译的个人冲突,误兵事而陷幼主,单此一条,其实便是万死不赦的欺君渎职大罪了!
旧日的屈辱和创痛重新沉浮,宣帝的脸渐渐苍白起来,眼中开始浮起阴郁之火,却沉默不语着。
“捋须之事,陛下可曾听说过?”郑译又问。
“捋须?捋什么须?”宣帝不解地望着郑译。
“臣近日闻听,当年陛下在御苑寿宴左右大臣,乌丸轨借酒醉移至先祖身边,当着众臣的面捋着先祖的胡须说,‘咳!可爱好老公,只恨后嗣太弱啊’。此事,莫非陛下未曾听说?”
少林方丈(第三十三章)(2)
宣帝的脸开始青紫起来:“竟有此事?”
“当时有好几位老臣在场,臣岂敢信口胡言?”
“奸臣!竟敢如此猖獗!若非父皇当年对朕父子情深,朕哪里还有今天?”宣帝抖着嘴唇说。
自诛杀齐王之后,宣帝其实已不想再诛杀他人了。眼下之大周,西北部落对中夏年年侵扰掠袭,南朝陈国也一直伺机以待。王轨、神举和孝伯个个文韬武略、智勇双全,确是大周不可多得的龙虎之将。然而,蓦然记起旧事,令他禁不住重新涌起尽除宿敌的心思……
郑译继续说:“陛下固然有惜才之心,只怕那郯国公未必珍重陛下的这份宽厚。自古以来,哪一朝的江山社稷不是断送在所谓的旷世武勋手中?他们功大盖主,又原为党朋,始终于陛下心存嫉恨,臣只怕,早晚会从他们那里生出事端来!”
宣帝沉吟道:“如此,即令朕不杀乌丸轨,乌丸轨迟早也必生反变?”
郑译道:“陛下,臣以为,治国用臣,长久之计宁可用平凡之辈,上德之人;决不用奇略之才,下德之人;陛下若存妇人之仁,恐怕酿成大患。”
宣帝默默无语,当晚,整整碾转反侧了大半夜也未曾入睡……
第二天下朝后,令郑译召几位内史一齐进殿,当众诏布上大夫王轨诸般罪名,并命内史杜虔信等人立即拟敕:即刻诏敕斩杀乌丸轨。
孰知,中大夫元岩、岩复继和东宫早年的侍读颜之仪等人一闻听宣帝要拟诏诛杀王轨,俱都大惊失色,众人一齐叩跪在地,反复述说眼下大周强邻四敌、南北未一,南朝陈国几欲进犯,唯因有王轨把守而不敢轻动。恳求谏劝宣帝不可妄杀忠良、冷了人心。
岩复继更是垂泪脱巾、三拜三进,反复叩首恳求宣帝饶过王轨。
宣帝因一向信任这几位朝臣,故而才召来拟敕的。如今见众人齐齐都为王轨说话,一时郁躁难遏,不觉大怒:“朕当你们是多年的忠良辅弼,哪里知道,原来你们一个个竟然全是他的同党!”
岩复继叩地再拜:“陛下,臣等决非郯国公同党。臣等恐陛下滥诛功臣,失天下众望啊!”
颜正仪也劝谏道:“陛下若对郯国公有疑虑之处,可先下诏削除其官职,令其反省,以观后效。”
宣帝忍耐不住,便将当年王轨总领兵事进退,西征吐谷浑大军无功而退之事叙述了一番。
颜之仪叩头释疑道:“陛下,悬师西征,一入他国,便呈凶险四伏、生死难料之势。吐谷浑士卒一向骁勇善战,狡诈多变。当时臣也在军中,确时兵机不佳。郯国公辅佐太子深入敌境,身兼万钧重担。以当时之势,兵事胜败为小,储君安危事大。若贸然出兵,一旦有何闪失,即令砍掉十个、百个吐谷浑可汗吕夸的头,又岂抵得我大周储君之万一?”
岩复继道:“陛下,颜大夫所言有理。臣以为,当年郯国公辅佐太子西出无功而返,肯定有他的难言之隐。陛下何不过问清楚再做计较?”
宣帝见他竟为王轨如此辩解,越发气怒难忍了!一时五内躁热,暴怒之下,竟叱令内侍们将岩复继打出殿去。又气急败坏地喝令杜虔信立即拟敕,并命他带人速到徐州传旨并监斩王轨。
杜虔信原本胆小,见宣帝动怒,不敢再抗旨拖延,急忙依命拟旨并带人出京。
镇守徐州一方的王轨闻听新帝登基不久,郑译便官复原职的消息后,当即预感到祸事不远了。果然,不久便闻听齐王父子数人遭满门抄斩,连带安邑公等人也被诛杀的消息。
他料知,接下来轮到自己了。
他从容地安排好了公私诸事后,叫来左右心腹交待:“当初,我在高祖面前曾屡言太子之过。本心仍是为了大周的江山社稷所图。时至今日,祸变可知。本州控带淮南,近接强寇,若欲保全身家,实在易如反掌。但忠义大节乃王氏传家立世之本。况我受先帝厚恩,志在效死,怎敢因获罪嗣主而背叛先朝?今只有坐以待毙。望千载之后,功罪评说,苍天可鉴我心。我别无所求,死后只请照料好京城我的老母幼儿……”言罢,长泪不禁。
果然,王轨刚刚交待完后事不几日,杜虔信便带着圣旨和侍卫,赶到徐州传诏并赐郯国公王轨一死。
杜虔信监斩已毕、回京复命时,对陛下讲述上大夫王轨死前跪地谢恩、平静就死,并言说王轨死前之言,“吾受先帝厚恩,情愿伴侍先帝在天龙辇。臣虽知死之将近,而忠义之节并未违逆……”
宣帝闻说半晌无语!看来,这个王轨果然不同于齐王,齐王是恨怒而死;而这个王轨,直到临死之前,仍旧能平静谢恩,甘心受死……
如此,原打算决意要斩草除根、一并斩尽王轨满门子孙的念因此而打消了……
王轨被诛后,宣帝在宫中诏见了被冷落了好些日子的宇文孝伯。孝伯进殿后,宣帝冷冷地打量了孝伯半晌,而后先声夺势地突然质问:“公卿,你既然早已得知齐王有谋反之意,为何隐匿不报?”
孝伯闻听宣帝如此质问,清知齐王、王轨之后就该轮到自己了,然而却并无一点惧色,一面直言道:“陛下,齐王和郯国公效忠社稷,可惜竟为郑译、于智等群小陷害。臣受先帝嘱托,未能进谏劝止,有负先帝之托。陛下若欲赐臣死罪,臣甘心受死,决无怨言。”
少林方丈(第三十三章)(3)
其实,宣帝此番诏见孝伯的本意,原不过想敲山震虎一番,若孝伯知道惊怵,或是能为自己辩白一番,或是肯稍稍示弱的话,宣帝便会念在父皇去后,他曾一片忠心辅佐自己的份儿上,有意放过他去。
孰知,这个孝伯竟是如此的不识相!不仅不肯为自己辩解几句,反倒说什么“甘心受死”,这下竟弄得宣帝自己也无法下台了。
宣帝原是自尊极强,且是恩怨必报的性情,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