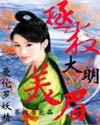大明金主-第21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收集和新市场开拓两个部分,前者顾水生已经布了不少线,这回也交到了他手上。至于市场开拓,他是第一批有家客栈的店长,在这上面比从未站过柜台的顾水生还要顺手一些。
*
*
求推荐票,求月票~!
*
PS:求各种支援~!
三五三章送米
传统商行之中,有规矩没制度。规矩也往往因东家、掌柜而异。基于这种情况,东家的确不需要太多人手,反正伙计能听话干活,大方向不犯错就行了。
徐元佐却是个淡化规矩强调制度的人,为了保证制度推广和坚持,人员配置要求就很高,如果质量实在达不到,只能通过数量去弥补。
即便在二十一世纪,这两种企业仍旧并存,从管理学而言各有优缺点。对于中小微型企业来说,规矩显然比制度更灵活,更贴合市场,更能提高生存指数。一旦企业上了规模,制度的重要性就会越来越明显。因为公司不再以生存为目标,而是以发展为核心,所以即便制度化管理会带来一定的程序僵化、思维固化,但是抗风险能力也会随之提高。
徐元佐从未担心过徐氏集团的生存问题。即便不说历史上徐家与国同休戚,光看眼下的环境,徐家也没那么容易倒塌。
为了能够在万历“大爆炸”时代获得最大的利益,徐元佐一开始就是冲着“发展”去的。别看手下这些同学才十六七岁,等再过两年,二十啷当岁正是年富力强的年纪,又有三五年工作经验和制度熏染,派出去就是能干活的好苗子。
对于这个时代的伙计而言,规矩就是贴出来的标语,有一句是一句;制度却是一个体系化,非但要理解,还要遵守。这对从业人员的素养要求略高,绝非文盲能够理解的——如果哪个文盲能够天才到无师自通,或是一目了然,那他在徐元佐的教育体系中肯定能以最快的速度摆脱“文盲”的帽子。
为了打破知识禁锢,降低教育门槛,徐元佐非但坚定地让当初夏圩徐园的学习会继续下去,还从各个方面刺激知识的普及和提高。只有把水潭挖成湖泊,才能打到更多的渔获。若是能够挖成大海,说不定还能打条龙上来呢。这方面投资,绝对是物超所值的。而且徐阁老将此视之为养望。如今眼看着徐元春能够入仕,无论如何也得在家乡给他打造一个基本盘,所以这养望是势在必行的。
段兴学从苏州府长洲县探亲回来,首先去府学销假。他今年没有打算参加乡试。所以缺的月考都得补上,幸好平日也有存稿,压力还不算太大。想想同为府学学生的徐元佐,常年累月地报病假,别说平日功课。就连月考都不参加,完全不把学校的规矩放在心上——人与人的差距怎么就那么大!
段兴学原也有心要在科场中搏个头脸,不过一步步走来,又看了今年乡试的程墨,只觉得自己前途渺茫。再看看同样学富五车的徐元佐,竟然痴迷于末业,更是对他科举出头的信念造成了打击。作为小康人家出身的子弟,段兴学每每想起徐元佐指派壮士清扫山贼土匪,难免羡慕他那指挥若定的风采。
“戒子!你回来了!”
段兴学一进府学学宫,就碰到了同学。连忙站定行礼。
“快去领米。”那同学笑道:“今日是最后一日了。”
“今日发廪讫?”段兴学也是一等廪生,每月有朝廷发的廪给,虽然按照典章,廪生一日有一升米的补助。虽然没有副食品可以填胃,但有这每天一升米打底,总算那些没有田宅的秀才相公不至于饿死——前提是他能在岁、科二试中获得好成绩。只吃廪讫的秀才自然会很穷,若是不出卖自己两石的税赋优免,便是名副其实的穷秀才。
“并非廪讫,乃是广济会发的助学金——折成米发,人给五斗。”同学十分兴奋。
“五斗米?”段兴学小康之家。对于五斗米并没有多大感触。不过他看同学那么兴奋,知道家境贫寒的子弟是很在意的。单纯靠每天一升的廪米,连奉养父母都不够,若是上有老下有小。那基本上只能勉强不饿死。
更何况廪生名额有限,增生和附生可是一点收入都没有的。
那位兴奋的同学便是属于家境很一般的。他拉着段兴学同去,仍旧不忘普及这些日子郡城的新闻。
“听说小财神去了一趟了京师,回来便开始大发善心了。”那位同学道:“非但在府县学校发助学金,还给全县的社学、蒙学都送了助粮,按人头每人三斗。”
段兴学面带微笑。心中暗道:如今斗米不过二三十钱,统共也就百钱上下,便将人心都收买了。他刚兴起这个念头,又觉得自己恐怕是犯了嫉妒心——学校同学固然不多,但是全县的蒙学、社学学子加起来就不是个小数目了。
“广济会的人说了,这回是按照人头五两银子算的,全部折成稻米发,发足为止。”那同学喜滋滋道:“下月还有呢!”
段兴学这回有些佩服徐元佐了,道:“这样算下来,岂不是要好几千两银子?”
“几千两恐怕还打不住呢。”那同学给段兴学算账,道:“若是全县有一千读书人,那就是五千两了。而每次童生试都有两三千人,便照两千算,那就是一万两银子。”
段兴学瞪大了眼睛:“徐家还真舍得!”
那位同学啧啧有声:“徐家果然不是玩虚的。他们捐了好几万亩地给广济会,显然是要彻底将收益都用在乡人身上啊。”
段兴学道:“这可真是做下了大功德。”
“老黄堂已经上报了南京,少不得要请朝廷赐下旌典。”
“唔,理所当然,这份义举不知能助多少学子脱离苦寒了。”段兴学又道:“其实家境若是尚可的人家,大可不用发……”他话未说完,却也发现有些不妥了。那位原本关系不好的同学脸上的笑容也渐渐发冷,再不如刚才那般亲热。
段兴学心中暗恼自己不会聊天:这样一说,难免不叫人误会这是徐家给的施舍。读书人面皮薄,自尊心甚强,真要说是给家境贫寒者的施舍,谁肯吃这米?就算实在无奈受人恩惠,恐怕也要和着眼泪吞下去。
*
*
求推荐票~求月票~!
*
PS:晚上还有一更~求各种支援~!
三五四学在四夷
徐元佐在辽东用米换鹿茸,赚得实在有些连自己都害怕。虽然他不相信天谴这儿回事,但考虑到徐阶教诲的“良知”,还是决定回到唐行之后,以广济会的名义向府县二学和全县四十八所社学捐款。
虽然他没有指望朝廷的嘉奖或者牌坊,但是捐款总额高达一万两,实在震惊了整个南直。非但府学学宫刻碑纪念,就连新任的浙江学台都题书嘉奖。海瑞更是特意作文派人送来,同样刻成了碑文,放在学宫和乡贤祠,恨不得送到徐阁老家里去。
徐阶是个不介意银子的人,但是这么大一笔数目仍旧让他有些心惊。养望归养望,但是遽然拿出这么大一笔银子做善事,风头鼎盛,实在叫人有些不踏实。不过既然家业打理都交给了徐元佐,而且家中资产还在持续增加,就没有干涉的道理。更何况徐诚拿了广济会的账目回家禀报,发现这笔银子是另外捐助的,想来是徐元佐在别处化缘得来,那就更没有干涉的理由了。
徐元佐最初是想直接发银子,却又担心这笔银子被人挪用,并不直接发到每个社学。更为了避免学生拿到银子,被家中没收,从而使得发银子完全变成了无意义的作秀活动,所以才将银两折成稻米分批以实物形式发放。
按照每人五两银子的总预算,每月一次发放,考虑到米价的涨跌,差不多可以发放一整年。用长达一年的时间来提醒学生:徐氏愿意为改善他们的学习生活会钞——至于日后如何处理与徐氏的关系,自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只是接受过这份礼物的人,无论走到哪里都吃徐家的嘴短,轻易批评华亭徐氏,难免被人视作白眼狼。
眼看过了九月,又要进入征收秋粮的时候了。
今年上海和崇明因为风灾略有歉收,不少田地被洪水淹没。不过华亭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田产与往年相平。徐家的田地因为雇佣了不少流民里的庄稼老手,带来了一些实用的异地手法,庄稼长势比之往年还要好些。
徐元佐虽然对农田不甚了解。但是充分利用每一寸土地的理念是有的。之前许多被弃之不顾的边角上也种了蓖麻、棉花、绿肥之类的经济作物。
其中叫人诧异的是蓖麻。这种传自天竺的作物在江南虽然不罕见,但是从来没人刻意去种植过。因为它的价值要等到工业化之后,才会显现出来——作为高级润滑油。
徐元佐刻意安排蓖麻种植,主要是为了榨油。虽然文科生不了解技术。但是印刷术总该有所涉猎。尤其是在涉及古籍版本的问题上,纸墨装帧都是绕不过去的关键点。如今的印刷墨料仍旧是水基墨,这就导致活字印刷术的质量远远不如雕版印刷。
报纸这种每天要刊行的文书,用雕版印刷成本实在太高,而且做工时间也太长。没人能够承受得起,即便通政司发的邸报也是使用活字印刷。别人都可以接受的色泽不匀、墨水透面等问题,徐元佐却实在难以忍受——他甚至只看《曲苑杂谭》的小样,那是手抄本。
就徐元佐所知,印刷的主流还是走雕版路线——后世的激光制版原理也是雕版印刷术。不过眼下自己要想做出有质量,又能控制成本的快消文本,活字印刷术总是逃不掉的。而性价比最高的,莫过于改进墨料,用油墨取代水墨。油墨用的油,便是以蓖麻油为上。这种工业用油粘度高。凝固点低,既耐严寒又耐高温。榨油之后的油饼中富含氮磷钾,用高温脱毒之后就是很不错的肥料。
蓖麻虽然不挑土质,房前屋后到处都可以栽培,但是吸肥力也强。加上江南还没有人刻意栽种蓖麻,在育种和田间管理上都缺乏经验,收获并不理想。好在徐元佐并不需要大量使用,今年的主要任务还是摸清性状,请药农帮忙看顾——蓖麻一直是作为药材被人所知的。
然后就是研究从木、煤之中制取炭黑,研究配方。当然。这事基本上也可以交给李腾去做。
徐元佐在唐行东山——难民营后面为李腾买了一块坡地,盖了一座三进的道观。
如今道观建筑已经起来了,不过订制的神像还没送到,也就没有开门接纳香客。至于李腾带着四个徒弟住在观里。实际上他也不打算对香客开放,那样会影响他“清修”和“炼丹”的时间。只是身为道士,有义务供奉三清圣像,这才占用了二进的正堂,观名也就成了很没特色的“三清观”。
徐元佐去三清观从来不坐马车或者肩舆,权当散步一样。带着棋妙,在罗振权或者甘成泽的陪同下就走过去了。每回他过去都要带点文稿,主要是两本书的草稿:《物理小识》和《初等数学》,至于化学这门高深的学问,徐元佐暂时还没想好该如何下手——当年他就没怎么及格过,如今更是基本上忘干净了。
李腾对于《物理小识》很感兴趣,而且贡献颇多。不过数学方面就不怎么吸引他的关注了,尤其对于徐元佐所谓的:万事万物可以由数学表达——这一论点颇有怀疑。当然,这也怪徐元佐,谁让他连圆锥体体积公式都忘了,还是李腾帮着研究了几天,方才总结出来,然后放水验证。
就在这种磕磕绊绊之中,徐元佐终于在某一天忍不住摔书了:“我决定了,派人去澳门!”
“澳门?”李腾很是疑惑,头回听说这个地名。
“唔,广东香山,那里有一群泰西葡萄牙国的人。”徐元佐道:“他们那边有一群景教教徒,在数学和物理上有些小造诣。”
李腾微微颌首:“物理对于工匠的确颇有用处,数学也有其精妙的地方,不过也不值得跑那么远去求教吧。”
“不光是工匠有用。”徐元佐大摇其头:“想春秋战国之世,百家并起,我们非但有道儒法家之教,也有墨农医家之术。这两类,前者是研究人组成的社会,夫子们琢磨的是如何让人幸福快乐地生活,如何让整个社会更加有秩序,更加和睦美满。虽然主张不同,主旨却是一致的。”
李腾点了点头,并不觉得意外。
“墨农医……其实主要是墨家的机关术和医家,钻研的是如何利用天地之力,了解天生之物,从而为我所用的学问。这一类,便是后来的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为君子所不耻。”徐元佐道。
李腾道:“其实我道门也有经义学与炼丹术的分野。你想说的,大约就是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道学和器术吧?”
“并不尽然。”徐元佐摇头道:“数学、物理也是能够衍伸出自己的道。更像两种入手功夫……唔,对了,就是道家所谓的性命之学,是从了性入手,还是了命入手。”
李腾怀疑徐元佐的解释有些牵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