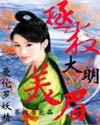大明金主-第20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唔?”程宰一愣。他很难想象,竟然还会有人像徐元佐一样没事烧钱。虽然得民心者得天下。但显然办报是最烧钱,得民心也最慢的手法当然,这肯定是因为佐哥儿不是冲着得天下去的。不管怎么说,这个有模有样学着烧钱的人是谁呢?
程宰是靠文字吃饭的人,对字句文章有着经年累月培养出的敏感性。他一目十行,速读了这《姑苏时报》的头版头条。原来是一篇批判士绅之家经营末业,败坏士行的社论。
社论这东西也是佐哥儿首创,旨在移风易俗。《曲苑杂谭》第一篇社论就是“礼乐不可偏废,以礼立身,以乐和心”,还是找的天下闻名的大才子王世贞主笔,出手不凡,果然引得许多士子在“乐”上开始下功夫。连带着以往不值钱的清倌人,也越来越金贵了。
程宰读完了文章,隐约中嗅到了针对徐元佐的满满恶意。虽然文中没有指名道姓,但是“举人生员云集一堂,不以文章相见,而苟且于阿堵之物”这分明是在说仁寿堂。后面甚至直接说到了“大士豪绅,为其张目,鱼肉百姓,聚敛贪虐”,这分明是在说徐家。
“不知有多少人看过这《姑苏时报》。”程宰不知道发行量的概念,本能地意识到报纸的影响力与读他的人成正比。
姜百里微微摇头:“此报自称发行五百份。”
程宰微微皱眉:这人真是豪富。
“其实我也知道是谁家出钱出力办的。”姜百里道:“只是一时想不到对策,特来求教陈先生。”徐元佐经常说起程宰,说他是智囊谋臣,但凡有什么问题,找他总有解决的办法。
姜百里对徐元佐是百分之百的信任,自然也信任程宰。
“若是份份有人读了,便是五百人;若是这五百人再拿给别人看,起码就有一千人了。”程宰说罢,又觉得自己估算的太保守了。谁会看了报纸不跟人聊聊呢?否则岂不是憋得自己难受。
姜百里微微点头,表示认同。
“一千人不是小数目啊。”程宰觉得益发热了,走到冰盆旁边方才觉得有丝丝凉意。他突然问道:“你这是哪里取得的?”
“是有朋友去苏州,随手带回来的。据说这报纸是放在货栈、码头,分文不要任行旅取阅的。”姜百里道。
之前顾水生在苏州放了不少包打听,专门收罗苏州消息。上到地方官员的去留。下到民间的鸡毛蒜皮,什么都要收罗了送回来。为此市场部还有专门几个人,整日里就是研究这些苏州送回来的东西,主要是要预测苏州各类商品的价格走向。
“八成是东山翁氏做的。”姜百里道:“他们之前收买了两家刻坊。还在市面上招雕工。没过多久,他们这《姑苏时报》就出来了。”
“他们这是要画骨呀。”程宰感叹道。
姜百里的主要业务是联络大客户,拉拢感情,收集反馈,提供售后服务。对于东山翁氏被佐哥儿教训的事所知并不多。不过他从别处隐约听说,佐哥儿曾叫翁氏吃了大亏。
“该如何是好?总不能叫他就这么犬吠下去。”姜百里毫不客气道。
程宰绕着冰盆走圈,眉头拧紧,道:“隔空相骂终究大失颜面。对了,这事你与吴先生说过么?”
姜百里道:“尚未来得及。佐哥儿说有大事先向程先生讨教。”
程宰听了心中一喜:原来佐哥儿表面上无所谓的模样,内中却是如此信任我。
这一瞬间,他更加有了“士为知己者死”的念头,只觉得自己蹉跎大半生,终于遇到一个明主了。
“吴先生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如今又管着《曲苑杂谭》。这《姑苏时报》等若是跟他打擂台呢。咱们先去找吴先生,与他商议看他如何说的。”程宰道。
姜百里道:“正是正是,还是程先生想得周全。”
程宰心中暗道:你还是太嫩了。人家在报上如此辱骂了你,哪里是两份报纸打擂台?这分明是要拼个你死我活啊!若是在唐行有这么个对手,早就叫人去砸了他的铺子,烧了他家刻板。可惜人家远在苏州,鞭长莫及,更何况很可能有官府罩着。
而且如今正是仁寿堂空虚之际。
徐元佐远在辽东,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呢!
主帅不在,难免叫人乘虚而入。
程宰打定主意。与姜百里上马车,赶去书房见吴承恩。
吴承恩在他们看来总是带着神秘光环。此人功名不显,但是学问渊博。待人谦和,却做过首辅文主。他主持《曲苑杂谭》之后。总让人觉得这报纸尽说些家长里短,游戏玩乐之事,但是细细回味,却又有种润物无声的妙趣。
如果是这样晴朗的下午,吴老先生肯定在亭中读书。读得累了便掩卷小憩,醒来之后再读书。就如个悠闲的读书人。看不见他在忙,但是篇篇文章都安排得格外妥当,从未见他误过事。
程宰和姜百里将《姑苏时报》递给吴承恩看。吴先生也是扫了两眼便知意旨。他道:“的确是来者不善,但这手段实在有些愚蠢。若是翁氏就这等水准,焉能做得出翁百万的名头?”
姜百里和程宰都有些不解,不知道这“愚蠢”的考语是从何而来。他们读这文章,还觉得写得颇有章法呢。
吴承恩起身笑道:“敬琏办报的目的是什么?”
程宰和姜百里自有思量,只是不说,等他说出高明的看法来。
吴承恩道:“是要移风易俗,牵领群氓。”
不过尔尔嘛。
程宰和姜百里不约而同心道:我也看得出来啊!
“说难听些,他是把百姓当傻子看,所以走的是润物无声之路。”吴承恩道:“某虽不能苟同,但百姓的确有盲从之弊。故而二夫振臂,云者万千。不过这《姑苏时报》却做了件傻事,画虎画皮难画骨,反倒类猫了。”
程宰顿时脸上一红。
吴承恩自然不知道程宰没多久之前还赞这家“画骨”有术呢,自顾自道:“他写这文章,看似立意颇高,直接拔到了‘士行’的层面。可他是写给谁看的呢?寻常百姓岂会在意‘士行’?他们更喜欢才子佳人私会南墙根……说白了就是爱看伤风败俗的东西。要是说写给士人看的呢?他这般写来,却让人生疑:莫非你是在骂我?”
姜百里脸上一红。
程宰笑道:“是了,他没有指名道姓,本以为刀锋所指人尽皆知。可惜却忘了姑苏也是官商汇聚之地,多少通贵显贵人家都在做买卖,这岂不是在骂他们了。”
吴承恩抚须笑道:“所以说他蠢,便是在这里了。”
“那咱们还需要理会他么?”姜百里问道。
吴承恩道:“这文章居高临下写得满口官气,矛头的确是冲着徐阁老来的。怕就怕这纸荒唐文,被有心人送到朝堂,竟披个‘民意民声’的袍子,叫高拱拿了兴风作浪。”
姜百里的心又提起来了,道:“这如何是好?”
程宰道:“先生既然洞若观火,必有应对之策。眼下敬琏不在,一切还要您老费心。”
吴承恩道:“我只是一介客卿……这事必得知会阁老才行。”
姜百里知道自己功力尚浅,没法跟苏州人对台斗法。但是要他就这么去找徐大爷,恐怕就白白错过这么个学习的机会。他道:“吴先生,即便呈给徐爷决策,照佐哥儿的规矩,下面经手之人也要写上分析和对策。学生就厚颜抄您的分析,还请好人做到底,一并给个对策吧。”
吴承恩头一回见姜百里,觉得这少年好学懂礼,说话也耐听。虽然不愿冒然做人师,却还是道:“这是你家佐哥儿锻炼你们的法子,你竟是要我帮你作弊么?”
姜百里连忙道:“岂敢!”他想了想,道:“依学生愚见,咱们大可也作论一篇,就将矛头指向姑苏城里的士绅,把水搅浑。”
吴承恩抚须而笑,食指虚点:“你这是偷懒耍滑。”
“还请先生赐教。”
“这是街头孩童骂仗的做派。于己无益,于人无损。”吴承恩摇头道。
这回连程宰都好奇了。因为他刚才自己摸摸想了想,应对之策与姜百里的也基本差不多。
“若是要叫他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倒是很简单:应他一声,抬他一把。”
吴承恩口吻清新,语调和缓,齿间却流淌出细细杀机。
*
求推荐票,求月票~!
*
ps:求各种支援~!sf0916
三四四探访
翁弘农很不甘心。身为自己心中最为崇拜的楷模、榜样、偶像的父亲,竟然要将家里的商路拱手让给一个毛头小伙子!然后呢?全家去做泥腿子么?家里聚财百万,尚且没有培养出一个真正进入仕途的士子,难道耕读传家之后反倒能够出进士了?这简直就是老糊涂!
翁弘农思考了很久,倒是终于叫他想到了一个办法出来。
他不怀疑父亲的眼光,徐元佐能够被父亲高看一眼,必然是有旁人不能企及的能力。自己要是与他硬碰硬,或许真的会着了他的道,反倒丢人现眼。他想到了小时候跟父亲下棋。因为棋力悬殊,他便学着父亲的走法走:父亲出马,他也出马;父亲拱卒,他也拱卒。虽然最后还是难逃落败,但是比自己瞎来要强得多。
这就叫临摹!
翁弘农与左膀右臂翁弘济商议了良久,发现这个办法或许还真能有用!首先,商场不是棋盘,领先一步固然能够占据优势,但是商场上更多的还要拼人脉和资本。在这上面,徐家的老营在松江,翁家的老营在苏州,看起来苏松一体,实则语言、风俗都不一样,可以说是两国交战各有营垒,翁氏未必就比徐氏要差。
其次,朝中有人好办事。若是徐阶还在内阁,那华亭徐家当然是金钟罩体,见到了还是躲远些好。可是徐阶已然致仕,而翁家这边还有蔡国熙这条门路,可以直通高拱高新郑那位才是当今真正的首辅。更何况高首辅与徐阁老是你死我活的天敌,说不定更乐见翁氏去打徐家耳光。
这固然有给人当枪使的嫌疑,更可能会被口舌之辈说是给人当狗。然而家族利益当前,做狗又如何?翁弘农益发觉得徐元佐的厚脸皮黑心肠,对他有极大的影响,偶尔间甚至会生出虚心学习的感觉来。
“徐元佐做了什么,咱们也做!许多事隔岸观火看不真切,还以为是闲手,说不定其中就藏着杀招!”翁弘农对弟弟们如是说。
翁老先生要带着家族转型。这是损害所有翁氏子弟败手!众人当下盟誓:众志成城,同心同德,定要保住翁氏的商路。
“不说打败徐元佐,起码也得叫他知道咱们不好惹。”翁弘济恨恨道。他最先代表翁家跟徐元佐接触。回来之后大吹法螺,结果却被打得鼻青脸肿,对徐元佐的仇恨丝毫不逊于翁弘农。
商议定策之后,翁弘农安排弟弟们潜入松江,察访徐元佐的所作所为。这事是翁弘济带头。他直扑徐元佐的老家朱里,租了一间客舍,整日间探访徐元佐过去的点点滴滴。
徐元佐自从“开窍”之后,便铁了心要在名利场上搏杀一番,当然不可能跟个间谍似的低调行事。对他来说,知名度就是无形资产,美誉度就是优质无形资产,街头多一则正面传闻,便是资产增值这种情形之下,恨不得上个厕所都要登报纸。哪里会偷偷摸摸?
而且这两年徐元佐对乡梓的改善实实在在。朱里本来只是个普通的江南小镇,然而如今徐氏集团的中高层管理人员一大半都是这里出去的。他们领着远高于乡邻的收入,每次放假回来,都带动了一波消费热潮。平日送回家里的钱财,也刺激了小镇的日常消费。最先是走街串巷的小贩开始增加了前来兜售货物的次数,然后是附近的农民发现朱里镇上买鸡鸭鱼肉的人家越来越多,再接着便是那些积蓄了资本的行商在镇上租门面,开个小店,成了坐商。
居移气养移体,生活环境改善了。身体营养状况也改善了,整个镇子的风貌自然大大不同。人们不是傻子,很清楚这一切的根源就是徐元佐。哪怕不说感恩图报,光想想自家子侄还捧着徐元佐的饭碗。便不会说徐元佐的坏话。
翁弘济到了朱里之后,很快就听说了徐元佐的各种传说。大多都是吹捧的,说得徐敬琏仿佛仙人下凡。甚至还有人说他出生时就有异象,乃是财神爷身边的小童子降生。从小就大智若愚,从来不跟人计较小钱小利,也不跟别的孩子一样闹腾。
翁弘济听得胸闷。唯一叫他顺耳一点的,是个铁匠的老婆。那婆子说:“徐家大郎原本是个痴肥呆蠢之人,突然有一天开窍了……”话没说完,那婆子就被她男人抓了手腕,又拿一根铁钎子狠抽。翁弘济看那架势,生怕打死了惹出麻烦,慌忙逃走了。
不管怎么说,徐元佐以前的点点滴滴倒是被翁弘济挖出来了不少。很多事就是如此不公平:徐元佐当年上课睡着了被陆先生打手板,现在变成了徐元佐睡觉的时候都坚持上课;当年买糖葫芦被人骗了两文钱,街坊四邻都说他脑汁不够用,现在则变成了从小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