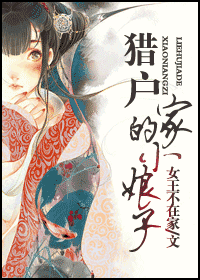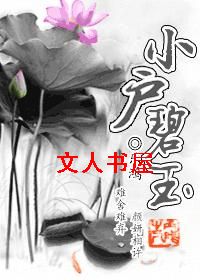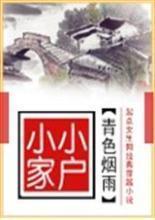辽东钉子户-第21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啊!”
熊若光张大了嘴巴,能塞进去一个鸭蛋,少年比他还吃惊,嘴里能塞进去鹅蛋。
“哎呀!都是属下有眼无珠啊!”
熊若光早就听说张恪的大名,可是他万万想不到驰骋疆场的名将,竟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他只当张恪是勋贵子弟。异想天开呢!
“少保,都是属下无知,属下有眼不识泰山,请大人恕罪。”
“不知者不怪罪,的确安全是很大的事情,把大家伙都叫过来,本官亲自解说一二。”
“是!”熊若光转身就走,猛然发现少年还傻愣愣盯着张恪,老头吓了一跳。急忙拉着他就走。
……
时间不长,难民们都聚集过来,大家伙一听说张恪就是在浑河大杀建奴的人,顿时崇拜之情犹如滔滔江水。大家伙一窝蜂跪倒在张恪面前,痛哭失声。
“大人,大老爷!带我们杀回去吧,我们要回家啊!”
哀鸿遍野。发自肺腑的呐喊,让张恪鼻子头发酸。
“大家放心,我们一定会消灭建奴。收复家园!不过有个前提,就是大家必须听我的安排。”
“大人,您让我们往东,绝不往西,让我们打狗,绝不赶鸡!”
“好!”
张恪微笑着点点头,他当即把屯垦草原的方略说了。首先所有难民编成两千人一组,从中抽取两百精壮,配发武器,主要对付狼虫虎豹,防止零星贼人袭击。每十组,也就是两万人,义州兵会提供保护。
他们在草原屯垦头三年不收田赋,三年以后,按照一成收取。唯一要做的就是接受军事训练,战时要出兵出人。
简言之这些难民就是军户,只不过他们比军户的负担轻,而且茫茫草原上,土地众多,还不用担心兼并。
“乡亲们,到了草原未必一定种地,也可以养牲畜。本官在义州建有毛纺作坊,虽然刚刚起步,但是需要羊毛惊人,你们只要肯干,绝对比当佃户过得好!”
此言一出,百姓们最后的担忧也解除了,大家伙跪在张恪的面前,叩谢再造之恩。
王化贞也笑道:“大家同意了就好,马上就开始编组训练,本官会提供粮食,大家尽快开赴草原!”
有吃的,也有出路了,百姓们热情地欢呼,简直如同过节一般。
可是另外一边,榆树村原本的百姓互相看了看,艰难地咽口唾沫。
“四爷爷,才一成田租啊!”有人咬着后槽牙说道,羡慕的模样简直不用说了,恨不得加入其中。
有个高挑细瘦的中年妇人撇着嘴,讥笑道:“老七,没听说,是去鞑子那边种田,就你这小胳膊小腿的,还不被鞑子撕了,咯咯咯……”女人刻薄地笑了起来,年轻人羞红了脸,低下头。
常四爷叹口气,说道:“唉,他们是没活路了,要拼命的。咱们是本分的庄稼人,守着一亩三分地,有口吃的,就别折腾了!”
榆树村的百姓眼看着难民们都跟着张恪走了,按理说没了一个麻烦,可是他们却没有什么喜悦,每个人都心事重重。
村子外不用安排眼线了,可是刚过半天时间,突然一伙人跃马扬鞭,冲到了村子里。
为首的是一位盔甲鲜明的武将,在他的旁边跟着一位富态的老者。
这位武将面对着村民,趾高气扬说道:“老子叫鲍承先,是堂堂副总兵,听说你们这帮刁民欠了徐老爷的银子!一时三刻马上还钱,不然老子不客气!”(未完待续。。)
第二百八十五章 跟着我,有肉吃
“末将鲍承先,拜见少保大人。”
张恪一脸骗死人不偿命的笑容,轻轻摆手。
“鲍将军,你是原本是贺总兵的部下,我和贺总兵是世交,咱们也是朋友,你赶快起来吧。”
鲍承先一听张恪这么客气,顿时也松了口气,他本来帮着岳父徐寿讨要榆树村民的欠款,结果张恪突然派人让他过去。鲍承先还以为恶了张恪,他舍了岳父,带着手下急匆匆赶回来,浑身都被汗水湿透了。
“鲍将军,西瓜在井里拔过了,来一块吧。”
侍女奉上西瓜,鲍承先受宠若惊,连连称谢,捧起西瓜,冰凉甜润的汁水流到心头,燥热不翼而飞,别提多畅快了。
“少保大人如此厚待卑职,真是不知道该如何报答大人,日后卑职一定唯少保马首是瞻!”
“哈哈哈,镇守辽东也少不了宝将军这样的勇将。”张恪转过话头,问道:“鲍将军,你写信提到过想弄些田产,可有此事?”
“啊,没错。”鲍承先摸不着张恪的脉,只能含混说道:“少保大人,不光是我一个人,还有不少武将弟兄,大家伙的田产都没了,家当也一点不剩,实不相瞒,过的连要饭的都不如,这些日子属下就在岳父家里,成了倒插门的女婿,没脸见人啊!”
鲍承先说着还擦了擦眼泪,装的万分委屈,张恪心头好笑,也不戳穿他。
“鲍将军,大家伙的艰难我都看在眼里,可是你们也知道,田地终究有限,我总不能去强征土地,划给你们吧!”
鲍承先继续哭丧着脸哀求:“大人,实不相瞒。下官世代效忠大明,屡立战功,累计的土地超过一万七千亩,全都在盖州一带,沦于建奴之手了,朝廷总该给忠心耿耿的臣子一点奖励吧,让我们能活得下去啊。”
张恪故做沉思,思索了半天。
“鲍将军,你说的本官都知道,可是巡抚王大人那里接到了百姓告状。他们说有人强抢土地!”
“绝无仅有,请大人明察。”鲍承先急忙否认,说道:“大人,都是刁民无理取闹,田地租给谁,本来就是地主一言而定,外人凭什么置喙。”
张恪点头道:“有理,不过毕竟有碍观瞻,这样吧。鲍将军,只要是公平买卖,谁敢找你们麻烦,本官一力承当。话又说回来。你们要是仗着武力,仗着官身,欺压百姓,我也不能坐视不理!”
兴奋过度的鲍承先根本没有理会后面半句。他只当张恪站在了他们一面。说起来也没有什么意外的,张恪也是辽东的武将,怎么可能不帮自己人呢!
鲍承先心满意足地告辞。临走的时候,留在桌上五张银票,张恪接过来一看,都是一千两一张,见票即兑。
“哈哈哈,挺有钱的,不过很快就会没有了!”
张恪轻蔑地冷笑道。
半个月时间,张恪陆续知会了退回来的所有将领,包括原来广宁的孙得功和汤辉也都得到了通知,不许强买强占。
大多数人眼里,根本不痛不痒。
鲍承先再次带着他的家丁跑到了榆树村,他把村口堵起来,逼着老百姓还钱。不还钱他就提高田租,总之有一万种方法炮制老百姓。
“常老头,没别的说的,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你们还有什么说的。”
常四爷拿着旱烟袋,狠狠吸了口,吐出一个大大的烟圈,缓缓问道:“鲍大人,就不能缓缓吗?”
“缓什么缓,我告诉你,外面有的是贱皮子想租田地呢,你们不还钱,这些田都收回去!”
“好啊,真是好啊!”
常四爷仰天叹口气,苦笑道:“真是不给好人活路,鲍大人,小的们惹不起,还躲得起!”
老头站起身,冲着村子里大喊道:“乡亲们,留下来是没活路了,咱们走!”
此话一出,鲍承先一头雾水,可是村子里已经走出了好多百姓,他们扶老携幼,把破破烂烂的家具装在独轮车上,背着布包,默默向村外走去。
“你,你们,要干什么?”
“不干什么!”常四爷磕了磕烟袋,冷笑道:“鲍大人,您岳父的田我们租不起,欠多少银子,地里有庄稼,还有这些房子,都归你们了。”
“乡亲们,走啦!”
村民们含着泪,走出了世代生长的村子,纵使有千般的不舍,可是一想到让人眩晕的地租,他们就没有一丝犹豫了。
鲍承先看着远去的人群,他顿时傻眼了,这帮人怎么轻易就走了,没了田地,他们还有什么活路?
鲍承先百思不得其解,不过他还是如愿以偿了,田地都归了他。赶快让人去把岳父徐寿找来。
“爹,村里的贱胚都走了,这些田就是咱们的啦!我这就去招募流民过来,地里还有一季庄稼,简直赚大了!”
鲍承先手舞足蹈,高兴地没边,可是岳父徐寿脸上却一点笑容没有,相反五官扭曲,难看的要死。
“爹,你高兴地糊涂了?”
“唉,高兴什么啊,咱们摊上麻烦了!”徐寿无奈地叹道。
其实何止是他,那些磨刀霍霍的将门大族都憋着兼并田地,好好捞一把。他们巧取豪夺,用尽一切办法,占有更多的田地,把田租抬得更高。
辽西就这么大,还不任由他们上下其手,大发横财……
不过这只是梦而已,他们发现先是难民陆续都消失了。就算没有消失,也纷纷聚集到朝廷搭建的营地之中。
每天里面都飘出米香,离着老远能听到训练演武的声音。
一两个月的时间,难民就会跟着明军离开。空闲的营地很快会被其他人填满,而这些人多半都是他们手下的佃农。
刚开始人员流失,谁都没当回事,三条腿的蛤蟆没有,两条腿的活人遍地都是!
你们不愿意干,还有别人干呢!
可是很快他们就感到了不妙。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消失,只留下空荡荡田地,虽然庄稼还在,可是总不能让尊贵的地主带着三妻四妾去收割吧。
惊醒过来的地主急忙打听,他们终于弄清楚了,原本的佃农都被朝廷忽悠走了。
去草原屯垦,三年不收地租,朝廷派遣军队保护,而且随便垦荒,能种多少就种多少。
这消息简直把辽东的大户都砸晕了。开什么玩笑,去蒙古人地盘上垦荒,找死啊!
愤怒地大户地主召集了打手,要给不知死活的佃户一个教训。他们雄赳赳刚出动,义州兵就像闻到血腥味的鲨鱼,毫不犹豫冲过来,暴揍一顿,打得他们爹妈乱叫。
张少保说得好,佃户去留。各凭本事,敢用强,杀无赦!
大户们傻了眼,只能反复告诉自己的佃户。千万不要上当,去了蒙古那边,就再也回不来了!
苦口婆心地劝说似乎有点用处,佃户流失的速度变慢了。
秋收的时节也到了。地主们因为缺少人手,不得不纡尊降贵,跑到田里和百姓一起劳作。一天下来。腰几乎折了,细皮嫩肉的双手全都细小的口子和血泡,简直欲哭无泪。
而真正麻烦的事情却从天而降!
不知什么时候,乡间突然多了很多商贩,他们推着小车,上面放着崭新的苇席,大声吆喝着。
有好奇的百姓凑过来,一见之下,顿时吓了一跳。
“你,你不是榆树村的田老七吗?怎么做生意了!”
田老七呲着板牙,嘿嘿笑道:“还不许俺时来运转吗,大家伙看看苇席吧,全都是上好的货!”
拿开了席子,下面还有两个大木桶,大家往里面一看,眼睛都直了。
“这,这是什么东西?”
“连这都不认识了?”田老七笑道:“左边的是口碱,蒸馒头用的。右边是咸盐,不要我说了吧!”
盐!
有人抓起来,尝了一口,果然齁死人。他们痴痴瞪着田老七,惊骇地说道:“贩私盐,你不怕掉脑袋?”
这话一出口,围拢过来的人全都倒退好几步,自觉和田老七划分界限。
大明的食盐一直是专卖的,贩卖私盐从来都是掉脑袋的重罪,不由得普通百姓不怕。
田老七却满不在乎,笑道:“乡亲们,我这可不是私盐,你们看看,这是辽东巡抚衙门发下来的盐引,小弟我每年能贩运两千斤咸盐。我的盐可都是顶好的,和青盐差不多。”
为了证明自己所说不假,田老七呲着雪白的门牙。只是大家并不在乎这个,他们想知道田老七是怎么咸鱼翻生的。
“实不相瞒诸位,我们都跟着朝廷的军队到了草原上。到了地方,才知道满地都是宝贝。一人多高的芦苇,砍下来编成席子,男女老少一起干,有晋商过来收购,一个女人半个月就能赚三两银子!”
多少!
在场的百姓嘴长得老大,简直不敢相信耳朵,他们一年也挣不到三两银子啊!
“嘿嘿嘿,这算什么,我们新村子周围有盐湖,里面都是白森森的食盐,还有口碱。这玩意在草原上没有人在乎,和废物一样。”田老七美滋滋说道:“我们采盐,每个月给军爷一千斤,剩下的可以自己卖,小弟不才,就有两千斤的盐引,这可是传辈儿的宝贝,儿子,孙子,都指着发财呢!”
田老七说着,小心翼翼把盖着大红官印的盐引塞到了怀里。
周围的老百姓眼珠子都红了,一个个垂涎三尺。
“老七,七爷!快告诉大家伙吧,怎么交好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