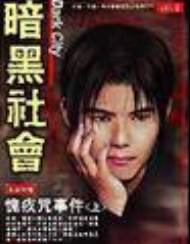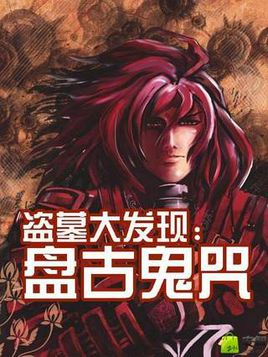重新发现社会-第5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要面包,更要玫瑰】
岁月无情,当年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如今已经步入生命的暮年。反思这场运动,主流态度不外乎两种:一部分人持否定态度,有人甚至将这场运动简化为一场“打砸抢”、一场“意识形态病”的急性发作;另一部分人则得了怀乡病,1968年的5月,只是他们人生中一个远逝的梦想。至于在这一运动中受到冲击的官方,尽管他们当中许多精英都是“‘六八’下的蛋”,但没有人会给当年那群“越革命越想做爱,越做爱越想革命”的才子佳人们颁发奖章。
毫无疑问的是1968年5月改变了法国。如上所述,这与其说是一次“失败的革命”,不如说是一次“成功的改良”。度过七十年代的广泛的自责与失落后,当历史进入八十年代,“五月革命”的成果才依稀显现。过去僵硬的社会关系消逝了,象征性的等级制度不明显了,取而代之的是工资的迅速提高而带来的收入等级。“五月革命”以其特有的反抗方式改变了当代法国的历史风尚。用一个法国学者的话来说,“五月革命”以后的法国的生活变得性感。
从此以后,“对话”与“商讨”成了法国政治中的一个常态。法定的程序、绝对的命令、神圣的指示不再那么高高在上。“五月风暴”以其特有的方式客观上完成了社会力量对政治力量的一种抗衡或者分权,表明这场文化革命所具有的政治内涵。
几百年前,托克维尔曾经指出,法国大革命的一个根源在于法国农民受到的束缚大辐度减少,生活水准显着提高,而随着手铐的去除,剩下的脚镣往往会变得百倍的不能容忍。这说明,革命或者群体性混乱并非都是在一个国家政治、经济走向崩溃时才会发生。发生在1968年的“五月风暴”,同样具有这一内涵。不同的是,这次“革命”已经不像往常,而是褪去了尖牙利爪。
进一步说,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疑难,革命并非只是发生在贫穷、落后或有冲突的地区,解决了“温饱问题”不等于解决了“革命问题”。法国“五月风暴”便是在一片莺歌燕舞的社会转型中发生的,而且,这场“革命”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不是为了面包,而是为了玫瑰而发起的。1968年的法国,正处于法国由古老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强力转型的混合时期,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即将流行的新潮思想,与二三十年代的家长制社会并存。这种新旧混合同样表现在那些要求革新的年轻人身上——他们喊着二十世纪之初的革命词语,引领法国走向一个新的时代。
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1968年“不创造,毋宁死”的改革诉求,还是今日法国遭遇的“谁改革,谁下台”的政治困境,其背后的逻辑都是法国的社会力量对政治运行有着深刻的影响。或许可以说,从1968年开始的“五月革命”并没有真正结束,政治力量与社会力量的对话或者对垒从来没有停歇。正是对话的存在,避免了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冲突与动荡。
世界永不完美,冲突还在继续。回顾发生在四十年前的这场近乎风花雪月的“革命”,不难发现,对于任何国家来说,当危机来临时,最重要的是社会力量与政治力量必须恪守自己的边界,一起守住底线,一起守望。
错过胡适一百年
我常把读书的乐趣融于人的历史。在所谓人的历史中,读传是条捷径——传记“浓缩人生精华”。你甚至只需几个小时,就能把一个人看进了坟墓,想象他在坟墓中仰卧起坐,唉声叹气。茔墓之外,我们在逝者的影子下完成对社会的回忆与改造,完成对往届社会优良品质与智慧的追索与继承。
坦率地说,是黄仁宇让我重拾对历史的兴趣。我是说,我从学术上看出了历史的乐趣。这位国民党军官在美国写了《万历十五年》。用他的话来说,他研究的是大历史(Macro…history),这个词很玄乎,我倒宁愿把它想成“随心所欲读历史”。黄仁宇的学问的确是做得很好,也很中立,因此也给了我们读者一次换个角度读历史的机会。黄仁宇和周恩来同是南开校友,遗憾的是,南开大学没有把肄业生周恩来的礼遇分给肄业生黄仁宇一点,但这并不影响黄仁宇声名远播。
读了黄仁宇的历史书,我开始对海外的中国史家产生了兴趣。作为旅美学者,唐德刚自然成了我书屋里的贵宾了。虽然直到今天,唐德刚的书我只看了两本,一本是《晚清七十年》,另一本即是我这里要介绍的《胡适杂忆》——严格地说,还有《胡适口述自传》,收录在《胡适文集》中。对于胡适的追寻,大概就是从这本书开始的。
唐德刚是胡适晚年的入室弟子,曾亲自录制并译注《胡适口述自传》,被公认为海外论胡允当者。唐之“胡说”不辱大方,意创笔随,明珠走盘,的确是些好书。唐德刚在《杂忆》书尾称:“关于了解胡适,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要了解胡适,我个人的看法,最可靠的两部书,便是《四十自述》和《胡适口述自传》。”在我看来,《杂忆》是可以和上述两本比肩的。在该书中,唐德刚对胡适没有太多的隐讳,尽可能地做到客观(当然,也有些看法和读者大相径庭)。
在杂忆胡适时,唐德刚并未因为是胡适的入室弟子而像罗尔纲写《师门五年记》《胡适琐忆》时那样毕恭毕敬,更多是尖刻、风趣与超脱。比如谈到胡适与政治,唐德刚说胡适是“不要儿子,儿子来了”;胡适容忍,是“爱惜羽毛”“畏首畏尾”(借李宗仁语);搞政治胡适后天不足,“在主观条件上,胡先生所缺乏的是:他没有大政治家的肩膀、中上级官僚的脸皮和政客与外交家的手腕,他甚至也没有足够作政论家的眼光”;胡适被杜威老师牵了一辈子鼻子,做了几十年齐天大圣,最后发现自己不过是个癞和尚的保镖;老顽童甚至向读者回忆起胡老师挤上公共汽车时的情景,“一个瘦骨嶙峋的脊椎动物”。
当然这些并不影晌唐德刚对老师的正面评价:胡适是“近代中国唯一没有枪杆子做后盾而思想言论能风靡一时,在意识形态上能颠倒众生的思想家。”胡适的确是个圣人,在他身上,全然没有两千年来无数乡愿、学究、家天下帝王及其臣仆们自阉精神的“继往”,更没有极端年代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狂阉他人的“开来”。
对于“五四运动”,唐德刚与胡适的观点并不一样。胡适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反对政治,另一方面,却又做了一辈子的政治票友,“胡先生是反对五四运动的。他认为新文化运动的夭折,便是把五四运动政治化的结果”。唐德刚后来解释道:“新文化运动这部列车,被这批小伙计板错了方向盘,就横冲直撞起来,结果,目的热,方向盲,列车出了轨、翻了车,弄得伤亡遍野。可怜的老胡适也被弄得教授当不成,新文化运动前功尽弃,而跑到纽约来落草。所以他反对五四运动。”
对于五四运动的是非褒贬由来已久。胡适的观点是:“新文化运动才是那害了两千年瘫痪病的中国固有文明的对症良药,是当前救国救民的唯一道路。”胡适的理想是在一个非政治化的环境下投身文化与科学教育,再造文明,完成中国的文艺复兴。折腾了一百年往回看,胡老夫子不是没有他的道理。忽略真正的文化和教育,仅靠几个先知先进带着群盲打打杀杀瓜田分地杀资本家,仅图一时一势的革命,是不能真正改良社会的。革命到底是解放人的事业,而不只是解放猪圈里的牲口,让它从张家的院子跑到李家的厨房。
历史车轮鬼打墙。转到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到处都是“人文关怀”。除了卖猪饲料的,什么样的企业都开始将“以人为本”的招牌挂上了大街。当然,以人为本并非舶来品,甚至可以说是中国的国粹。中国从来就是以人为本的。只不过,中国的人本是以钳制人为本,而西方的人本却是以尊重人、解放人为本。关于这一点,胡适在一次出游东北时有所感悟:中西方文明的区别是,前者是人力车文明,后者是摩托车文明。所以胡适要在思想上解放中国,再造文明,要实用主义,要杜威哲学,要全盘西化(后措辞为“充分世界化”);因为要自由,所以要容忍。胡适说的容忍并不是菩萨说的容忍。
胡适一生奉行多研究些问题,少谈点主义。唐弟子给胡老师的“挽联”却是,“多研究经济,好研究问题”。
“胡先生告诉我,他在康乃尔读大学本科时,对经济学就没有兴趣,未尝先修有关经济学的科目,因而他一辈子对各种经济学也很少涉猎。这便是他老人家晚年谈政治问题的致命伤”“胡适之先生对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虽然生死以之,他却始终没有搞出一套完整的理论来。不是他无此才华,而是他在社会科学上无此功力!没有一套完整的理论来对近百年——乃至三千年——的中国政治经济的演变做一番通盘的了解,而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地去搞一点一滴的改革,那就必然扶得东来西又倒。”
胡老夫子如果知道他的入室弟子这样给他盖棺定论,定会气得从棺材里坐起来。生死以之,忙了一辈子竟然被弟子说成了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江湖郎中。
胡适生前建树颇多,也因此被“我的学生毛泽东”(胡适语)组织了大陆学界搞了数百万字的批判。
胡适膝下有二子,长子胡祖望,得名于胡母冯顺弟,有允宗耀祖之意;次子胡思杜,由胡适亲赐,寓意“思念杜威”,既表达了他对老师的敬重之情,更含着他一生对自由主义的竖定信仰。1949年后,胡适去了美国,祖望继续留在美国,而思杜却留在了大陆,并于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改造。1939年6月27日,性格泼辣的江冬秀在给胡适的信中写道:“小三(胡思杜)死没有出息,他要学政治,日后做狗官。”其实在那样一个政治压倒一切的年代里,即使胡思杜当年不问政治,政治最后也是会问到他的。
“不要儿子,儿子来了。”胡适曾说,“思杜是我创造的”。大意是说中国该选择杜威,更要一代代“思杜”下去,但他怎么也不会想到,他的儿子竟会朝他飞来投枪,称他是“帝国主义的走狗”。1951年,胡思杜在《中国青年》上发表了《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他对反对派的赤胆忠心,终于挽救不了人民公敌的颓运,全国胜利来临时,他离开了北京,离开了中国……今天,受了党的教育,我再不怕那座历史上的大山,敢于认识它,也敢于推倒它,也敢于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天秤衡量他对人民的作用。从阶级分析上,我明确了他是反动阶级的忠臣,人民的敌人。在政治上他是没有什么进步性……这一系列反人民的罪恶和他的有限的(动机在于在中国开辟资本主义道路的)反封建的进步作用相比,后者是太卑微不足道的……在他没有回到人民的怀抱来以前,他总是人民的敌人,也是我自己的敌人。在决心背叛自己阶级的今日,我感受了在父亲问题上有划分敌我的必要。经过长期的斗争,我以为在阶级上大致划分了敌我,但是在感情上仍有许多不能明朗割开的地方。除了自己随时警惕这种感情的危害性以外,我并要求自己树立起工农大众的感情来。”
对胡适的批判,我在《胡适日记》第八卷(1950~1960年)里能找到不少记录。
〖1950年9月23日
附录一则英文剪报:Chinese ex…envoy denounced by son(《中国前公使受到儿子的谴责》),引语是“胡适之子接受共产党教育,胡适成为攻击目标——指控其受美国影响”。
1950年9月24日
附录一则英文剪报:The case of DR。 Hu shih(《胡适案》)剪报提到,胡适博士获悉其子“因受中国共产党人的赤化反戈一击”,谴责他是“反动派的忠实官吏及人民的公敌”消息后,做出下述简明但是意味深长的评论。他说,过去我们注意到,在共产主义国家中是没有言论自由的;但现在还可以看到,在这些国家中也没有“沉默的自由”。他说,在共产主义的统治下,人们必须做效忠与信仰的声明。就目前的情形而言,没有“沉默的自由”导致目前令人作呕的滑稽事件的发生。我们所有的人对此一定会感到非常难过,不是为胡适博士,而是为被迫做出这种虚假荒唐声明的年轻人。……胡适博士时常睿智尖刻地批评国民党政府的种种错误,然而,面临国民党政府与共产主义(从知识上和道德上奴役人)两种选择时,他显然选择了前者……
另附一则英文剪报:Father not disturbed(《父亲巍然不动》)。
1950年9月26日
附录《华侨日报》9月25日的文章,文章提到“胡适被自己之儿子声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