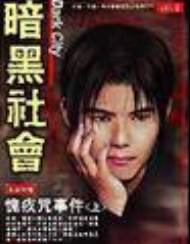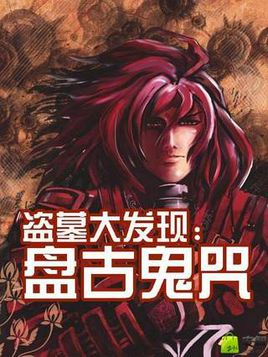重新发现社会-第5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子、一个道家和一个土匪。如何看这种划分或者概括?
王学泰:大传统与小传统之说来自台湾李亦园院士,是芝如哥学派考察文化社会学的一种方法。它视纽约一类的城市文化为大传统,墨西哥印第安乡村怪力乱神文化为小传统。用这个来套中国的传统我觉得有点“不合”。在我看来,中国上下几千年城乡的传统是类似的,都属于主流文化。如果说有个与主流文化大相径庭的文化,应该是游民文化。但是中国的游民文化不是在乡村发展起来,而是在城里发展起来的。孔子、道家是指中国士人思想主流,也就是李泽厚说的“儒道互补”。“土匪”如果指游民文化,我以为如果以此分析宋代以后的士人思想,那是“虽不中,不远矣”。
熊培云:您知道,墨家在秦以后就渐渐没落了。《水浒传》里的“梁山好汉”是否是“落草的墨家”呢?
王学泰:这点我是不同意的。墨家曾经是显学,历史上有天下“不归杨,即归墨”的时期。春秋时期君主、诸侯、大夫、士、庶民各安其位,每个人有自己的生活“点”,所谓天下“无旷土,无游民”虽然有些夸张,但在当时游民的确很少。《左传》里有“大夫无境外之交”的说法,周朝建立的是一个垂直统治的专制政体,其对治下的“横向联合”必然是加以防范的。但是到了春秋后期,孔子的《论语》开篇便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说明那时候社会的横向联系发生、发展了。这种横向联系也是侠得以产生的条件。《史记》里的“战国四君子”如信陵君、春申君、平原君、盂尝君等都是善于横向交往的人。“侠”字最初意思就是一个大人夹两个“小人”,表示有人追随,“四君子”都是有大批人追随的贵族。这不同于金庸小说里独来独往的武侠(近代武侠小说,特别突出独行侠,作者不懂传统的“侠”却是热衷于成帮搭伙的)。墨子也可以说是侠,有许多人追随他。同匪不同的是,墨家还有自己坚定的信仰。
【从江湖到庙堂】
熊培云:范仲淹在《岳阳楼记》里感慨“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庙堂对于许多人来说,通常都意味着高高在上的权力。但江湖却不一样。中国人常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意指“江湖险恶”,而“重出江湖”与“退隐江湖”里“江湖”的内涵更是完全对立。如何理解中国人心目中的“一样的庙堂”与“不一样的江湖”?
王学泰:“江湖”作为一个词在先秦就已经出现,最初的意义就是指江河湖海。这是江湖的第一种含义,即大自然中的江湖。二是文人士大夫的江湖,意指逃避名利的隐居之所。第三个是游民的江湖,也是我们现在经常活跃在口头的江湖。这种江湖充满了刀光剑影、阴谋诡计和你死我活的斗争。所谓“常在江湖漂,哪有不挨刀”讲的就是水浒里的江湖。
论及庙堂,中国两千年历史中,基本上是五十年一小换,两百年一大换。改朝换代垂直流动最大的就是皇族与游民。前者生命不保,后者有可能做了功臣显贵甚至皇帝。比如朱元璋,有人说他是农民,其实他没有土地,以乞食为生,做了很多年游僧,真正的身份是游民。高高在上的帝王与沉沦底层的游民,表面上看相隔云泥,是尖锐对立的,但实际上两者在心态、思考问题的方式上往往是相通的,而士大夫属于夹心层,通常会受到来自两方面的夹击。
熊培云:所以困顿其中、左右为难的士大夫阶层通常是既有儒家修齐治平的入世精神,又有道家闲云野鹤的出世精神。
王学泰:庙堂与江湖对立,一个主流,一个隐性。打天下和治天下通常都少不了儒家的一些精神。当然,儒家很多东西是好说不好做,更多只能是幻想。如果儒者统治一个以宗族为主体的小国家,几万人,可能还可以。儒家要解决的是熟人社会的问题,比如它强调的“知耻”,便是调整熟人关系的。但现代社会更需要调整的是陌生人之间的关系。记得解放初每个家庭都要拟订“家庭爱国公约”,实际上家庭是不需要公约的,真正需要公约的是陌生人社会。
熊培云:这也从另一个倒面反映了当时政治高度介入家庭,使家庭成员“陌生化”,互不信任。
王学泰:回过头说五伦。孟子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所调整的都是熟人关系。然而,从秦始皇开始中国就进入一个陌生社会了。陌生社会怎么能用熟人社会的办法统治呢?陌生社会遇到更多的是五伦以外的问题,这就是所谓的“第六伦”,即陌生人之间的关系。而调整这种关系最有效的还是法律。你知道文革的乱,当时中国人已经基本没有什么法律意识了,虽然“判决书”上照例说“特依法判决如下”,但“依”的什么“法”,不仅被判决人不知道,恐怕连判决者自己也不知道。因为文革中“公检法”已经被砸烂,“法律”被视为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产物。历史学家唐德刚说当时是“两部法律(《宪法》与《婚姻法》)治中国”,实际上当时连《宪法》也已废止,所以准确说是“一部《婚姻法》治中国”。
熊培云:梁漱溟先生曾将个人与组织的关系称为“第六伦”。您曾谈到中国人“庙堂很远,江湖很近”的现象。中国不断开放,游民意义上的江湖也在不断开放、膨胀,此过程是否也在孕育危机?
王学泰:担心是有的。封闭时代农民逆来顺受,认为不公平生活是“应该的”。当传统社会解体,农民子弟走出家乡,眼界宽了,想法也会变化。你看为什么近代革命在湖南闹得那么厉害?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曾国藩将一帮淳朴的乡野子弟带出去当兵打仗。后来曾国藩功成名就,为了避嫌就把军队解散了。这些有见识、对不公正敏感,而且强壮勇武、有功名、没收入的“复员兵”回到家乡,马上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后来湖南帮会林立,山堂香水遍地,就与这帮人有关。
熊培云:在庙堂与江湖之间,在国家与社会之间,中国人是否还有其他栖身之所,比如心灵?
王学泰:李敖说,知识分子首先要解决自己吃饭的问题。我想这点是十分重要的,而且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这样。中国这些年的进步首先就体现在告别了管仲所谓的“利出一孔”的时代。我写中国饮食文化史,说到夏、商两朝灭亡理由几乎都是一个样——君王贪恋女色,吃喝没有节制。当时所谓大吃大喝也只是“肉林酒池”,这有什么美好呢?但是在底层社会眼里,的确是没有比“多吃多占”更令人憎恨的了。应该说,这种憎恨与大家长期吃不饱有很大关系。现在人们对吃倾注了那么多的热情,是与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物质饥渴”有关的。文革中对知识人来说是精神饥渴时代,刚改革开放,人们也曾有过一哄而起的精神追求,但很快就平复了,而“吃”的追求仍是方兴未艾。我们这个民族的长期贫困,单独对心灵方面的追求是比较少的,对“心”也是忽略的,所以中国传统小说里对心理描写也很少。
熊培云:三国里倒是有,但更多只是心机与权谋。中国人的心灵,可能更多是通过诗词来表现的。
王学泰:《红楼梦》就不一样。整体来说,只有满足了温饱之后,人们才会注意精神上的追求。当然,独立的心灵空间在文人士大夫世界里是存在的。《易经》里就有“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说法,后来衍生出老庄学派,有了对功名利禄的拒绝。而“江湖”最早也是见于庄子,虽然指的是江河湖海,却有广大无边、自由自在的意味。庄子感慨涸辙之鲋,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但若没有宽阔的江湖,就不可能“相忘于江湖”。
【大王专制与大哥专制】
熊培云:王蒙在《〈三国演义〉里的前现代》一文中谈到:一些三国故事,颇有浓厚的黑社会黑手党故事的意味。上来就是“桃园三结义”,典型的黑社会做法和黑手党语言:“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一副盗匪的亡命气。请问庙堂与江湖对社会成员的控制有何异同?
王学泰:儒家较重视长远利益,庙堂自西汉以后重“外儒内法”,儒家思想多少对皇权还有约束。因此虽然皇权也专制,但想到子孙还是有些通融之处的;而江湖是大哥专制,他们处在隐形状态,面临的风险更大,其专制力度更大,也更容易极端。例如洪门成员常说“哥不大,弟不小”,实际上“大哥”是受会众崇拜的。臣民崇拜的皇帝只是个符号(很遥远),而后者却是很具体。比如李逵对宋公明的崇拜要比百姓对天子的崇拜就更狂热更具体。在大哥专制里,熟人社会和生人社会的统治兼而有之。
熊培云:这样说来,这里的庙堂与江湖,便可以分别称为“大王专制”和“大哥专制”了。不过,“大王专制”到了极致,可能比大哥专制也并不差。比如,历史上敢于到南洋创业的人,一旦在外面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或被人杀害,中国皇帝的反应是臣民离开本土死了活该。这个传统可以上溯到姜子牙时期,据说当时有庶民想到小岛上自耕自足,姜子牙认为不配合当时的周王就把他给杀了。现在我们讲国家应该是“自由人的联合”,但上面的这种国家伦理却意味着国民想“退出国家”,或像古罗马平民一样用脚投票(另一种意义上的“金盆洗手”)几乎是不可能的。到了近代,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不仅钳制民权,而且也直接导致了一个帝国的衰弱。
王学泰:过去把国看成帝王之家,不让民众出去。另外,中国是个政教合一的国家,对于不接受国家教化的人们(离开故土被视为脱离教化)是敌视的,是看做“可诛”的。这都不是现代国家所追求的。前不久,我对记者说,考察欧洲的人口发展,英国是个好例子,可与中国对照。英国可供耕作土地并不多,农业生产的条件也不是太好。十五世纪中叶英国才200万人,五百年后增加了至少100倍。中国那时(相当于明朝中叶)人口接近一亿。英国传统没有安土重迁的观念,自十七世纪以来,先是自发地向外流动,政府不管,后来得到政府的支持。其实,“殖民”是一个中性词,在民族国家形成(十九世纪)以前,人口密度大的地区向人口密度较小的地区流动是正常的,错的是有些国家武力殖民,杀戮原住民。自古汉民族安土重迁,视他乡为畏途;政府对于人口外流不仅不支持反而打压。
乾隆时期,荷兰在婆罗洲杀了好几千中国人,那时清朝还很强大,荷兰人很恐惧,向乾隆致歉。但乾隆说这些“莠民”不顾祖宗“庐墓”跑到外面谋生,做化外之民,回来也要杀头的,你们替我们惩办很好。这就是统治者对于老百姓到海外去谋生所持的态度。当中国人口发展到四亿,以当时的农业生产力很难养活这么多人的时候,本来有可能分流到南洋去,但被禁止了;向东北流动,但那是满洲皇帝的禁脔,有柳条边政策,不许汉人染指。遂使东北疆域广大,人口稀少,清统治者又保护不了自己的土地,以至于被西来的俄罗斯人占领了很多。直到清末才开放东北,但已经晚了。西伯利亚一带,滨海一带,清末民初中国人数远过于俄罗斯人,十月革命后,或被遣回,或被同化。
如果清朝不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亚洲版图也许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从这一点来说,使华人在世界上失去机会,历代统治者都有责任。最近在《万象》读到张大千在1960年代写给大陆亲属的家书,看到在那个极端困难时期对有可能外流人口的严密控制,真让人感慨万千。
熊培云:有时我想,在庙堂与江湖之间,最需要的是能够回到人的内心和个体的权利本身。这也让我不由得想起亨利·梭罗,他既能回到瓦尔登湖那样的自然江湖,又能独立并守卫自己的权利江湖,而且他的努力与修为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个体价值高扬于庙堂之上,即有所谓“公民不服从”的权利。在实现普选的公民社会,我想每位公民其实已经“从江湖到庙堂”了。
【科举与革命】
熊培云:古代人通过科举“考公务员”。科举制度是读书人不入江湖而跻身庙堂的重要途径。黄仁宇先生说中国“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即是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即是成千上万的农民,其组织以淳朴雷同为主。中层机构筒单……上下的联系,倚靠科举制度”。黄先生称之为“潜水艇夹肉面包”(Submarine Sandwich),您如何看科举存废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王学泰:虽然科举制度始于隋唐,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