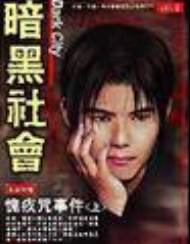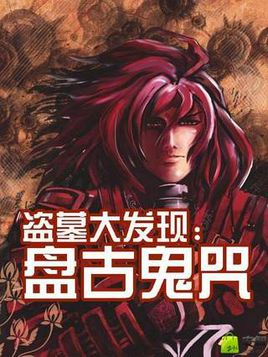重新发现社会-第3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的道路,以更加理性务实的态度寻找自己的现代性时,必定会经历一个重新发现传统的过程。
进一步说,在人类文明进程中,传统不仅是不断地被发明创造出来的,同样需要不断地被发现出来。如果说胡适的思想重新被发现是百年来中国政治思想由极端走向理性的一个脚注,那么中国重新发现墨子更意味着今日中国人在重新寻找自己文明的坐标时,跨越两千年皇权上接到了先秦——一个和五四时期一样充满自由气息的时代。
【谁是新青年?】
1915年9月,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即后来的《新青年》)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感叹中国人的衰老:在中国,人多以“少年老成”相谓,而在英美等国家,却以“年长而勿衰(Keep young while growing old)”相勖。“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
当我们重新回味这段话时,不难发现,在早年陈独秀身上所具有的某种改良倾向——新陈代谢必然是有序的、渐进的,是“天然淘汰之途”,而非“美丽新世界”里所写的那样急风骤雨般制造“新人”或“新青年”。
谈到实证主义时,陈独秀表示:“举凡政治之所营,教育之所期,文学技术之所风尚,万马奔驰,无不齐集于厚生利用之一途。一切虚文空想之无裨于现实生活者,吐弃殆尽。……若事之无利于个人或社会现实生活者,皆虚文也,诳人之事也。诳人之事,虽祖宗之所遗留,圣贤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会之所崇尚,皆一文不值也!”由此可见,在陈独秀眼里,政治的终极目的是生活,是厚生利用,而非其他虚无的宏大涟想与道德说教。
不可否认的是,在经过二十世纪诸多波折之后,时至今日,生活文明已被视做政治文明的重要标杆。关于这一点,即使是在若干年以前,我们亦可从米兰·昆德拉的小说中找到证据。在《生命不可承受之轻》中,昆德拉说,那些行进在大街上的捷克人民手里高举某个主义万岁的标语,而喊在他们心里的没有写出来的口号却是“生活万岁”。从某种意义上说,承认“生活万岁”,就是从集体自负回到人的内心与本性;让极端的革命狂热回到脚踏实地的改良,让削足适履的政治从此服务于人的生活。所谓政治当为人所利用,而非人为政治所奴役。
同样,在谈到科学时,陈独秀抨击了那些不切实际的臆想。“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的中国人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急起直追。“无常识之思维,无理由之信仰,欲根治之,厥为科学……夫以科学说明真理,事事求诸证实,较之想象武断之所为,其步度诚缓,然其步步皆踏实地,不若幻想突飞者之终无寸进也。”
上世纪初,中国正面临一场文化与政治上的危机,在选择疾风骤雨的革命与润物无声的改良之间,陈独秀最终选择了前者。显然,陈独秀的家长式作风与激进的态度使他在参与社会改良时同样保持着一种“舍我其谁”“唯我独尊”的立场。应该看到的是,在几十年后的新启蒙运动中,当中国知识分子群起要求“告别革命”时,其所告别的,并非带来社会进步的革命本身,而是在革命无序中滋生的“真理病”与强制。因为“真理”及其排他性的存在,在一定条件下,原来的进步力量会迅速转向保守甚至反动。关于这一点,在二十世纪初期自由辩论的黄金时期,陈独秀已经表露无遗。
1917年1月1日,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在《新青年》上发表、因此引发了一场意义深远的“白话文学运动”。在这场争论中,主持《新青年》的陈独秀的立场是“(白话文运动)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之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而胡适所持的自由立场是,“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应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即熟,是非自明。吾辈主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绝不敢以吾辈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新青年》,第3卷第3号)在胡适看来,陈独秀之“不容”恰恰是中国政治与社会败落的症结所在,是迫切需要改进的地方。
1925年12月,北京发生《晨报》报馆被焚事件。时已成为“新青年领袖”的陈独秀对此回答竟是一个“该”字。这个态度让自由的胡适一时寝食难安。在给陈独秀的信中胡适表示,争自由的唯一原理是:“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众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众人之所非未必真非。争自由的唯一理由,换句话说,就是要大家容忍异己的意见和信仰。凡不承认异己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争自由,就不配谈自由。”(《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0册)
在胡适看来,没有宽容精神的新青年就不是真正的新青年,他们注定会重拾旧势力的道路。诚如是,有同乡同人之谊的陈独秀不但无法做朋友,“简直要做仇敌了”。
无疑,胡适之于近现代中国的贡献,在于倡言精神独立与思想宽容。胡适提倡“做学问要于不疑处有疑,待人要于有疑处不疑”“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1926年5月,当鲁迅、周作人和陈源之间的论争转向彼此对骂时,胡适“怀着无限的友谊的好意,无限的希望”,致信给鲁迅、周作人和陈源:“……三位这八九个月的深仇也似的笔战是朋友中最可惋惜的事……我最怕的是一个猜疑、冷酷、不容忍的社会。我深深感觉你们的笔战里双方都含有一点不容忍的态度,所以不知不觉地影响了不少的少年朋友,暗示他们朝着冷酷、不容忍的方向走。”(《胡适书信集》,上册)
如胡适所说,二十年代,“不容忍的空气充满了国中”。这一切与“五四运动总同令”陈独秀等人启蒙下成长起来的“新青年”不无关系——“并不是旧势力的不容忍,他们早已没有摧残异己的能力了,而是来自一批自命为最新人物的人”。胡适所担心的是,“如果一个社会不容忍的风气造成之后,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更惨酷的社会,我们爱自由争自由的人怕没有立足容身之地了”。(《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笫20册)
然而,早在1915年,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如此诠释个体解放与精神自由:“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盖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
显然,陈独秀早先的这一主张与胡适奔走呼号的自由思想不谋而合:“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1930年)
孰料,当陈独秀成为新青年们景仰的导师之时,他已自封为真理的绝对拥有者,以致当日有志同道合者拂袖而去。二三十年代,胡适偎心挂怀的是,只有每个人争自由,中国才会有自由;与此相反,陈独秀认为只有跟着陈独秀本人争自由,中国才会有真正的自由。
自由迟早是要到来的,然而不容辩说。在写给陈独秀的信里,胡适坚持即使是一个常识,每个人都应有机会自己判断,而非通过强力灌输。如其所言:“我的根本信仰是别人有尝试的自由”。
英人卡尔·波普尔有言,多见一只白天鹅不能证明所有天鹅是白的,因为只要有一只其他颜色的天鹅出现,“天鹅皆白色”这个命题就会被推翻。既然谁也无法保证此“真理的白天鹅”可以永远不被证伪,那么“非真理”“非主流”的价值就有自我尝试的权利。换言之,人类没有一劳永逸的真理,只有基于经验与创造而生的源源不断的知识,人类只能“通过知识寻求解放”。
1920年9月,陈独秀发表《论政治》,公开与年轻十二岁的胡适决裂。九十年前的这场风云际会不欢而散,新文化运动从此绑上了政治的马车冲出了原有的跑道,其本质上是中国知识精英关于真理标准的一次分道扬镳。如果说陈独秀曾经代表着与帝王中国决裂的新青年的勇气,胡适则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新青年的灵魂。陈独秀一生颠沛流离,思想多有流变,至晚年重新回归五四时期民主、科学的立场,而胡适一以贯之地坚持自己最初的关于自由与容忍的理想。
亲历了二十世纪的风雨洗礼与返朴归真的中国人渐渐知道,真正政治文明必定奠基于生活文明之上。没有生活文明,政治文明就会失之空洞与轻佻。应该说,今日中国人多以生活诉求(而非政治诉求)为旗,为自己的权利奔走,它非吊诡而是真实地表明了中国的进步。正是这种对生活文明的琐碎而真实、循序渐进的追求与争取,在一点点锻炼中国的政治文明,推动中国积百年之沉郁的转型。
“庸俗革命家”与“增量历史”
曾经读过一本名为《蚂蚁的革命》(La revolution des Fourmis)的法国小说。书中提到的“庸俗革命家”这个概念给了我非常深刻的印象。所谓“庸俗革命家”,就是那种不论付出什么代价、采取什么手段,也要在其有生之年见到所有革命成果的人。不可否认,人类历史上的许多社会运动,由最初的革命走向最后的极端,便是在这种心理驱动下发生的。关于这一点,法国大革命无疑是最好的解剖样本。
【“没有本钱的生意”】
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无疑是世界历史上的划时代的大事件。转年,柏克发表《法国革命论》,猛烈地攻击法国大革命的原则。你也许会说,柏克带有长久以来英国人对于法国人的偏见。但不可否定,柏克在书中提到的一些观点有着极其重要的时代内涵。柏克反对法国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这场革命不是来自生活经验,来自现实生活,而是以抽象的理性观念为基础。在柏克看来,法国大革命所标榜的“自由”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抽象概念,那只能造成灾难。真正的自由乃是现实生活中的具体自由,是符合自然秩序的自由。“高谈一个人对食物和药品的抽象权利又有什么用呢?问题在于怎样取得和支配它们。”
和卢梭主张的“天赋人权”不同的是,柏克更注重“人赋人权”。柏克并不否定“天赋人权”里人权的价值,但是认为它更多只是价值论上的,而非方法论的。天赋是先天的,是既定的,而人赋是后天的,是需要生长培育的。在此意义上,柏克所谓“人赋人权”,既包括价值论,又包括方法论。如胡适所主张,考虑到人的局限性与社会的复杂性,只能是一点一滴地建设。
对于流行于革命岁月的乌托邦主义,桕克认为它们也是靠不住的。“人性是错综复杂的;社会的目标也有着最大可能的复杂性;因此之故,权力就没有一种单纯的意图或者取向是能够适合于人性或者人事的性质的。当我听说有任何新的政治体制在寻求并且炫耀自己设计的简捷性的时候,我就毫不怀疑可以断定设计者们对自己的行当是全然无知,或者根本就不懂得自己的责任。”“他们不尊重别人的智慧;他们以对自己的过分自信取代了这种尊重。对于他们,一种事物的规格只要是旧的,就有足够的理由被毁掉。至于匆促建立起来的新规格,他们也丝毫不关心它的持续……”在柏克看来,当理论家们所号称的权利走向极端,“这些政治的宏伟目标就是要使法国变形,从一个伟大的王国变为一个大赌场;把它的居民变为一个赌徒的民族……”
同样是在《法国革命论》一书中,柏克这样写道;“你们(指大革命时期的法国人)开始得很糟糕,因为你们是以鄙视属于你们的一切事物而开始的。你们是在做没有本钱的生意……尊敬你们的前人,你们也就学会了尊重你们自己。你们就不会认定法国人是一个昨天的民族,是一个天生低贱、奴颜婢膝的可怜虫的民族,直到1789年的解放为止。”
【什么时候4等于3?】
4等于3,你相信吗?如果你不相信,我可以用数学的方法证明给你看。
具体解答步骚如下:
第一步:假设A+B=C;
第二步:推出(4A…3A)+(4B…3B)=4C…3C;
第三步:整理方程式4A+4B…4C=3A+3B…3C;
第四步:提取公因式4(A+B…C)=3(A+B…C);
第五步:去掉同类项(A+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