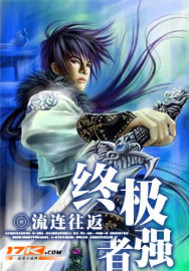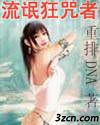奠基者-第1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年轻人于是争先恐后地回答。有的说地质勘探就是千里眼,一眼能看到地底下的矿藏;有的说地质勘探就是先锋官,祖国建设我们走在最前边。
刘少奇笑笑,猛吸了一口烟,然后习惯地踱起步来:“地质勘探嘛——我打个比喻吧!就像我们过去打游击,扛着枪,钻山洞,穿森林,长年在野外,吃饭、穿衣……都是很大困难。今天的地质勘探工作和这差不多,也要跋山涉水,吃不好饭,睡不好觉,吃很多很多的苦……可是我们为什么要吃苦呢?”
没有回音,只有一双双聚精会神的目光和沙沙作响的笔记声。
“过去,我们那一代人是革命战争时期的游击队。吃苦,为的是打出一个新中国。今天,你们去吃苦,是为了建设美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少奇同志拍了拍坐在一边的老将军何长工,把声音提高了一倍,“打游击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你们知道这位老将军的腿是怎么跛的吗?就是打游击留下的残疾!现在轮到你们打游击去了,你们怕吗?怕苦吗?怕献出生命吗?”
“不怕!”同学们齐声回答。
“对,不要怕嘛!因为你们是建设时期的游击队、侦察兵、先锋队!”
“哗——”那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在场的年轻大学生们以这特殊方式回报领袖对自己的崇高褒奖与希望。
“过几天,同学们要奔赴四面八方,为祖国找宝,打游击去。我很想送给你们一件礼物。”少奇同志的话使肃穆、庄严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
“刘伯伯,您给我们讲了三个小时,就是最好的礼物了!”有同学兴奋地站起来说。
“不,礼物是一定要送的,否则有人会哭鼻子的!”少奇诙谐的话,引来一阵阵哈哈欢笑,“对,我把(“文)伏罗希洛(“人)夫同志给我(“书)的猎枪送给(“屋)你们。当年我在打游击时很想得到一支枪,但没有。现在你们打游击了,应该有支枪。有枪就不怕危险了!”
“可以赶跑野外的老虎和狼嘛!”何长工的插话又让同学们捧腹大笑。
这是多么幸福与难忘的时刻。在我采访的那些当年在余秋里领导下参加过大庆油田会战的老一代石油勘探队员中,他们许多人就是因为被毛泽东、刘少奇等领袖们的一个题词、一枝猎枪或一次握手而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艰苦的石油事业。
余秋里在拿着上面两张英勇牺牲的年轻女队长的照片的同时,他还知道另外两名石油勘探地质队的男队员确实是带着猎枪出发上野外的,可他们没有回得来——那是115队的一个送水的骆驼队的驼员,年仅18岁。那天晚上暴风刮来,十余峰骆驼跑了,这位队员就带上猎枪顺着骆驼留下的新鲜脚印去追踪。可两天后队上的同志们仍没等到他回来。队长急了,发动全队人结群到处寻找,最后在距队部200多公里的山岭边发现了骆驼,而同时也在距骆驼群50来公里地方的一个黄色土堆前发现了这位小队员的尸体——那儿无水无草更无人,只有一望无际的荒漠。那小队员的胸前布满了他自己的指痕,那是他口渴、胸闷、难忍而用自己的手指抓留下的伤痕。队友们见此景,一拥而上抱住其尸体,个个号啕大哭……与115队相邻的另一个地质勘探队的一名男队员却因出去为同志们拉水而一去未归。队友们找遍了整个大盐滩,除找到点点遗物外连遗体都未见……
这就是昨天的建设者。这就是余秋里领导下的石油战斗中的战士们。
松辽找油战斗比这要惨烈得多!我从好几个人那儿知道,余秋里曾经做过这样的心理准备:松辽找油大战中或许要牺牲几千人……
现在不是谈论牺牲多少人的问题,而是油在哪儿的事。
油,能在哪儿呢?
余秋里已有些日子在为松辽的找油前景焦虑和着急了。自他上任石油部长后,部里已经向松辽平原派去了一支又一支队伍。康世恩从地质业务的角度告诉他:要想在一个不见油砂露头、不见明显地质构造、又不见任何前人留下的原始资料的“三无”地区逮住“地下大敌人”,就必须不断加强那儿的普查和勘探队伍。余秋里是谁?什么仗没打过?在用兵问题上,他有娴熟的指挥艺术。
那个后来为大庆油田发现作出特殊贡献的西安地质调查处的杨继良,被抽调往松辽石油勘探处途中,石油部机关有人托他带一枚“石油部松辽石油勘探处”的图章,说是那边宋世宽他们正等着用章“开张”工作呢!杨继良兴冲冲地带着公章找到当时还在长春的宋世宽他们。
“呃,宋处长,我把章给你带来了。”杨继良一直是名技术干部,他哪见过“处级”大公章呀?从北京出发的一路上他视这枚“石油部松辽石油勘探处”的大章比自己生命还宝贵。年轻的小媳妇几次在北行的火车上让他帮着照看一下随行的几个包裹,他杨继良双手插在衣袋里就是不理不睬,一副大少爷的架势,惹急了他瞪大眼珠,朝小媳妇吼一声:“你以为我闲着呢啊?”看小媳妇愣在一边,他就悄悄露一下口袋里的那枚红色公章给她看看:“明白吗,知道我在干啥了?”小媳妇讨个没趣,只好自个儿大包小包地独自看管。
“哈哈哈,杨地质师,你的那枚已经要进历史博物馆啦!”宋世宽朝新来报到的杨继良直乐。杨继良被笑得双眼发愣:“咋,你们连公章都可以不要啦?”
“余部长已经把我们松辽石油勘探处提升为松辽石油勘探局啦,他宋处长现在是宋局长啦!”有人告诉杨继良。
“这、这不到一个星期时间就、就……”杨继良拿着那枚他视为生命的公章,怎么也转不过弯来。
“小杨同志,余部长等部里领导每天都在等着我们松辽这边的找油进展,如今松辽大地上的石油勘探一天一个变化。你一年前要是到这儿来,我们石油部的地质勘探人员加起来也就几十个人,现在已经有一千多人了,余部长他们还在不断往这儿派人哪!这说明啥?说明我们松辽方面能不能早日找到油,成为北京方面天天都在盼望的大事啊!年轻人,甩开膀子痛痛快快干吧!”宋世宽一番话,说得初来乍到的杨继良热血沸腾。
杨继良在这之前没有见过部长余秋里,他区区小地质队员,自然不知身经百战的将军是如何指挥一个又一个大战役的。但“公章事件”让他多少了解自己的部长原来真的是“干大事”的人啊!
余秋里那个时候当然更不知道杨继良是何人。而他关心的是如何迅速打开一直在雾里观花的松辽找油局面。所谓“雾里观花”,就是开始外国人一直说,中国“贫油”,后来地质学家们——包括苏联大专家们都说“东北有油”、“松辽前景可观”,再后来地质部何长工先是送来韩景行他们到野外采集到的油砂,再后来是“南17孔”的岩芯含油喜讯,而石油部自己的队伍也相继获得一份份“松辽有油显示”报告,可油到底在哪儿?余秋里要的不是两军对峙前那些侦察员向他报告的有关敌方的捕风捉影的虚玩意。
“‘有预料,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有光明。’这话我不反对,可我更想能逮到就早逮到,逮到了就早吃掉!”秦老胡同夜深人静后,李人俊他们几个副部长都走了,秘书们也一个个在隔壁的房间睡倒时,会客厅里就剩下余秋里和康世恩时,余秋里把脚上的鞋子往边上一甩,双腿盘在屁股下面,拿起烟盒朝康世恩甩过一支烟后,张大嘴巴、仰着头这样说。
康世恩笑了,说:“根据目前已经掌握的第一手资料,以及我跟苏联专家分析的结果看,逮到‘大敌人’是早晚的事,到时候我还担心你余部长吃不掉呢!”
余秋里“噌”地又从木椅上放下脚,光着在地上来回走起来,然后突然停在康世恩面前,大声说:“那我们俩再回部队去,向主席提个请求,让我们俩联手跟台湾的老蒋干一仗!到时把所有的大炮、军舰,都他妈的装满装足我们的油,然后直杀那边去,省得老蒋和美国佬总在那边吵吵嚷嚷的,害得毛主席和全国人民不得安宁。”
康世恩又笑了:“怕真到那时,毛主席还是不会让我们回部队的。国家建设那么快,用油的地方太多,他老人家还不希望我们再多逮住几个‘大敌人’嘛?”
余秋里耸耸肩,甩一甩那只空洞洞的左袖,自己也笑了:“那倒是。”
这时,秘书手持一份电报进屋:“报告部长,松辽那边来电说,松基一井今天正式开钻了。”
余秋里和康世恩几乎同时伸手捏住电报,兴奋地:“好啊,终于要看结果了!”
“走!”只见余秋里的右胳膊向前一甩,便直奔院子外。
秘书着急地:“部长您干啥呀?”
“回部里去呀!”黑糊糊的院子外传来爽脆的声音。
康世恩拉着秘书,笑:“走吧,你还不知道他的脾气。今天晚上让他睡也睡不着了。我们上部里给松辽那边打长途问问情况!”
古城北京,东方欲晓,一轮霞光正透过天安门城楼,射向四方。
一辆苏式轿车越过安定门时,车内传出余秋里的声音:“老康啊,松基一井是我们松辽勘探战役的第一炮,关系重大,这个钻井队是哪儿派去的?”
“是玉门那边调去的32118钻井队。这是我们的王牌钻机了,苏式的超级深井钻机,能打四五千米呢!”这是康世恩的声音。
“不是一共调了两个钻井队吗?”
“是,还有一个钻井队是32115队。这个队的任务是准备打松基二井,过些日子也马上要开工了。”
“噢。这两口基井都很重要,但第一口井意义更大些,我建议派个得力的队长去!”
“好的,我把你的意见马上转告给松辽局。”
余秋里和康世恩在车内的这段对话是俩人正准备赴玉门和新疆等西北油田调查考察之前说的。
搞石油勘探的人都知道,要探明地下生储石油的情况,就先得钻上那么几口基准井。大松辽平原,从南到北,从东至西,茫茫几十万平方公里,一亿万年前,这儿曾是一个风景秀美如画的水乡泽国,气候温暖潮湿,河湖的四周岸头,树木参天,绿阴成林……随着亿万年的地质变化,这里的湖河以及在此滋育成长的生物也跟着沉积在厚厚的封尘之中,折叠成松辽盆地这本叠叠层层的地质构造巨著。基准井的目的就是通过钻探获得这部“巨著”的每一个时代留下的科学符号,也就是说科学家们通过钻探手段取上的岩芯来判断地下宝藏到底有没有、在哪个位置、有多少储量。松辽平原找油初期,根据石油部和地质部的约定,两个部门在地质调查和地震物探方面的工作有分有合,主要以地质部为主,而在钻探和施工方面则主要由石油部的队伍来完成。基准井决定着当时松辽找油的直接前景,加上只有石油部才具备深井钻探的技术与设备条件,因此在两个部门的技术人员确定基准井方案后,石油部迅速调集了两个“王牌”钻井队来到松辽。
这时间应是在余秋里执掌石油部帅印后首次赴四川前后与康世恩共同在东北地区布下的一着战略棋子。
松辽第一口基准井确定在黑龙江安达县建设乡,距安达县城47公里,简称松基一号井。松基二号井确定在松辽盆地的东南部的隆起区域,即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登娄库构造上。这两口基准井说是重要,但当时石油部在松辽前线工作的技术力量少得可怜。像承担基准井研究队队长的钟其权、参与确定基准井位置的地质工程师杨继良他们,都才是二十四五岁的年轻人。余秋里有些不放心,让康世恩从石油部研究院调了资历相对老一些的余伯良等人过去。后来在关键时刻又搬出了翁文波这样的大家坐镇前线,进行技术决策,当然康世恩在这样的重大技术问题上是跑不了的。
何长工在松辽基准井准备开工之前,向余秋里叫苦,说秋里你虽来石油部几天,但论装备我还得叫你石油部是“老大哥”,说地质部搞普查和打浅井没问题,可打几千米的深井,连台机器都没有。这份功劳你余秋里一个人捞着,我何长工尽管很眼红,但也只能望尘莫及。
余秋里新来乍到,很一阵得意,可当他一问康世恩,心里也有些凉:原来石油部的家底也可怜得很。比如32118队,只有两名正副队长和4个钻井班,其他方面的干部和工人——应该还配有非常重要的钻井、地质和泥浆技术员可都没有。32118队原来在玉门油田,接到命令转赴几千里之外的松辽平原后,同志们下火车一看,要路没路,要运输车没运输车,要吊车没吊车,这咋办?几十吨重的钻探设备怎么才能搬到四五十公里之外的目的地呢?
“愣着干啥?没有吊车还没有肩膀吗?学着我的样——抬!”八路军骑兵连长出身的老队长李怀德将外衣一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