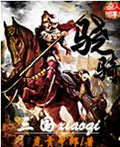骁骑-第86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还真别说,经过李利这么一拉一摁、再拍两下肩膀,刘璋彻底清醒了,并且脸上的惊骇惶恐之色随之消退,渐渐冷静下来。尽管刘璋心里仍是如惊涛骇浪般的震惊不已,但至少他的神色趋于正常,不复方才的狼狈不堪,强作镇定,作出一州之主应有的矜持与尊严。
这是因为堂内此刻还有很多人,堂下坐着张松和董和,吴懿站在门后,阶下两侧还站着四名侍女,当然他身边还坐着“不速之客”李利李文昌。对于素来极重颜面的刘璋来说,不管置身于何种环境之中都不能不顾面皮,即使是打肿脸充胖子也要装下去,不能丢了面子,失了体统。
所以刘璋此时很镇定,很冷静,神色如常,坐的端端正正,哪有半点惊慌失措的样子。唯一美中不足的是,他端着茶盅的右手不住地发抖,以致杯中的茶水洒了出来,手背上满是茶水,浸湿了衣袖。
“别端着了,这里没有外人,你端着架子给谁看呐?”看着刘璋装模作样的故作镇定,李利忍不住笑了。
随即他招手示意侍女上前擦掉刘璋手上的茶渍,重新倒上一杯茶,送到刘璋手里,笑道:“喝口水,压压惊。这么多年了,你还是一点没变,死要面子活受罪。在我面前,你不用活得这么累,随意就好,只要自己觉得舒服,便无须刻意约束自己。在这个世上,没有人会因为你礼数周全便得到尊敬,也不会因为你举止有度、温文儒雅便令人敬畏,真正能让大多数人敬畏的只有自身实力。”这是李利的肺腑之言,但是落在刘璋耳朵里却是另一番感受,一种被奚落的感觉油然而生。
但见刘璋的脸颊顿时一红,浮现出无法掩饰的愠色,低垂着头,眸子中闪过恼羞成怒之色。怎奈迫于李利就坐在身边,以致他敢怒不敢言,只得生生咽下这口怒气,佯作镇定,强迫自己喜怒不形于色。
少许沉默之后,刘璋再次端起茶盅将大半杯已经微凉的茶水一饮而尽,借着凉茶让自己冷静下来。慢慢放下茶盅,他缓缓抬起头,正视着面带微笑的李利,平心静气地道:“不知兄长何时驾临成都的,事先何不言语一声,也好让小弟早作准备,略尽地主之谊?”这是典型的敷衍托词,避重就轻,藉此掩饰他心中的恐慌。不过刘璋的这句“兄长”说的很顺溜,开口便来,似乎已经形成了习惯,成为一种固有称呼。
但事实上,刘璋比李利年长许多,彼此相差十岁,近乎两代人的年龄差距;就如同李利与其叔父李傕的年龄差距一样,李傕年长他十三岁。是以刘璋和李利之间的称呼有些于理不合,不伦不类,可是这种称呼却是刘璋主动提出来的,声称“不拘俗礼,达者为先”,由此确立了他们之间称兄道弟,的友情关系。
说起来,这是七年前发生的事。当时刘璋兄弟三人都在长安为质,其兄刘范和刘诞二人时任御史中丞,相当活跃,与朝中老臣交往甚密,伺机制造混乱,蓄意挑起朝中百官与李傕、李利叔侄之间的矛盾,试图辅佐汉帝刘协夺回军政大权,匡扶朝纲,中兴汉室。而时任议郎的刘璋则整日流连于烟花柳巷之中,贪恋酒色,钟情于诗赋作画,与刘范、刘诞二人划清界线,泾渭分明,兄弟之间各行其是,背道而驰。
有一次,李利乔装前往青楼,碰巧遇到了刘璋,当时刘璋也像今夜这般酒醉微醺,迷迷糊糊之中便与李利攀谈起来。不承想,两人话语投机,相谈甚欢,尤其是谈及风月之事更是气味相投,颇有一见如故之感。第二天醒来,刘璋方知昨夜与他大谈风月、互诉风流韵事的正是执掌西凉军权,执天下牛耳的卫将军李利。于是刘璋权衡再三,终究决定攀上李利这棵大树,即使不能获得实实在在的好处,至少可以保全性命。
就这样,刘璋携带重礼求见李利,言语谦卑,曲意迎合,与李利攀上了交情。自此以后,刘璋便时常前去卫将军府“串门、靠近乎”,走动十分频繁;久而久之,便与李利的交情愈发深厚,随即他顺杆往上爬,尊称李利为兄,私下里与李利称兄道弟。这份情谊持续了一年多时间,而他真正赢得李利认可的时间,却是离开长安之前的三个月。那三个月里,李利经常和他一同饮酒作赋,一起赏舞作画,其间李利曾向他承诺,不久之后便护送他前往益州,继承益州牧之位。
果然,李利没有食言,言出必行,一诺千金,三个月后便兑现了承诺。于秘密前往中原游历之前,李利命人将他护送至益州,并助他坐上益州牧之位,随后李利游历归来,又将刘范和刘诞二人于长乐宫殿前当众斩首。自此,彻底扫清了刘璋即位益州牧的所有障碍,让他成为继承益州牧的唯一人选,无形中攘助他坐稳了益州牧的位子,提领益州九郡。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青春易逝,转眼间六年过去了。
当年正值而立之年的刘璋如今已步入中年,而李利也从朝气蓬发、挥斥方遒的年纪,日趋成熟,并且权势越来越盛,已然成为执掌天下兵马大权的大将军,数年间便占据了半壁江山,手握近百万雄兵,成为叱咤风云的强势诸侯,无可争议的天下第一霸主。
(……)
第161章 绕指柔,大势所趋
刘璋强作镇定,平心定气地道:“此番兄长莅临成都,事先何不言语一声,也好让小弟早作准备,略尽地主之谊?”
李利闻言心下了然,刘璋这番话实为敷衍托词,言不由衷,听着亲近,实则拒人于千里之外,颇有诘责之意。;
不过刘璋能够迅速平复心神,还能心平气和地寒暄敷衍,倒是有些出乎李利的预料之外,让他心生警觉,当即摒弃轻视之心,将他放在与自己同等的高度,真正重视起来。
诚然,此时的刘璋与六年前的落魄文官相比,差距之大何止千里,俨然今非昔比,不可同日而语。
六年前,刘璋身在长安为质子,虽有官职,却是身不由己,领着微薄的俸禄,终日无所事事。然而离开长安之后,他便摇身一变,承袭刘焉的益州牧之位,提领益州九郡,牧守一方,虽未明目张胆的割据自立,可实际上却是**于汉庭之外的“**王国”,而且是物阜民丰的“天府之国”。
整整六年的州牧高位,治下数百万人口,手握十几万大军,颐指气使,挥斥方遒。置身于这种环境之中,如果说刘璋还能一点不变,那么他早就被他人取而代之,身首异处了。
人都是随着环境的改变而改变的,刘璋自然也不例外。
刘璋虽然暗弱且多疑,可他并不愚笨。恰恰相反,他有着远超常人的聪明智慧,可惜的是他生平之志不在治理州郡和乱世纷争之上。而是醉心于吟诗作赋,痴迷于琴棋书画。即便如此,长期的上位者生涯还是让他在不知不觉中快速成长。识人用人,驾驭文臣武将,熟识政务和军事,进而坐观天下局势。
他能够清晰地认识到自身的现实处境,对未来的前途命运也有着某些预见性,知道将来要面对什么,自己又有什么样的结局。奈何他生性惫懒。对现状很满意,即使知道这种安逸的日子不会长久,却不愿意尝试改变。依旧浑浑噩噩,得过且过。
但是,刘璋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天竟然来得如此之快,快得让他措手不及。快得让他毫无准备。快得让他接受不了,却又无可奈何。
是以他明明听出李利方才提起“自身实力”时的潜在含义,隐含逼宫之意,但他却佯作不知,避重就轻,转而寒暄客套起来。他之所以这么做,无非是借此掩饰他内心的惶恐不安,掩饰他的不知所措。掩饰他不甘认命的挣扎,试图拖延时间。给他留一点思考的空间,从而保全自己仅剩不多的可怜的尊严。
稍事沉默之中,李利意识到刘璋之所以托词敷衍,其实是他此刻仍旧心存侥幸,存有躲避心理,不甘心就此让出益州,将刘氏基业和江山拱手送于他李利。
想都不用想,李利就能猜出刘璋此时内心深处的犹豫和挣扎。
现如今,天下局势已然明朗,李利一家独大,冀州曹操次之,再次是荆州刘表,而后便是他刘璋,排在最末的是江东孙策。这是目前天下仅存的五方势力,西凉李利独占半壁江山,实力之强无以伦比。冀州曹操占据三州之地,实力虽不如李利,却明显强于其他诸侯;而荆州刘表和他刘璋治下的益州实力相当,但荆州军的战力明显高出益州军一大截,是以荆州刘表的实力犹在他之上。
而今李利挥师进取益州,如果没有老贼赵韪发动叛乱,刘璋有信心抵挡李利麾下的西凉军;即便最终仍是斗不过李利,至少可以拖延三年以上的时间,藉此消耗西凉军的军力和物力,为其他诸侯赢得时间,继而出兵蚕食李利的地盘。
按理说,刘璋绝不会做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但是凭着李利对他的了解,刘璋一定会这么做。因为刘璋是汉皇后裔,是刘氏皇族的子孙,骨子里流淌着刘氏宗族的血液,担负着维系皇族正统的义不容辞的重大使命。
在天下半壁江山都落到李利手里的情况下,刘璋绝对不会坐视李利继续做大,更不会拱手让出益州,从而加剧刘氏江山灭亡的速度。为此,他一定会阻止李利的进一步扩张,迟滞李利进取天下的步伐,宁肯血战到底,也不会眼睁睁看着李利一步步夺取大汉十三州,进而黄袍加身,将刘氏江山取而代之,窃取整个天下。
这是身为刘氏皇族应有的觉悟,深藏在骨子里的骄傲,亦是他们这些汉中宗亲无法躲避的命运。无论如何,他们都会竭尽全力保住大汉天下最后一块土地,维护汉皇后裔最后的荣耀。
在这一点上,不用任何人提醒,李利便已心知肚明,并对此深有感触,体会颇深。后世倭寇侵略中华大地,之所以能够抢先占据辽东,借此站稳脚跟,其根源便是某些满清贵族不甘失败,试图垂死挣扎,由此就给了倭寇以可趁之机,打着建立伪满政府的名义,荼毒炎黄大地。直到辽东大地上的劳苦大众不堪其辱,最终奋起反击,从而动摇了倭寇在中华大地上的根基;加之倭寇野心太大,以致多个战场接连失利,最终竹篮打水一场空,全线崩溃,而后夹着尾巴仓惶奔命,滚回海岛,苟延残喘。
千年之后的鞑子尚且冥顽不化,眼下的刘氏皇族焉能心甘情愿的拱手让江山?
然而朝代更迭乃大势所趋,绝非某个人或一小撮人能够阻挡的。挽狂澜于既倒之事并不是没有,但是必须顺势而为,不可倒行逆施,否则力挽狂澜不成,反倒被狂澜摧枯拉朽地连根拔起,亦未可知。
显然,刘璋绝不是力挽狂澜于即倒之人,即便他有此志向,此刻也没有机会了。
自顾不暇,遑论其它?
“季玉有这份心便好,愚兄实感欣慰。”
沉默半晌,就在刘璋小心翼翼地留意着李利的脸色,额头上冒出密密麻麻的汗珠之时,李利终于开口说话了。
“季玉或许还不知道,迄今为止,愚兄已在益州逗留了八个月之久,十几天前便已来到城中。当时季玉帐下大军刚刚击退赵韪叛军,正当季玉下令封锁城池之际,愚兄带着几位妻妾于封城前夜进城,那时我还以为贤弟故意将为兄挡在城外不予相见呢,现在看来全是一场误会。这几日,幸得子远盛情招待,为兄一切安好。闲暇之余,带着你几位嫂子在城里四处走走、看看,倒也惬意。”
说到这里,李利话音一顿,笑眯眯地看着刘璋,夸赞道:“不得不说,贤弟虽然治理州郡尚有些许不足,但是瑕不掩瑜,成都城还是很繁华的;商铺林立,百业兴旺,人口众多,百姓们相对富足,此一节值得称道。”
话锋陡转,李利脸上的笑容随之敛去,正色道:“相对于郡县政务,季玉在境内治安方面着实有些不尽人意,无甚作为。自季玉离开长安至今,已整整六年零两个月,然则季玉提领益州以来,治下时有匪患肆虐,西南南蛮屡屡寇边犯境,劫掠西南郡县,以致自蜀郡以西的各个郡县常年遭受南蛮滋扰,百姓生活困顿,苦不堪言。
可是季玉从未领军征剿南蛮,疏于军务,军械荒废,兵马松弛,由此才会引发此次赵韪拥兵叛乱,以致季玉倾尽全州之兵马鏖战数月方才平定叛乱。这其中有很多教训可以总结,有很多弊端值得深思,而其根源仍在季玉贤弟身上;若是你早作准备,积极操练兵马,加大军力投入,区区南蛮焉敢肆意横行,小小赵韪又能掀起多大的浪花!”
话音未落,不等刘璋接话,李利便继续说道:“然而这一切都已经过去,此番愚兄麾下二十万大军便是特意赶来助贤弟一臂之力,平定益州所有边患和隐患的。贤弟无须紧张,为兄麾下兵马皆是久战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