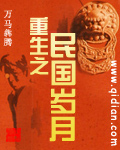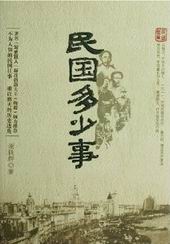细说民国大文人-第21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啊!”鲁迅答:“这叫至死不变!”(据胡適说,他没有说过卷土重来的话。)
鲁迅说:“我的戒酒,吃鱼肝油,以及延长我的生命,倒不尽是为了我的爱人,大半乃是为了我的敌人,要使他的好世界上多留一些缺陷。”
一次,鲁迅对高长虹谈及成仿吾,很是愤慨,高问道:“你还记得那件事情吗?(指鲁迅与成仿吾论战之事)”鲁迅豹眼圆睁地昂然答道:“他要毁灭我,我如何能忘记了呢?”又一次闲聊中,鲁迅说:“只要有成仿吾在艺术之宫的门口,我是不进去的。”
冯乃超与梁实秋发生笔战,鲁迅马上写了一篇《“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的杂文为冯助战。当鲁迅将文章写好后交给冯雪峰时说:“你看,比起乃超来,我真要‘刻薄’得多了。”接着又说:“可是,对付梁实秋这类人,就得这样。……我帮乃超一手,以助他之不足。”
张友松回忆:“有一次我请鲁迅和林语堂等人吃饭,林企图替梁实秋说情,要求鲁迅不要对梁抨击太甚,鲁迅立即以严正的态度答道:‘这个家伙,我怎么能饶他!’”
孔另境说鲁迅:“先生有两个超于常人的特点,其一是恩怨观念十分着重,只要这个人被他骂过,他会永远记住,像陈源教授,事情已经隔十多年了,但他还常常要带到他”,无论是谈天还是写文章;要是这个人确实和他有感情,即使这人现在已十分落伍,他也不肯骂他,倘有人提及此人,他只是笑。“先生另外的一个特点是重气节,疾恶如仇”,他对没有节气的人从不饶恕。某文学家被捕后,鲁迅尽最大努力去营救,但这人后来变节,立即平安无事,鲁迅得知后非常生气,从此再不愿有人提及此人一个字。鲁迅最佩服至死不屈的人,如瞿秋白,所以后来尽心尽力为瞿编撰《海上述林》。
胡风回忆,一次左联约好在某小馆子吃饭,预定由茅盾谈话。到了时间,茅盾不来,周扬便到内山书店请鲁迅救场,鲁迅听罢说:“这很不好。”于是便和周扬一起到小馆子来,和大家闲谈。之后茅盾来了,谈起他的《子夜》和《林家铺子》的创作经验,鲁迅露出不耐烦的神色,说:“我的想法不是这样……”茅盾很是尴尬。
鲁迅有一把不锈钢的小刀子,胡风见后夸赞了一句,临走时,鲁迅将刀子包好递给胡。胡有些不好意思,说:“再不好对周先生的东西说好话了。”鲁迅答:“我不愿送的东西,你再说好话我也不送的。”
张友松与新月派论战,鲁迅支持张,林语堂表示,“双方都是好朋友”,所以他不参加此次笔战。鲁迅冷笑道:“此人一贯如此,不足为奇。”
张友松回忆,某青年总向鲁迅宣传无政府主义,劝说鲁迅不要相信马克思主义,吃过多次闭门羹仍锲而不舍。最后一次,此人又来劝说鲁迅,并苦口婆心说:“我也是出自一片好心哪!”鲁迅气极,声色俱厉地质问道:“你把刀子放在我脖子上,也是一片好心吗?”随即跺脚骂道:“你给我滚出去!”
冯雪峰对鲁迅谈及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鲁迅虽不明确表示怀疑,但谈话间流露出对统一战线内国民党的不以为然。冯对他详细解释,鲁迅听罢说:“我不是别的,就只怕共产党又上当。”
1936年7、8月间,鲁迅谈及自己的病情时说:“大概是有点沉重的,我以前也就自己觉得,但我不愿意让人知道,连许(广平)也在内。这是我的老脾气,不使仇人高兴,也不使爱人苦痛。”
高长虹回忆,凡是革命的,进步的,鲁迅一般都赞成。高曾问他对于马克思主义有什么意见,他说:“怕是对的吧!”不过,他对于青年共产主义者却表示不满,常说他们是皇太子主义,以为明天的天下一定是他们的。
周起应改名周扬后,鲁迅对胡风说:“周扬,以后可以叫他周阿弗了。”因为创造社将德语Aufheben(扬弃)音译为“阿弗赫变”,鲁迅以前两个字“阿弗”代表“扬”;又一次,鲁迅说:“周扬是一定要做芦那卡尔斯基(苏联人民教育委员长)的……”
鲁迅在回答徐懋庸的文中写道:“胡风我先前并不熟识,去年的一天,一位名人,约我谈话了,到得那里,却见驶来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周起应(周扬),还有另两个(指夏衍和阳翰笙),一律洋服,态度轩昂,说是特来通知我:胡风是内奸,官方派来的。我问凭据,则说是得自转向以后的穆木天口中。转向者的言谈,到左联的奉为圣旨,这真使我目瞪口呆。几经问答之后,我的回答是:证据薄弱之极,我不相信!当时自然不欢而散。”
后来,夏衍告诉冯雪峰,此文发表后,周扬、苏灵扬、周立波、沙汀四人拿着棍子准备到茅盾家中打其一顿泄气,为夏所阻。周扬也告诉冯,他当时谁都不恨,只恨茅盾。
半个世纪后的1979年,夏衍在《一些早该忘却而未能忘却的往事》中说,鲁迅说的“一律洋服”并非事实,他当时穿的是一件深灰色骆驼绒袍子;他们当时都三十上下,身体没病,“轩昂”了一点可能是真的,但那是战友间的会面,不自觉“轩昂”一点,也不至犯了什么不敬罪吧。
鲁迅与左联的领导人周扬等人关系不睦,深恶痛绝,以至在见到阔别两年多的冯雪峰时,未及寒喧,劈面就说:“这两年我给他们摆布得可以!”
许广平说:“你的弊病,就是对一些人太过深恶痛绝,简直不愿同在一地呼吸,而对一些人则期望太殷,于是不惜赴汤蹈火,一旦人家不以此种为殊遇而淡漠处之,或以寻常人者对你,则你感觉天鹅绒了。这原因,是由于你的感觉太锐敏太热情,其实世界上你所深恶痛绝的和期望太殷的,走到十字街头,还不是一样吗,而你把十字街头的牛鬼蛇神硬搬到‘象牙之塔’、‘艺术之宫’,这不能不说是小说家,取材失策,如果明了凡有小说材料,都是空中楼阁,自然心平气和了。”
【婚恋】
1906年,在日本留学的鲁迅接到家中急电,称母亲病重,速回。原来,鲁老太太听说鲁迅在日本已经结婚,有人看见他带着妻儿在街上走,忙把他叫回绍兴,为他完婚。
有研究者认为,鲁迅在日本曾有一段恋情,其小诗《无题》“寄意寒星荃不察”句中的“荃”即指其日本恋人。
母亲为鲁迅选择的妻子朱安,当时已二十八岁,比鲁迅大三岁,是传统的旧式女子,三寸金莲,身材矮小,温柔善良,没有文化。
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谈到,鲁迅的婚姻,是上了媒人的当。媒人是鲁老太太的本家妯娌,“人极漂亮能干,有王凤姐之风。平素和鲁老太太也顶讲得来,可是这一件事却做得不十分高明。新人极为矮小,颇有发育不全的样子,这些情形姑媳不会不晓得,却是成心欺骗,这是很对不起人的。”周作人还曾对张铁铮说,朱夫人有侏儒症,发育不全。
鲁迅族叔周冠五在《我的杂忆》中说:“鲁母知道我和鲁迅在通信,就叫我写信劝他,我写信后得到鲁迅回信,他说:要娶朱安姑娘也行,有两个条件:一要放足;二要进学堂。安姑娘思想很古板,回答脚已放不大了,妇女读书不太好,进学堂更不愿意。后来把这情况又告诉鲁迅,结果鲁迅回信很干脆,一口答应了,说几时结婚几时到,于是定局结婚。定了日子,鲁迅果然从日本回国,母亲很诧异,又是高兴又是怀疑,就叫我和鸣山两人当行郎,他穿套袍挂,跪拜非常听话。”
婚礼当日,朱安知道鲁迅不喜欢小脚,为了讨好鲁迅,特地穿了双大鞋子,里面塞了很多棉花。然而,花轿落地,朱安下轿时,鞋却掉了,当场就露了馅。
新婚的第二夜,鲁迅便睡到书房,据鲁迅家的仆人王鹤照说,由于新房印花被的靛青把鲁迅的脸染青了,他很不高兴。按例新婚夫妇要去祠堂祭拜,鲁迅也未去。第四天,鲁迅即东渡日本,继续学业。
鲁迅对这桩婚姻极其厌恶,他曾对好友许寿裳说:“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他说:“朱安是我母亲的太太,不是我的太太。”
在鲁迅几十年的日记中,只有一处提到了朱安:“下午得妇来书,二十二日从丁家弄朱宅发,颇谬。”
在和许广平同居前的21年中,鲁迅和朱安一直过着有名无实的夫妻生活。鲁迅在《随感录四十》中说:“在女性一方面,本来也没有罪,现在是做了旧习惯的牺牲。我们既然自觉着人类的道德……又不能责备异性,也只好陪着做一世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账。”
郁达夫在《回忆鲁迅》中说:“鲁迅虽在冬天,也不穿棉裤,是抑制性欲的意思。他和他的旧式的夫人是不要好的。”
鲁迅在《独身者》中说自己“不得已而过独身生活者”,以致“精神上常不免发生变化”,“表面上因不能不装作纯洁,但内心却终于逃不掉本能的牵掣,不由自主地蠢动着缺憾感的。”但即便如此,他也不能接受朱安。在绍兴任教时,他曾在给许寿棠的信中说:“又翻类书,荟集古逸书数种,此非求学,以代醇酒妇人者也。”
买下八道湾的房子后,鲁迅将母亲从绍兴接到北京居住,朱安也来到北京。晚间就寝时,朱安总会为鲁迅铺好被褥,等着丈夫,然而鲁迅却大发脾气,每每拒朱于门外。母亲曾让朱安给鲁迅做了一条棉裤。朱安做好后,悄然放在鲁迅床上,鲁迅发现后却将棉裤扔出门外。
朱安对鲁迅照顾很是细心,她几次让俞芳、俞藻姐妹不要吵到鲁迅,有时甚至是恳求她们:“大先生回来时,你们不要吵他,让他安安静静写文章。”鲁迅生病时,朱安千方百计做鲁迅平日喜欢吃的菜,让鲁迅开胃。但她自己却从来不舍得吃这些。
俞芳回忆:朱安“个子不高,身材瘦小;脸形狭长,脸色微黄,前额、颧骨均略突出,看上去似带几分病容。眼睛大小适中,但不大有神,而且有些下陷,梳发髻。脚缠得很小,步履缓慢不稳。……平日少言寡语,少带笑容。……操持家务是称职的,节俭持家,空下来就做做针线。她还能炒一手道地的家乡菜……”
鲁迅的客人来访,朱安总是尽心接待,但有时也会考虑不周,而落得个吃力不讨好的境地。一次,鲁迅的学生常维均来访,时值盛夏,天气极热,但朱安不仅泡了两杯热茶,还做了两碗热气腾腾的藕粉送过去。常接过点心,很是尴尬,鲁迅摇头苦笑道:“既然来了,就吃吧,无非是再出一身汗而已。”
荆有麟记载:据鲁迅家中的老妈子讲:“大先生与太太每天只有三句话,早晨太太喊先生起来,先生答应一声‘哼’,太太喊先生吃饭,先生又是‘哼’,晚上先生睡觉迟,太太睡觉早,太太总要问:门关不关?这时节,先生才有一句简单话:‘关’,或者‘不关’,要不,是太太向先生要家用钱。先生才会讲着较多的话。如‘要多少’?或者顺便问一下,什么东西添买不添买?但这种较长的话,一月之中,不过一两次。”
俞芳回忆,为了避免和朱安交谈、接触,鲁迅在自己的床下放了一只无盖的柳条箱,里面放着自己换下需要洗涤的衣裤;而箱盖放在朱安屋门右手边,口朝上,放着鲁迅替换的干净衣服,箱盖和箱子上各盖一块白布。这样鲁迅换洗衣服便不用和朱安交流了。而在俞芳的印象里,她和鲁迅夫妇同住了九个多月,但却不知道他们相互之间当面如何称呼。
张铁铮记载,孙伏园曾在一次座谈会上转述鲁迅所言,全家迁到北京后,一次鲁老太太寿宴,开席前朱安忽然穿戴整齐走出来,跪着对亲友说:“我来周家已许多年,大先生不很理我,但我也不会离开周家,我活着是周家的人,死是周家的鬼,后半生我就是侍奉我的婆母。”说完话,磕了头,退回房去。鲁迅说:“中国的就是妇女很厉害,从此所有的同情,都被他争取了去,大家都批评我不好。”
鲁老太太曾问鲁迅,朱安有什么不好?鲁迅只是摇头,说和她谈不来。他举例说,他有一次告诉朱安,说日本有一种食品很好吃,朱安附和说是的,是的,她也吃过。但这种食品只有日本才有,中国并没有,她怎么能吃到。
1927年,鲁迅与许广平在上海同居,朱安留在北平陪伴婆母。一次,俞芳去西三条看望鲁老太太婆媳,谈及此事,朱安很激动地说:“过去大先生和我不好,我想好好地服侍他,一切顺着他,将来总会好的。”她接着说:“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她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