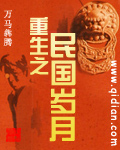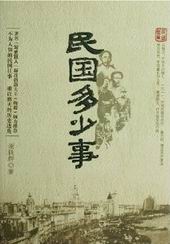细说民国大文人-第10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病重时,弘一法师每天照常工作,他对前来探病的广洽法师说:“你不要问我病好没有,你要问我有没有念佛。”
暮年,弘一大师给自己取名“二一老人”。这两个“一”出自“一事无成人渐老”,以及吴梅村的绝命词“一钱不值何消说”。
【乖僻】
李叔同经常虚言家世或虚写地名。1906年10月4日,日本《国民新闻》记者采访李叔同,记者问道:“您的双亲都在吗?”李答:“都在。”问:“太太呢?”答曰:“没有,是一个人,26岁还是独身。”其实那时李叔同的双亲皆已故世,他也早在18岁时跟俞氏结婚。
刘质平在《弘一上人史略》一文中也说:“(弘一)所写地名、山名、寺名、院名,有曾住者,有未曾住者,有寺名院名臆造者,有全部臆造者,均与笔名同时决定。”
一次,李叔同和欧阳予倩约好了早晨八点在李的寓所见面。两个人的住处距离很远,欧阳予倩因为赶电车迟到了。到了李家,递过名片,欧阳就在门外等候。不多时,李叔同推开窗门对欧阳予倩说:“我和你约的是八点钟,可是你已经过了五分钟,我现在没有工夫了,我们改天再约吧。”说完一点头,关上窗户。欧阳予倩知道他的脾气,只好回去了。
与欧阳予倩有同样遭遇的还有春柳社成员吴我尊。据徐半梅回忆,一次,李叔同约吴某日下午两点到他家中,吴晚了五分钟到达,李叔同不肯开门,只是从窗户对着楼下的吴我尊说:“我约你的,是下午二时,现在时刻已过,恕不开门了,我们再改约日期吧。”吴只能悻悻而返。
徐半梅还回忆,李叔同和日本女子福基婚后,岳母过来探访女儿,临走时天正下雨,于是就向李借一把伞。但李无论如何也不同意,他说:“当初你女儿嫁给我的时候,并没有说过将来丈母娘要借雨伞的。”岳母哭笑不得,只好淋雨回家了。
留日学生韩亮侯回忆,一次,他去听音乐会,在一堆衣着光鲜亮丽的听众中,见到一衣衫褴褛之人,坐在正厅优等座上。他颇觉奇怪,散场后,彼此打招呼,才知道此人也是中国人,叫李叔同。随后,韩随李到李宅做客,发现李居住在一栋漂亮的二层洋房中,房内环壁皆书,屋角放一架钢琴,觉得很是糊涂,仿佛读了一篇浪漫主义的传奇小说。而此时,李叔同已换上崭新的西服,请他一起去附近餐厅吃宵夜。
李鸿梁回忆两级师范任教时的李叔同:“他忽然变为一个很严肃的教师了。灰布长衫,黑布短褂,平底鞋,先后判若两人。在学校里很少见他的面,就是同事房间里好像也不很走动的,教员休息室里也不常去。到上课时,总是挟了书本去上课,下课直接回到房间。走路很迅速,不左右顾盼。冬天衣服穿得很少,床上被子也很薄,严冬并不生火。后来法师告诉我,他的身体不适宜多穿衣服,烤火更是有害,所以他晚年喜住在闽南,就是这个缘故。”
在浙一师任教时,李叔同几乎不与当时主持校务的经亨颐联系,有时请假,也是致电校工,从不直接告知校长和教导主任。
李鸿梁回忆,一次,几个同学找到日籍教师本田利实,请他给每人写一幅书法屏条。本田的文具不完备,大家便建议到李叔同的写字间里去写,本田连说不好。后来有人说李外出了,本田这才答应,还专门安排人负责望风,在扶梯上、走廊上、房门口,都安排了人,并一再嘱咐,李叔同回来须立刻通知他。学生们说:“李先生决不会因此发恼的。”但本田说:“在李先生面前是不可以随便的。李先生的道德文章固然不必说,连日本话也说得那样漂亮,真了不起!”等到字写好了,有人骗他说:“李先生来了。”本田听罢,狼狈起身逃回自己房间。学生们不禁大笑。
弘一法师曾自承:“弟子在家时,实是一个书呆子,未尝用意于世故人情。”
【丹心】
维新变法时,李叔同赞同康梁“老大中华非变法无以图存”的主张,曾私刻一印:“南海康君是吾师”,被当局视为逆党,不得不南下避祸。
1906年,在日本留学的李叔同,感慨故国民气不振,人心已死,挥笔赋七绝以明志:“故国荒凉剧可哀,千年旧学半尘埃。沉沉风雨鸡鸣夜,可有男儿奋袂来?”
辛亥革命成功时,李家的产业遭受了致命的打击,原因是辛亥革命引起的票号倒闭,这使得李家的百万资产荡然无存。但李叔同却写下一曲慷慨激昂的《满江红》,以志庆喜:
“皎皎昆仑,山顶月,有人长啸。看囊底、宝刀如雪,恩仇多少。双手裂开鼷鼠胆,寸金铸出民权脑。算此生不负是男儿,头颅好。
荆轲墓,咸阳道;聂政死,尸骸暴。尽大江东去,余情还绕。魂魄化成精卫鸟,血花溅作红心草。看从今,一担好河山,英雄造。”
弘一法师经常吟诵宋代名臣韩琦的两句诗:“虽惭老圃秋容淡,且看黄花晚节香。”抗战期间,五十四岁的弘一法师到闽南潘山凭吊韩偓墓庐,收集韩的生平资料,嘱咐高文显为韩作传。因为他钦佩韩偓虽遭遇国破家亡的惨痛,却不肯附逆(朱温),仍耿耿孤忠于唐室的情怀。
1937年8月,他在青岛湛山寺作“殉教”横幅题记:“曩居南闽净峰,不避乡匪之难;今居东齐湛山,复值倭寇之警。为护佛门而舍身命,大义所在,何可辞耶?”翌年,他报柳亚子偈云:“亭亭菊一枝,高标矗劲节。云何色殷红,殉教应流血。”表达了为护佛而殉教的决心。
弘一法师从青岛回到厦门时,厦门正处于危亡之中。弘一发愿与危城共存亡。大家劝他避难,他说:“为护法故,不怕炮弹。”他将居室命名为“殉教堂”,以誓护法报国之志。弘一法师致函道友李芳远云:“朽人已于九月二十七日归厦门。近日厦市虽风声稍紧,但朽人为护法故,不避炮弹,誓与厦市共存亡。……吾一生之中,晚节为最要,愿与仁者共勉之。”
是年,厦门市为鼓舞民众的体育精神,募捐拯救四川难民,决定举行第一届全市运动大会。运动会筹委会请弘一法师为大会撰写会歌。弘一欣然答应,并在三月间就把词、谱都写了出来。他在作歌时,又联系到当时日寇猖獗侵略中国的现实,把体育与振奋民心、团结抗暴结合了起来。《厦门第一届运动会会歌》是李叔同为后人留下的最后一首歌曲。
1938年年初,弘一法师先后在晋江、泉州两地开讲《华严经普贤行愿品》,后他又在泉州清尘堂开讲“华严大义”,讲毕,特叮嘱听法者缁素,共诵《行愿品》十万遍,以此功德,回向国土众生,倡佑国运,消弭业灾。一日,法师在斋堂用餐之际,忽然潸然泪下,对身边弟子说:“吾人所食为中华之粟,所饮乃温陵之水,身为佛子,于此之时,不能共纾国难于万一,为我佛如来张点体面,自揣尚不如一只狗子!狗子尚能为主守门,吾人一无所用,而犹腼颜受食,何能无愧于心?”一座僧众,为之肃然。
林长弘回忆,1938年4月的某日,日本舰队司令久仰弘一法师盛名,特登岸寻访法师,并要求法师用日语对话,但法师坚持“在华言华”,拒绝说日语。司令邀请法师到日本,说定以国师之礼奉之,法师答道:“出家人宠辱俱忘,敝国虽穷,爱之弥笃!尤不愿在板荡时离去,纵以身殉教,在所不惜!”
【至孝】
李叔同5岁丧父,此后便与母亲相依为命。李与母亲的感情很好,他对丰子恺说:“我从20岁到26岁之间的五六年,是平生最幸福的时候。此后就是不断的悲哀与忧愁,一直到出家(按:他将出家看成是新生)。”
李叔同的母亲王太夫人是李父的小妾,在家中地位低微,李曾不止一次对人提起“生母很苦”,直到出家多年后他一想到母亲还有余哀。
1905年,王太夫人病逝于上海城南草堂。母亲离世时,李正外出为母亲预置寿木,不在母亲身畔,他终生引以为憾。他曾多次对友人说:“母亲不在的时候,我正在买棺木,没有亲送。我回来,已经不在了!”母亲去世后,他万分悲痛,改名李哀,号哀公,屏谢余务,闭门守哀,感叹“幸福时期已过”。
是年六月,李叔同扶柩北上,到达天津后,二哥李文熙以“外丧不入门”的旧制,不同意王太夫人的灵柩入府,兄弟二人为此而发生龃龉。关于此事,李叔同的三子李端记载:“我祖母的灵柩运回天津以后,我的二伯父借口我祖母是‘外丧’,不能进旧宅的大门。为此,我的父亲不依,和我的二伯父闹了一仗。他们兄弟间公开闹矛盾,这是第一次。经亲友调停说和,才让我祖母的灵柩进了旧宅,后即择日举殡,安葬在新开河边张兴庄以北的李氏祖茔内。”
李叔同痛恨旧制,决定采用西式丧仪为母亲举行追悼会。他在告知亲友的《哀启》中写道:“我国丧仪,繁文缛节,俚俗已甚,李叔同君广平,愿力祛其旧。爱与同人商酌,据东西各国追悼会之例,略为变通。”启文中说明,免收一切致丧礼物,如呢缎轴幛、纸箱扎彩、银钱洋钱等,只收取诗文、联句、花圈、花牌等;免除吊唁旧仪,改行鞠躬礼;丧仪有开会、致哀辞、唱哀歌、献花、行鞠躬礼等几个过程。全家人穿黑色丧服,演唱哀歌时,由李叔同亲自弹奏钢琴伴奏。李家还为吊唁宾客准备有西餐。天津人皆称:“李三爷办了一件奇事!”
出家后,李叔同斩断一切尘世情缘,唯独对母亲的感情难以割舍。他在《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一文中说,1918年正月十五日他皈依佛门,“二月初那天,是我母亲的忌日,于是我先两天就到虎跑去,在那边诵了三天的《地藏经》,为我的母亲回向。”此后每逢在亡母重要的冥诞,他便书写过《地藏经》或地藏忏仪,以此功德,回向亡母。
1930年,天台静权法师在金仙寺讲《地藏经》两个月,静权将经义与中国的孝道联系起来,提醒听法之人,对于父母的生养之恩更当深铭于心。弘一法师前去听法,从未缺席。亦幻法师回忆:“静权法师从经义演绎到孝思在中国伦理学上之重要的时候,一师当着大众哽咽涕泣如雨,全体听众无不愕然惊惧。座上讲师亦弄得目瞪口呆,不敢讲下去。后来我才知滚热的泪水是他追念母爱的天性流露,并不是什么人在触犯他伤心。”亦幻深受震动,他自出家以来,因惧俗累,对于在家的母亲极少过问,自觉惭愧,此后即开始照拂母亲的晚年生活。
【情爱】
天津梆子名伶杨翠喜是第一个走进李叔同心扉的女子。李叔同对杨翠喜极为倾心,每晚都去为杨捧场,散戏后还提着灯笼送她回家。闲暇时,李叔同为杨翠喜解说戏曲的历史背景,并指导她唱戏的身段和唱腔。对杨翠喜而言,李亦师亦友。但因为李母和二哥的强烈反对,两个人的爱情最后夭折。李叔同到上海后,给杨翠喜寄来两首《菩萨蛮》,其一为:“燕支山上花如雪,燕支山下人如月;额发翠云铺,眉弯淡欲无。夕阳微雨后,叶底秋痕瘦;生怕小言愁,言愁不耐羞。”
杨翠喜的命运让人唏嘘。光绪末年,段芝贵为了巴结权贵,将杨翠喜买下献给有名的花花公子——庆亲王之子贝子载振。御史赵启霖联合岑春煊上奏朝廷,弹劾载振,由此引出令朝野哗然的官场花案。
此案发生后,杨翠喜被偷偷送回天津,成为盐商王益孙的小妾。王益孙在其宅前院为杨翠喜另建房三间,并带私家戏楼,让其在戏楼里唱戏过瘾。但为防止世人口舌,他不准杨出屋一步。杨每日如同坐监,由于心情郁闷,一代名伶不足30岁即早早地离开了人间。所遗二子,下落不明。
十八岁时,李叔同由母亲做主与俞氏结婚。在关于李叔同的资料中,并无俞氏真实姓名的记载,只知小名蓉儿,是天津一位茶商的女儿。她是一位旧式女子,相夫教子,克己持家,但却始终未能获得丈夫的爱。
李叔同肖龙,俞氏比他大两岁,肖虎,李的保姆王妈妈说二人为“龙虎斗”,一辈子不合。而不幸为王妈妈所言中,婚后,李俞相敬如宾,但却不算琴瑟相和,日后更是聚少离多,有名无实。婚后不久,俞氏产下一子,乳名葫芦,但不幸天折。
俞氏与李叔同共度的时光,是在二人婚后迁居上海,到李留学日本之前的几年间。母亲去世后,李叔同扶灵北上,办完母亲的丧仪后,他将妻儿安顿在天津老家,只身赴日本留学。
从日本回国后,李叔同在天津住了一年多。据其子李端回忆,在他的印象中,父亲没有在家度过春节。当时李叔同将日本妻子安顿在上海,春节期间,他可能在上海度过了。
1912年,李叔同离开天津后,就再也没有回过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