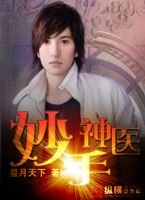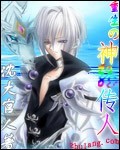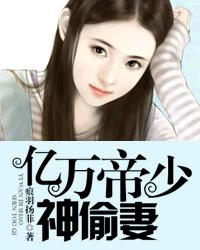藏獒的精神-第3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咳恕蔽蘼墼谛睦砩匣故窃诳谕飞希几兄赜诟叽舐降娜僖⒌谌姆绻猓兄赜诟咴松目嗄鸦砗蜕苎У钠毡槿现灰皇敲娑浴癎DP”、“年收入”、“私家车”、“高尔夫球场”、“花园别墅”、“出国旅游”等这样一些“迷茫的小路”一样会令人悲壮起来的问题,他们就没有理由一味地把谦虚发展成自卑。可以说他们在形而下的氛围里谦虚,在形而上的氛围里骄傲。由于他们从骨子里就喜欢较为抽象地思考,较为超拔地活着,所以他们的自豪和骄傲比起他们的自卑和谦虚来要多得多。甘肃有拉卜楞寺,青海有塔尔寺,它们地位相当,都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六大丛林之一,但是你在普通的甘肃“西部人”那里很少能听到关于拉卜楞寺的情况介绍,而在最普通的青海“西部人”嘴上却往往会有关于塔尔寺的详细说明,尽管他们未必是香情佛缘的信徒,未必有阅读经堂经卷的爱好。有一个特点非常鲜明:青海的“西部人”自觉不自觉地都以藏族人为友、为师、为骄人的社会关系,以藏传佛教为自己存在的金铜的衬景;最优秀的音乐家、画家、作家、诗人,都把最纯粹、最高昂的激情献给了反映藏族生活和藏族心灵的艺术创作;有的干脆娶了藏女为妻,把文成公主和藏王松赞干布的皇室婚配民族联姻发展成了现代版的自由恋爱平民好合,尽管这样的婚姻和所有的婚姻一样也有幸与不幸之分,但内心的倚重、情感的附着却因此而班班可见。
不仅如此,作为金铜般辉煌的存在而让青海的“西部人”仰首伸眉的,还有全国最大的咸水湖青海湖,还有野生动物的家园可可西里无人区,还有横空出世的昆仑山,还有伸手把天抓的唐古拉山,还有和甘肃一家一半的祁连山,还有世界最大的盐泽柴达木,还有长江的源头、黄河的源头、澜沧江的源头。没有哪个地方能像青海这样把不朽的自然直接转换成人的精神、人的眉眼、人的资本;也没有哪个地方的人能像青海的“西部人”这样,把自己的喜怒哀乐直接和胖山肥水、旷原大漠联系起来,从而在和外界的对话中获得话语权的优势。是的,我真的看到过这样的情形,1996年在北京的一次人文精神讨论会上,当一个青海人突然从沉默中爆发大讲特讲起自然和人的关系时,所有那些目中无人自以为真理在握准备反驳一切的人都收敛起倨傲的态度开始洗耳恭听了。他们还能反驳什么呢?这个青海人讲的完全是他们闻所未闻、读所未读的事情。他们没有准备好批判的武器自然就不能进行武器的批判,只好沉默着,突然有人说:“高人原来在这里。”那个青海高人突然就红了脸,一句不吭了,半晌才说:“是啊,我就是高人,是高海拔的人,我也只能说说高海拔的事情,说别的,不会。”这是诚实的表白。曾几何时,离开了替山川宣言、替江河布道,青海的“西部人”就不知道说什么才能在话语的汪洋里找到自己的立锥之地。我说了,他们是谦虚的。
谦虚的副产品是内向和保守。保守的原因是他们过于频繁地审视着自己,过于自律地看到了自己的不足,就只好诚实地以为自己是不行的。其实不是这样,放大自己的不足而缩小自己的实力,这是青海“西部人”的一个特点,自然也是一个缺点,至少在过去是这样。有一些不甘寂寞的佼佼者曾经把它颠倒了过来:放大自己的实力而缩小自己的不足。于是马上就有了峰回路转的效果:想有的有了,该成的成了。青海的“西部人”普遍地老实忠厚,且常有一些胆小怕事者不知疲倦地教人如何安守本分。但也不是绝对如此,一俟风云际会,凤凰来仪,平静之中也能猛不扎扎地诞生几个掀天揭地之人、震电惊雷之才,在省内省外干成一番大事业,令世人半张了嘴刮目相看。这样的人,学界里有,艺道中有,文坛内有,仕途经济上也有;这样的人,近年来增加了不少,好像猛然开窍了似的东一头西一头地冒了出来。在青海的“西部人”中,过去是搞文化的人多,搞经济的人少,想搞经济的都到省外的广阔天地历练折腾去了;现在有了变化,在经济的深海里踏波走浪的渐渐多起来,而且是卓有成效的——眼见着洽谈会开得如火如荼,贸易风吹得漫天彻地,高层建筑比肩接踵,形象工程闪亮登场,旅游探险渐趋火爆,酒楼饭店吃客盈门。相对而言,潜心搞文化的人似乎变得稀稀拉拉了。这大概也是发展变革的一个标志,只有在那些没有机会也没有条件搞活搞火经济的地方,识字的人才会成群结队钻到文化里去寻找出路,殊不知文化要是没有经济做支撑,就是一只没有翅膀的鸟,飞都飞不起来,哪里还有什么出路?
现在该说说陕西人了。因为陕西以汉民族为主,所以我就没有必要使用“陕西的‘西部人’”这样一种表述,又因为西部的文化含义应该是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兼有、少数民族文化和汉民族文化的杂交,而陕西只有单纯的以农耕文化为主要凭借的汉文化格局,所以我考虑更多的是陕西人是不是离“西部人”太远了些,而离中原人更近了些?离中原人近了又怎么样?难道他们就不是西部人或者不是正宗的西部人了(确曾有人在讨论西部文学时认为,陕西自古就是中原的核心,和文化层面上的“西部”根本就没什么关系)?还是让我们丢开迷彩似的抑或是阴霾似的文化,面对平平常常、朗朗净净的现实吧。现实的陈列是:陕西在经济和行政上是大西北的龙头大省,过去的西北局就设在西安小寨,加上陕北老区的存在和关中丰富的干部资源,1949年以后西北各省的领导干部大都要从陕西派去,所以陕西人的身影在大西北的官场上是来去最多的,各省区厅级以上的干部中撇着关中腔说着陕北话的人没有一大半也有一小半,厅级以下的干部就更多了,多得就像拉网一样。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老百姓只要听到谁在滔滔不绝地说陕西话,那一定是在下指示或者作报告。用官员们的语风便是:陕西人对大西北的建设是作出了贡献的,老百姓是不会忘记他们的。不会忘记的标志之一是大西北的老百姓都听得懂甚至都会说陕西话尤其是关中话,标志之二是如果没有别的诸如热歌劲舞、美国大片的消遣而只有戏,老百姓一般都还是喜欢那种“唱戏和吵架分不开”的秦腔的。各省区过去也都有秦腔剧团,这固然与历史上的“秦陇一家”、“文化西向”分不开,但更有赖于各地陕籍干部的倡导和垂范,所谓上行下效、家至户到而已。既然陕西以及陕西人对大西北有着如此深广的影响,陕西人是不是正宗西部人的问题就显得有点多余了。况且这不是一个你认为怎样就怎样的问题,正如一个陕西人对我说的:早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七个五年计划草案中,就明确将全国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地带,包括在西部地带中的省区有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四川、云南、贵州、西藏九个省区。国家早已决定了的事情,你们怎么还能煞有介事地讨论呢?一想也对,这么大的问题,国家能让咱文化人说了算?说了不算的事情就不要说了吧。
陕西有着西部各省区无法比拟的地理优势,所以它迄今仍然是大西北经济最繁荣、文化最发达的一个省。但是西部人对陕西尤其是西安的标准向来都是苛求而超高的:按照你的基础、你的优势、你在西部人心目中的地位,你是不是应该更好一点呢?过去西部腹地的人到了西安就觉得到了最了不起的地方,现在他们还希望这样,还希望到了西安就不想到别的地方去了。西安是个大都市,是个雄霸霸的古地方,有十二个王朝在这里建都,在这里发布政令统治着全中国。这样一个在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升起着太阳的中心都市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它装载着陕西人的全部骄傲,装载着这些骄傲能够经久不衰、能够流布四方的全部光耀:有巍峨的城墙,有辉煌的陵墓,有奇伟的兵马俑,有华丽的宫殿,有先民的村址,有数不清的遗迹遗物。但是再辉煌的陵墓也是活人不羡慕的,再奇伟的兵马俑也是真人不愿意为伍的,再华丽的宫殿也是今人所无法亲合的。对真实、自我、创造、现代、心灵、自由这些更为贴近时代的词汇来说,历史的骄傲似乎可以减免成无,因为它作为远去的刚健只能衬托出今天的软弱,作为陈年的辉煌只能衬托出今天的平淡,作为旧有的经典只能衬托出今天的遗憾。在我们必须热情而敏感、智慧而理性地把握住迅变的今天而不是盲目地享受以往、陶醉古老的时候,一种时尚的装束、一个现代的眼神、一副自信的做派比巍峨的城墙、先民的残址、价值连城的遗迹遗物更能体现一个城市的品貌和一个人群的格调。所以包括陕西人在内的西部人都知道,城墙、陵墓等等都不应该是今天人们的骄傲,要骄傲也是替古人骄傲,骄傲完了你还得面对你自己,面对你那忧伤的怀想——怀想荡荡乎八水绕长安的秀丽,怀想皎洁灵潭、参差画舫、八街九陌、丽城荷香的都市人文。他们怀想的是他们的祖先和他们自己曾经的居住环境,是一个才丢失不久的梦,是深深憾恨中的浓浓迷茫,那意思便是:留下来的可以骄傲,破坏了的怎么办呢?如今的陕西人,最深最长的叹息便是河流的干涸、水资源的流失,以及由于河道年久失修而突然泛滥起来的洪水。为此他们本能地想抓住梦的手,抓住了也没用,既然是梦,丢失了就再也不能原模原样地回来了。陕西人都特别地明白这一点,所以也就变得十分谦虚:我们不行,我们比不上东部省份,更比不上沿海,尤其是在发展循环经济方面落后于人,人与环境的关系总是剑拔弩张的。
有个陕西朋友对我说:“我觉得我们陕西人有点尴尬,现代里靠不上,落后里又没有,说东不东,说西不西,说是在西部的前沿,可真正需要你风风火火面对世界的时候却又显得过于腼腆。”
如前所说,陕西人在西部官场中行走的比较多,这似乎已经成了一种传统、一种习惯,大家都觉得自己应该有个一官半职,应该在时来运到的时候跳到风云里头叱咤一番。这当然是大好的事情,谁不想云起龙骧,化为侯王,博得个封妻荫子乃至青史留名呢?再说了,领导大家搞工作毕竟要比听从别人搞工作爽得多,气派得多,就像俗话说的,是虎就想吃兔,是猫就想吃肉,是猴就想上树,是人就想进步。但是,如果太多的人热衷于官场大事业而不屑于经济小文章,那事业真正的发展、生活真正的兴旺恐怕就要大打折扣了。再加上文化,文化这东西,太古老,太厚重,太值得骄傲——骄傲得舍不得放下了,反而会变成累赘。人家是光着膀子、光着腿,就穿个裤衩往前跑,你是穿了西周的裤子,还要套上秦时的布衫,还要裹上汉朝的青衣,还要罩上隋代的锦袍,最后还要缠上一圈杨贵妃不小心丢掉的腰带,你说你累不累?你还能跑到前头去?对仕途的迷醉和对古董的流连拖累了他们,使他们显得不那么新锐,不那么前卫,不那么鲜活,不那么异类,不那么潇洒,不那么灵动,不那么“冷娃”,不是蹦蹦跳跳自由尖叫,而是背着两手迈着方步一副老成持重循规蹈矩的样子。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陕西人都这样,陕西人中的陕北人就显得不那么为厚重的历史和同样厚重的文化所累,也不那么认可唐城的布局一样齐整、兵马俑的排列一样有序的规矩方圆。他们从黄土地的沟沟壑壑里拼命往外爬,左冲右突,始终保持着一股令人感动也令人恻隐的倔强之气,那便是即使吃糠咽菜,也是贫而牛,贫而骄的。其中的优秀分子有着强烈的出人头地的欲望和一颗不就义不罢休的匪石之心,且能在欲望的实践中充分表现自己过人的聪明才智。但是浑厚的黄土地对他们毕竟有着无法抗拒的引坠之力,金属般光亮的故乡的桎梏以及秉性、语言、人际关系的限制毕竟太牢太重,他们往往走不了多远便要停下来。东山的狮子东山跳,就在陕北当地或者陕西境内寻找擂台,施展武艺,不像新疆、青海、宁夏的西部人,为了找到一个适合自己发展的位置,一腿就能从天山、从昆仑山、从贺兰山迈到广州、深圳、海口,普通话一说,别人就不知道他是哪座山里来的神仙了。
然而,如果有人把“伟大”这个词汇交给我同时又限定我在此文中只能使用一次的话,我仍然要把它献给陕西人。陕西人的肩膀是绝对担得起这个词汇的,无论是秦人的后代,还是匈奴的子孙,都在这块黄土的大地上把中国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