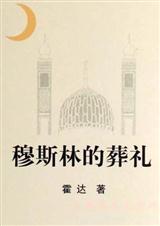卢布林的魔术师-第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如果世界上的人知道他,雅夏,心里在想什么,他早就被送进疯人院了。
4
暮色苍茫。城外还有一些亮光,但是在狭窄的街道和高耸的建筑物中间天已经暗下来了。店铺里点起油灯和蜡烛。留着胡于的犹太人穿着长外套和阔皮靴,在街上走着,赶去参加黄昏的祈祷。一个月牙儿升起,西凡月的新月。尽管太阳整天烤着这个小城,街上仍然有一个个水坑,春雨的遗迹。处处下水道里漫出脏水。空气里混着牛马粪的臭味和刚从乳房里挤出来的牛奶味。一缕缕烟队烟囱里冒出来;主妇们在忙着做晚饭:麦片汤啦、麦片炖菜啦、麦片蘑菇啦。雅夏向舒默尔告别,动身回家。卢布林以外的世界闹得沸沸扬扬。波兰的报纸上天天叫嚷战争、革命、危机。各地的犹太人都在被人从村子里撵出去。许多人正在移居美洲。但是在这里,卢布林,人们只感到一个长期建立的犹太人区的稳定性。城里有几所会堂还是好久以前克迈尔尼斯基时代造的。拉比、经书注释者、法律学家和圣徒们,他们一起埋葬在墓地里,每一个都在他自己的墓碑或者坟堂底下。这里流行着古老的风俗:女人经营买卖,男人钻研《摩西五书》。
五旬节还差几天,但是小学生们已经用许多图案和剪纸装饰窗子;还有用生面团和蛋壳做的鸟;树枝和树叶从郊区运进城来,纪念这个节日,那一天摩西在西奈山上被授予律法。
雅夏在一所会堂前站住脚,向里面望去。他听到一片众口一辞的、平静的声音。信徒们在吟诵《十八祝福词》。终年为造物主服务的、虔诚的犹太人捶着他们的胸脯,嚷叫:“我有罪”,“我们犯了罪。”有些人举起双手,另一些人抬起眼睛——向着天。
一个穿着斜纹布上衣的老人,戴着两顶便帽,再加上一顶高帽顶的礼帽,一顶叠着另一顶,扯着他的白胡子,低声呻吟。七枝烛台上点着一支纪念蜡烛,随着烛光的闪烁,人影在墙上跳动。雅夏在开着的大门前逗留了一会儿,闻着蜡、牛油和发霉的东西的混合气味——他从童年起就记得发霉的东西。犹太人——他们是一个完整的集体——在向一个没有人看到过的上帝说话。尽管他把瘟疫、饥荒、贫穷和屠杀当作礼物赐给他们,他们还是认为他仁慈和怜悯,并且自称是他的选民。雅夏经常羡慕他们的毫不动摇的信仰。
他在那里站了一会儿,才继续前进。街灯亮着,但是没有什么用。那些街灯只能使人看到在黑暗中有一些星星点点的亮光罢了。店铺里一个顾客也没有,为什么还开着门呢,真叫人想不通。那些掌柜的女人,剃过头发的脑袋上裹着围巾,坐在铺子里给她们的男人织补袜子或者给她们的孙子孙女缝小围裙和内衣。雅夏全认识她们。十四五岁上结婚,一过三十,她们都做祖母了。过早来到的老年使她们脸上长出皱纹,牙齿一个个脱落,人变得慈祥温和。
虽然雅夏同他的父亲和祖父一样出生在这里,他始终是一个陌生人——这不只是因为他抛弃了犹太人的生活习惯,而是因为不管在这里还是在华沙,不管在犹太人还是在异教徒中间,他一直是一个陌生人。他们都安定地居住着,有固定的家庭——他呢,一直东飘西荡。他们有儿女子孙;他呢,什么也没有。他们有他们的上帝、他们的圣徒、他们的领袖——他只有怀疑。对他们来说,死亡是天堂,但是对他来说,只是一片恐惧。去世以后是怎么一回事呢?灵魂那玩意儿到底有没有?灵魂离开了肉体怎么办呢?早在童年的时候,他就听到过恶魔、鬼魂、人狼和妖精的故事。他,他自己,也经历过没法用自然规律解释的事情,但是那到底有什么意思呢?他变得越来越糊涂和孤独。在他的心里,各种力量在激荡;激情折磨得他陷入恐怖。
他在黑暗中走着,埃米莉亚的脸在他眼睛前面浮现出来:瓜子脸、茶褐色皮肤、犹太人那样的黑眼睛、斯拉夫型的翘鼻子,脸颊上有两个酒窝,高额头,头发直向后梳,上嘴唇上微微有一抹黑接接的汗毛。她微笑着,既腼腆又风骚;她带着追根究底的神情打量着他,既显得老于世故,又像是姐妹似的。他想要伸出手去碰碰她。到底是他的想象力这么生动呢,还是这真的是一个幻象?她的形象好像是宗教游行队伍中的一面圣像牌向后移动着。他看到她的头发式样、脖子周围的花边、耳朵上的耳环。他多么想叫她的名字啊。他过去的那些私情都不能同这一次相比。不管是在睡梦中还是醒着,他都渴望见到她。他已经不再感到疲劳,简直等不及过了五旬节才到华沙去同她会面。他没法通过埃丝特来缓和激情,尽管他尝试过。
有人撞了他一下。那是担水人哈斯基尔,扁担上挑着两桶水。他看上去好像是从地底下冒出来似的。红胡子上闪烁着不知从哪里照过来的微弱的亮光。
“哈斯基尔,是你吗?”
“不是我,是谁呢?”
“这么晚还担水?”
“我得挣几个钱过节。”
雅夏在口袋里摸来摸去,摸到一个值二十个子儿的硬币。“拿去吧,哈斯基尔。”
哈斯基尔恼火了:“这算什么?我不接受施舍。”
“这不是施舍,这是给你的孩子买个奶油甜饼吃的。”
“那好吧,我收下——一谢谢。”
哈斯基尔的肮脏的手指头同雅夏的握了一下。
雅夏走到自己的房子跟前,从窗口望进去。两个女裁缝在做新娘的嫁妆。戴着顶针的手指头麻利地缝着。灯光下,一个女裁缝的头发看上去红得像火焰。埃丝特在炉灶前忙得团团转,把松枝加进三脚炉,炉上正在烧晚饭。屋中央摆着一个揉好的面团,面团上盖着旧布和垫子。埃丝特要用这些面粉烤一炉五旬节吃的奶油甜饼。我能离开她吗?雅夏想。这些年来,她一直是我唯一的支持。要不是她对我忠诚,我早就像风暴中的一片树叶那样飘零了……
他没有马上走进屋子,而是穿过走廊到院子里去看望那两匹马。院子好比城市中心的一小片乡村。绿油油的草上沾着露珠,苹果又绿又生,不过已经芳香扑鼻。这里的天空看上去好像比较低,星星更密。雅夏走进院子的时候,一颗星不知在太空中什么地方离开了轨道,陨落下来,发出一道火焰似的电光。空气里既有香喷喷又有冲鼻子的气味,充满着沙沙声、蠢动声和蟋蟀的叫声——一每隔一会儿就会变成一阵响亮的齐鸣。田鼠到处乱窜。老鼠在地上挖出一个个小上堆。鸟窝筑在树枝上、谷仓里和屋檐下。小鸡在草料棚里打盹儿。天天夜晚,那些鸡为了草料棚里那一片有争议的地方悄悄地吵架。雅夏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真奇怪,每一颗星都比地球大,都离开地球几百万英里。如果谁在地球上挖一条几千英里深的沟,他就会在美国的地底下钻出来。……他打开马厩门;隐藏在黑暗中的两匹马神秘地呈现出来。眼珠子很大的眼睛里闪烁着星星点点的金光或者火光。雅夏回想起他的父亲——愿他早升天国——曾经告诉他:牲口能够看见邪魔恶鬼。卡拉摇摇尾巴,用蹄子创刨地面。那匹马对主人显出一种扣人心弦的动物的忠诚。
5
所有的圣殿、会堂和哈西德派的集会场所都被过五旬节的人挤得密不通风。连埃丝特也戴上她结婚时候做的那顶帽子,带上烫金的祈祷书,向妇女的会堂走去。但是雅夏仍然留在家里。既然上帝从不回答,我干吗要去跟他说话呢?他开始看一本他在华沙买的、关于自然规律的、厚厚的波兰语书。书里对什么都有说明:引力规律啦,每一块磁铁怎么都有南北极啦,同性相斥、异性相吸是怎么一回事啦。书里还有:为什么船浮在水面上,水压机是怎么运转的,避雷针是怎么避免雷击的,蒸汽又是怎么开动火车的等等。这些知识不但使雅夏感到兴趣,而且对他干的那一行有重大的关系。多少年来,他一直在绳索上走,却不知道他所以能够待在绳索上,无非是因为他设法使重心始终保持平衡。但是他看完这部阐明事物真相的著作以后,许多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土地为什么吸住岩石?引力到底是什么?磁铁为什么只吸铁,不吸铜?什么是电?天空、地球、太阳、月亮、星星,这一切都是从哪里来的?书上提到康德和拉普拉斯的太阳系理论,但是不知怎么的,看上去缺乏说服力。埃米莉亚给雅夏一部论述基督教的著作,那是一位神学教授写的,但是照雅夏看来,圣灵怀胎的故事和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和圣灵——的解释,比哈西德教派赋予它的那些拉比的奇迹更不可信。她怎么能相信这种玩意儿呢?他问他自己。不会的,她只是装装样子罢了。他们全是装装样子的。整个世界演的是一场闹剧,因为人人都不好意思说:我不知道。
他踱来踱去。当别人都去会堂,他独自个儿待在家里的时候,他总是思想激动。怎么会造成这种情况的呢?他的父亲是一个虔诚的犹太人,一个经营五金用品的穷商人。雅夏七岁的时候,他母亲死了;他父亲没有再结婚;这孩子不得不自己照料生活。他往往到犹太小学里去上一天课以后倒要停三天。他父亲的铺子里,不用说,有许多锁和钥匙。雅夏对那些玩意儿感到好奇。他会反复摆弄一把锁,一个劲地钻研,直到不用钥匙也能把它打开。有时候,魔术师们从华沙和别的大城市来到卢布林,雅夏会跟着他们从一条街走到另一条街,仔细地看着他们耍的把戏;以后他会想方设法地模仿他们,表演得同他们一模一样。如果他看到有人用纸牌在变戏法,他会拿着一副纸牌玩个不停,直到他玩得得心应手。他看到一个演杂耍的在走绳索,马上赶回家去尝试。他从绳索上摔下来以后,会再跳上去。他在屋顶上奔跑,在深水里游泳,从阳台上跳下来,跳进逾越节前从床垫中换出来的干草中去,但是不知什么缘故,他从来没有受过伤。他在祈祷的时候说谎,亵读安息日,但是始终相信一位守卫和保护他免受危险的守护神。尽管他有不信教的人、无赖、野蛮人等坏名声,一位可尊敬的姑娘埃丝特爱上了他。他到处流浪,有时候在一个马戏团里搭班,有时候同一个要狗熊的搭档,有时候甚至跟着一个波兰杂耍班子到各地的消防站去巡回演出,但是埃丝特耐心地等着他,原谅他的一切不检点的小节。多亏了她,他才成了家,有一份产业。他知道埃丝特在等他,这才使他树起了提高自己的地位的雄心壮志,急切地想到华沙的杂耍场和夏季剧场去演出,终于使声誉传遍波兰。他现在不再是那种带着一个手风琴、牵着一只猴子的街头艺人——而是一位表演艺术家。报纸上向他喝彩,称他为大师、了不起的天才;老爷夫人们到后台去祝贺他。人人都在说,如果他到西欧去,他如今早已世界闻名了。
光阴一年年过去,但是他说不上一年年是怎么过的。有时候,他感到他好像仍然是个孩子;有时候,他看上去好像已经一百岁。他自学波兰语、俄语、语法和算术;他念代数、物理、地理、化学和历史的课本。他脑子里塞满了事实、日期和新闻。他样样都记得,什么也忘不了。他只要看一眼,就能肯定一个人的性格。人只要一开口,雅夏就知道他要说什么。他蒙住眼睛也能念书,精通催眠术、心灵感应术和传心术。但是埃米莉亚——一位教授的出身高贵的未亡人——同他两个人发生的事却完全不一样。不是他在用心灵感应术去吸引她,而是恰恰相反。不管他们相隔多少英里,她从来没有离开他的身边。他感到她的凝视,听到她的声音,闻到她的芳香。他像在绳索上走那样心情紧张。他一睡着,她就来到他的面前——是灵魂出窍吧,但是活灵活现,轻轻地说着情话,拥抱,接吻,向他流露出柔情蜜意;说也奇怪,她的女儿海莉娜也在场。
门推开了,埃丝特走进来,一只手拿着祈祷书,另一只手提着她那条绸连衫长裙的有褶的裙锯。她头上那顶有羽毛的帽子使雅夏想起结婚以后的第一个礼拜六,那一天新娘埃丝特被引进圣殿。眼下她眼睛里闪烁着欢乐的光芒——同别人一起过节的人才会有这样兴高采烈的心情。
“节日好!”
“祝你节日好,埃丝特!”
他拥抱她;她的脸像新娘似的羞得通红。长期的分离使他们保持着新婚夫妇的热情。
“圣殿里有什么新鲜事?”
“男人的呢,还是女人的?”
“女人的。”
埃丝特笑起来。
“女人总是女人。祈祷一阵,闲聊一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