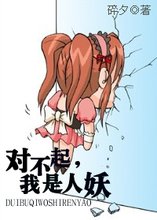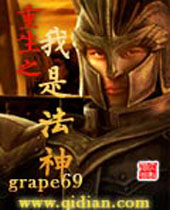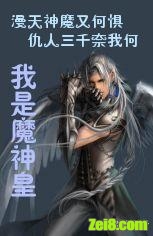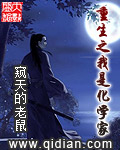我是北大留级生-自学成才之路-第3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喜欢18、 19世纪的欧洲学者,他们偏爱把自己的学问同哲学挂钩,这样整个认识层次便上了一个台阶。(大学三年级下学期我开始注意到了这种现象)
估计这是牛顿深远影响的缘故。牛顿把自己的代表作称之为《自然哲学数学原理和他的世界体系》。我对这个书名有种敬畏和肃然起敬感。尤其是站在该书的英文名字面前(每个开头字母大写),我的敬畏心情便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境界:The Mathematical Principles of Natural Philosophy and His System of the World.
“坚硬的岩石是时间的女儿”(2)
我这种大脑有关神经系统的反应既来自我的天性,也来自我在北大接受到的教育。这种反应和我对莫扎特钢琴协奏曲中“钢琴同整个乐队对话”的反应是属于一个性质。没有这种反应,我便不可能走向觉醒。没有这种反应,我的脑壳便不开壳。
牛顿还有一个习惯:他把物理实验称之为“实验哲学”,也给了我美好的、崇高印象。不要小看了这一个术语,它在当年对我洗礼、启蒙和正面的冲击足抵得上北大任何一位名教
授。
《动物学哲学》据我所知,这部经典我国至今没有中译本,而日本早在20世纪初便有了日文译本。一百多年来,日本这个国家和民族主要是靠翻译起家的。这样说,一点也不过分。
日本是西方文明最好的学生,是高材生。明治维新以前日本是中国文明的学生,后来是西方的学生。光这个书名给予我的就是一种神圣、高贵的冲击。
我不懂法文。当时我读的是英译本:《Zoological Philosophy》。北大图书馆又有收藏!记得盖了“燕京大学图书馆藏书”的印章。在书中,拉马克在扉页中谈起他的研究动机,引起了我的共鸣(同书中伟人产生共鸣是我6年求学时期最主要的经历):
“观察自然,研究她所生的万物;追求万物,探究其普遍的或特殊的关系;再去捕捉自然界中的秩序,把握她进行的方向,握住她运作的法则……这等工作……还能给我们找到许多最温暖、最纯洁的快乐,以补偿生命场中种种不能避免的苦恼。”
这后一句,尤其给了我安慰。逃向大自然是我当年倔傲抗世的方式。我只能走这条路。历代中国知识分子有这个传统:“天下有道则仕,无道则隐。”我也不例外。
拉马克(1744—1829)是法国人,进化论先驱。他有句格言给了我深刻印象:“大自然就是时间。”
意思是:大自然创造万事万物都需要漫长的时间。
他说,大自然的动作很慢,她非得用悠缓的时间去完成她的大业不可。生物进化便经历了漫长时间。
毕业前夕,我还给上帝下了一个定义:
上帝—大自然=时间+空间
“上帝—大自然”是个德文术语:GottNatur。拿掉时间和空间,上帝便消失了。上帝用时空搭建大舞台。在台上,他一边创造一边毁灭。
圣希兰(E.G.SaintHilaire,1772—1844)的《解剖学哲学》同样给了我智慧。他的专业是脊椎动物学。他和拉马克都是这类思想家:一方面注意观察,看重事实;另一方面又善于从大量事实中抽出普遍法则,追求哲理。从我的学生时代,直到40多年后的今天,我偏爱17、 18和19世纪的自然科学家追求自然界的普遍法则。记得1806年有位法国生物学家说过:真正的植物学家理应去追求普遍存在于自然界的永恒真理。
今天自然科学家的哲学倾向、气质和色彩比以前少了,淡了,我认为是退步。我建议把古生物学叫“古生物哲学”;把实验物理叫做“实验物理哲学”;把解剖学恢复到“解剖学哲学”,为的是在人心中激起一种神圣、崇高和庄严的感情。
圣希兰仔细解剖了各种脊椎动物,并作了比较。他发觉大自然是根据同一法则去创造一切生物的。主要、基本原理不变,只是在一些次要地方作了些改变。若是圣希兰活到今天,知道了DNA结构,他会更加为自己的这一自然哲学信念而兴奋不已,并喊出:
“壮哉,造物主!伟哉,大自然!”
三、 为“进化论”卖掉裤子
“典衣买书”在我的6年北大时期是生活中一件不算小的事。开始萌念买批书是在1958年秋。我渴望自己能拥有一批心爱的名著经典。有下面几件事对我是个触动:
1. 温德先生的小书房很温馨,古色古香,书桌很大,是明式家具风格,拥有大约四书架的书,约一千本。我也想将来有朝一日有这么一个做学问的环境。当年我没有想到,这要等到42年后(即2000年)才得以实现,地点在上海浦东, 三室一厅,带一个阁楼,斜屋顶,共130平米——这是我的终老之地了。
2. 有一回我在温德先生家翻到一本1948年的英国杂志,里面有张照片深深触动了我:1940年纳粹飞机轰炸伦敦,有的书店和图书馆被毁。可是爱书的英国人照样从容地在废墟中淘书看,暂时忘却了现实的苦难。
一个热爱阅读的民族是不会被征服的!
3. 想买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达尔文日记》。我特别羡慕他搭乘军舰“贝格尔”号在世界各地(主要是南美)进行古生物学和地质学方面的探险和考察。1831年12月17日,22岁的达尔文在《日记》中写道:“如果能够实现考察世界的愿望,那是一个多么稀有和了不起的机会呀!要作好到海洋去的思想准备……”
我自己不能去考察,从书本上同达尔文一块去游历、开眼界,也是一件好事。这叫“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胸中之块垒”。靠助学金是没有指望的。我拿的已经是最高一级了。对此,我要终生心怀感激之情。14元5角虽不多,却使我有了基本的温饱。若是像今天去打工,消耗掉我的相当多的精力,我还有时间去“俯而读,仰而思”吗?
“坚硬的岩石是时间的女儿”(3)
温饱之后还想买些书,这对我毕竟是个奢望。为了满足这个正当的奢望,我只有一个办法:卖掉母亲给我的衣服。
一共卖过5回,共计一只表、1个金戒指、3条毛料裤,一条羊毛毯。裤子是父亲的,有八九成新。
第一次采取行动便是为了买回进化论和达尔文的书,还有几本是古生物学教程和地质学。它激起了我的有关太古时期的梦。
典衣物的地点在前门大栅栏,要带学生证。价钱压得很低。
第二次是为了买回普朗克论文和讲演集,是为理论物理学及其哲学基础而狂热。归根到底是一次“朝圣”,向我心目中的“上帝”走去。
第三次是为了买英、德文原版的莎士比亚和海涅的全集。
第四、五次是为了买火车票回家探亲。6年,共回过3次家。北京—南昌路远,车票自然是个不小的负担。
昨天(2003年11月17日),我和南昌的大妹通了电话,共同回忆起往事和母亲在世的情景,为的是填补我在北大读书期间有关母亲的一些记忆空白。在电话里,妹妹告诉我,有一次母亲对邻居说:“我的儿子在北京读书怎么不花钱?不交学费吗?买书、买练习薄,不要钱吗?”
后来她才知道我每月领取助学金。但详细情况,她始终不清楚。我对母亲永远是“报喜不报忧”,免得她再为我牵肠挂肚。人的一生就是身处烦恼之海。我母亲摆脱不了生存的“烦”。
我父亲则很达观。所以在我的基因里既有忧虑又有达观。后来,我都把它们提升到了世界哲学的层面,成了“世界痛苦”和“世界解脱”。(提升要受教育)
所以我这个人有两个灵魂。或者说,我是两个灵魂的交织物或混血儿:“世界痛苦”和“世界解脱”。前者是母亲,后者是父亲。两个灵魂的起步和开始形成,都在北大。对时间、空间的感受和体认便涉及到“世界痛苦”和“世界解脱”。
许多年(从大学时代开始),我一直处在“对生的沉思和对死的默念”状态,包括追问时空的本质。
有位法国文豪说:“时间盲目,人类愚蠢。”
前半部他说错了。时间缓缓悠悠,不慌不忙,总是朝一个方向流驶,给人柔弱、无所作为的印象或错觉。
其实时间是最有作为的。它的目的性和方向性特别清楚,特别明确,而且是永不回头,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时间创造一切,也毁灭一切。它知道创造什么、毁灭什么。它有自己的选择和最高法则。它是法治。
在第一回“典衣买书”的壮举中,我买到一本《进化思想史》(英文)。其中提到两位19世纪的法国人:
奇内(E.Quinet),是位诗人哲学家,在1870年出版的《创造》一书中,他写下了一句箴言:“大自然是不回头的;她绝不去重新创造她所破坏的东西。”
比如恐龙就是一个例子。地球上再也不会诞生恐龙了。
古生物学家道罗(L.Dollo)于1893年发扬了奇内的观念,把它提升为“不可逆的进化理论”。
宇宙进化、地球进化、生物进化……统统在时空这个大框架内、大舞台上进行。所有的事件(天上人间发生的一切),都是大大小小的戏。宇宙一舞台,万事万物都是戏。没有空间,哪来时间?没有时间,何来空间?时空是一枚金币的两个面。当然还有物质。
20世纪德国大数学家魏尔(H.Weyl,1885—1955)有本经典就叫《空间·时间·物质:广义相对论讲义》 (1918年),我知道它很艰深。时空结构和本质,说到底是上帝的结构和本质。时间、空间和物质的起源,归根到底是上帝的起源。
生物进化有方向、有目的、有自己的路线和节奏,因为时间是不盲目的。不懂得对时间深表敬畏的人,我劝他不要去研究生物的进化(包括生物的多样性)——这才是我当年卖掉裤子得到的教益。
从今天的眼光去看,当年我涉及古生物学和地质学绝不是不务正业,而是我份内的事。因为它为我的世界观提供、搭建了一个地球和生物进化的大框架。学社会科学的人,从事文学艺术创作的人,也有必要读点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等进化论的书(即使是卖掉裤子)。原因很简单:它能有助于你“善养吾浩然之气”。对各行各业,这气是至关重要的。气,可营造一个人的大将风度。
退一步来看,当年我跑到地质学和古生物学去望野眼,的确有“以山林为小隐”、“以朝市为大隐”的味道。这是时代所迫。今天的大学生也许很难理解五十年代大学生的心态。特别是像我这样一个另类。像我这样的学生估计有一些。但我的生存方式和表现是很独特、很典型的。故意留一级恐怕只有我一人。这是病态环境下的健康反应;是健康的被扭曲或扭曲性质的健康。里面有坚强的主观战斗精神。(当然这是我今天的回顾和判断)
四、 死不瞑目
我是地球人。在我死之前,我怎能不对地球和生物现象谈谈我的看法呢?过几年,我一定写本《生物学的哲学》,为的是总结我多年对生物现象(包括地球的进化、气候变动和生物多样性)的惊叹。
“坚硬的岩石是时间的女儿”(4)
如果不写,就死不瞑目。
各人有各人的“死不瞑目”。
我想起1963年被人暗杀而身亡的美国前总统肯尼迪的遗孀杰奎琳。1964年4月的一天,她去找牧师,问:“如果我自杀,你认为上帝还会将我和丈夫分开吗?”
牧师开导她,说她的两个孩子需要她照顾。这样,她才放弃了自杀的念头。
我也有需要照顾的人和事物。撰写《生物学的哲学》便是其中一件。我忘不了当年我在北大卖裤子和在中国农业科学院17年的经历。每个人都要找到继续活下去的顽强理由。
写完这一章是2003年11月19日夜里11点半。我缓缓放下了笔,看着窗外连夜的风和雨,想起唐朝韩愈的诗:“从今有雨君须记,来听萧萧打叶声。”
多亏当年我的初恋失败,促使爱的目标大位移,居然把地质学和生物学的大门也推开了一条长长的缝!
汉朝焦赣说:“因祸受福,喜盈我室。”
又说:“初虽啼号,后必庆笑。”
此时此刻的我,书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