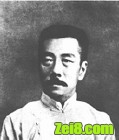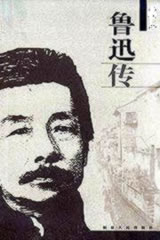鲁迅-第22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不能说他们是“读书人”。倘使《梁父吟》〔4〕说是“二桃杀三勇士”,自然更可
了然,可惜那是五言诗,不能增字,所以不得不作“二桃杀三士”,于是也就害了
章行严先生解作“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
旧文化也实在太难解,古典也诚然太难记,而那两个旧桃子也未免太作怪:不
但那时使三个读书人因此送命,到现在还使一个读书人因此出丑,“是亦不可以已
乎”!
去年,因为“每下愈况”〔5〕问题,我曾经很受了些自以为公平的青年的教训,
说是因为他革去了我的“签事”,我便那么奚落他。现在我在此只得特别声明:这
还是一九二三年九月所作,登在《晨报副刊》上的。那时的《晨报副刊》,编辑尚
不是陪过泰戈尔先生的“诗哲”,也还未负有逼死别人,掐死自己的使命,所以间
或也登一点我似的俗人的文章;〔6〕而我那时和这位后来称为“孤桐先生”的,也
毫无“睚眦之怨”〔7〕。
那“动机”〔8〕,大概不过是想给白话的流行帮点忙。
在这样“祸从口出”之秋,给自己也辩护得周到一点罢。
或者将曰,且夫这次来补遗,却有“打落水狗”之嫌,“动机”就很“不纯洁”
了。然而我以为也并不。自然,和不多时以前,士钊秘长运筹帷幄,假公济私,谋
杀学生,通缉异己之际,“正人君子”时而相帮讥笑着被缉诸人的逃亡,时而“孤
桐先生”“孤桐先生”叫得热剌剌地的时候一比较,目下诚不免有落寞之感。但据
我看来,他其实并未落水,不过“安住”在租界里而已〔9〕:北京依旧是他所豢养
过的东西在张牙舞爪,他所勾结着的报馆在颠倒是非,他所栽培成的女校在兴风作
浪:依然是他的世界。
在“桃子”上给一下小打击,岂遂可与“打落水狗”同日而语哉?!
但不知怎的,这位“孤桐先生”竟在《甲寅》上辩起来了,以为这不过是小事。
这是真的,不过是小事。
〔10〕弄错一点,又何伤乎?即使不知道晏子,不知道齐国,于中国也无损。
农民谁懂得《梁父吟》呢,农业也仍然可以救国的〔11〕。但我以为攻击白话的豪
举,可也大可以不必了;将白话来代文言,即使有点不妥,反正也不过是小事情。
我虽然未曾在“孤桐先生”门下钻,没有看见满桌满床满地的什么德文书的荣
幸,但偶然见到他所发表的“文言”,知道他于法律的不可恃,道德习惯的并非一
成不变,文字语言的必有变迁,其实倒是懂得的。懂得而照直说出来的,便成为改
革者;懂得而不说,反要利用以欺瞒别人的,便成为“孤桐先生”及其“之流”。
他的保护文言,内骨子也不过是这样。
如果我的检验是确的,那么,“孤桐先生”大概也就染了《闲话》所谓“有些
志士”的通病,为“老婆子女”所累了,此后似乎应该另买几本德文书,来讲究
“节育”。
五月二十四日。
※ ※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六月十日《莽原》半月刊第十一期。
〔2〕章士钊(行严)关于“二桃杀三士”的一段话,见他在一九二三年八月发
表于上海《新闻报》的《评新文化运动》一文:“夫语以耳辨。徒资口谈。文以目
辨。更贵成诵。则其取音之繁简连截。有其自然。不可强混。如园有桃。笔之于书。
词义俱完。今曰此于语未合也。必曰园里有桃子树。二桃杀三士。谱之于诗。节奏
甚美。今曰此于白话无当也。必曰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是亦不可以已乎。”
〔3〕《晏子春秋》 撰人不详。内容是记载春秋时齐国大夫晏婴(平仲)的言
行。这里所引的一段,见该书卷二《谏》下。
〔4〕《梁父吟》 亦作《梁甫吟》,乐府楚调曲名。此篇系乐府古辞(旧题诸
葛亮作,不确),鲁迅上文所引“谁能为此谋?相国齐晏子。”为诗中的最末两句。
“相国”一作“国相”。
〔5〕“每下愈况”语见《庄子·知北游》。参看本卷第114页注〔5〕。
〔6〕《“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一文,发表于一九二三年九月十四日的
《晨报副刊》(署名雪之),其时编辑为孙伏园;一九二五年十月一日起才由徐志
摩(即文中说的“诗哲”)编辑。关于“逼死别人,掐死自己”的话,参看本卷第
236页注〔16〕。
〔7〕“睚眦之怨” 意即小小的仇恨。语见《史记·范睢传》:
“一饭之德必偿,睚眦之怨必报。”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七十期
(一九二六年四月十日)发表《杨德群女士事件》一文,以答复女师大学生雷榆等
五人为三一八惨案烈士杨德群辩诬的信,其中暗指鲁迅说:“因为那‘杨女士不大
愿意去’一句话,有些人在许多文章里就说我的罪状比执政府卫队还大!比军阀还
凶!……不错,我曾经有一次在生气的时候揭穿过有些人的真面目,可是,难道四
五十个死者的冤可以不雪,睚眦之仇却不可不报吗?”
〔8〕“动机” 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二卷第四十八期(一九二五年十一月
七日)《闲话》中说:“一件艺术品的产生,除了纯粹的创作冲动,是不是常常还
夹杂着别种动机?是不是应当夹杂着别种不纯洁的动机?……年轻的人,他们观看
文艺美术是用十二分虔敬的眼光的,一定不愿意承认创造者的动机是不纯粹的吧。
可是,看一看古今中外的各种文艺美术品,我们不能不说它们的产生的动机都是混
杂的。”
〔9〕一九二六年春夏之交,冯玉祥国民军在直奉军阀的联合进攻下,准备放弃
北京。段祺瑞趁机阴谋与奉系军阀里应外合,赶走冯军。四月十日凌晨,驻守北京
的国民军包围段宅和执政府,段闻讯后即逃往东交民巷。随着段祺瑞的倒台,章士
钊也逃到天津租界。
〔10〕章士钊在《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九号(一九二五年九月十二日)上重新
刊载他所作的《评新文化运动》一文,前面加了一段按语,其中说:“北京报纸。
屡以文中士与读书人对举。为不合情实。意谓二桃之士。乃言勇士。非读书人。此
等小节。宁关谋篇本旨。且不学曰学。其理彼乃蒙然。又可哂也。”
〔11〕农业也仍然可以救国的 这是针对章士钊所谓农业救国论而说的。章曾
一再鼓吹什么“农村立国”,如在《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二十六号(一九二六年一
月九日)发表的《农国辨》一文中说:“凡所剿袭于工国浮滥不切之诸法。不论有
形无形。姑且放弃。返求诸农。
先安国本。而后于以拙胜巧之中。徐图捍御外侮之道。庶乎其可。”
。。
《阿Q正传》的成因〔1〕
在《文学周报》二五一期里,西谛先生谈起《呐喊》,尤其是《阿Q正传》。
〔2〕这不觉引动我记起了一些小事情,也想借此来说一说,一则也算是做文章,投
了稿;二则还可以给要看的人去看去。
我先要抄一段西谛先生的原文——
“这篇东西值得大家如此的注意,原不是无因的。但也有几点值得商榷的,如
最后‘大团圆’的一幕,我在《晨报》上初读此作之时,即不以为然,至今也还不
以为然,似乎作者对于阿Q之收局太匆促了;他不欲再往下写了,便如此随意的给他
以一个‘大团圆’。像阿Q那样的一个人,终于要做起革命党来,终于受到那样大团
圆的结局,似乎连作者他自己在最初写作时也是料不到的。至少在人格上似乎是两
个。”
阿Q是否真要做革命党,即使真做了革命党,在人格上是否似乎是两个,现在姑
且勿论。单是这篇东西的成因,说起来就要很费功夫了。我常常说,我的文章不是
涌出来的,是挤出来的。听的人往往误解为谦逊,其实是真情。我没有什么话要说,
也没有什么文章要做,但有一种自害的脾气,是有时不免呐喊几声,想给人们去添
点热闹。譬如一匹疲牛罢,明知不堪大用的了,但废物何妨利用呢,所以张家要我
耕一弓地,可以的;李家要我挨一转磨,也可以的;赵家要我在他店前站一刻,在
我背上帖出广告道:敝店备有肥牛,出售上等消毒滋养牛乳。我虽然深知道自己是
怎么瘦,又是公的,并没有乳,然而想到他们为张罗生意起见,情有可原,只要出
售的不是毒药,也就不说什么了。但倘若用得我太苦,是不行的,我还要自己觅草
吃,要喘气的工夫;要专指我为某家的牛,将我关在他的牛牢内,也不行的,我有
时也许还要给别家挨几转磨。如果连肉都要出卖,那自然更不行,理由自明,无须
细说。倘遇到上述的三不行,我就跑,或者索性躺在荒山里。即使因此忽而从深刻
变为浅薄,从战士化为畜生,吓我以康有为,比我以梁启超,〔3〕也都满不在乎,
还是我跑我的,我躺我的,决不出来再上当,因为我于“世故”实在是太深了。
近几年《呐喊》有这许多人看,当初是万料不到的,而且连料也没有料。不过
是依了相识者的希望,要我写一点东西就写一点东西。也不很忙,因为不很有人知
道鲁迅就是我。
我所用的笔名也不只一个:LS,神飞,唐俟,某生者,雪之,风声;更以前还
有:自树,索士,令飞,迅行。鲁迅就是承迅行而来的,因为那时的《新青年》编
辑者不愿意有别号一般的署名。
现在是有人以为我想做什么狗首领了,真可怜,侦察了百来回,竟还不明白。
我就从不曾插了鲁迅的旗去访过一次人;“鲁迅即周树人”,是别人查出来的。
〔4〕这些人有四类:一类是为要研究小说,因而要知道作者的身世;一类单是好奇;
一类是因为我也做短评,所以特地揭出来,想我受点祸;一类是以为于他有用
处,想要钻进来。
那时我住在西城边,知道鲁迅就是我的,大概只有《新青年》,《新潮》社里
的人们罢;孙伏园〔5〕也是一个。他正在晨报馆编副刊。不知是谁的主意,忽然要
添一栏称为“开心话”的了,每周一次。他就来要我写一点东西。
阿Q的影像,在我心目中似乎确已有了好几年,但我一向毫无写他出来的意思。
经这一提,忽然想起来了,晚上便写了一点,就是第一章:序。因为要切“开心话”
这题目,就胡乱加上些不必有的滑稽,其实在全篇里也是不相称的。署名是“巴人”,
取“下里巴人”〔6〕,并不高雅的意思。谁料这署名又闯了祸了,但我却一向不知
道,今年在《现代评论》上看见涵庐(即高一涵〔7〕)的《闲话》才知道的。那大
略是——
“……我记得当《阿Q正传》一段一段陆续发表的时候,有许多人都栗栗危惧,
恐怕以后要骂到他的头上。并且有一位朋友,当我面说,昨日《阿Q正传》上某一段
仿佛就是骂他自己。因此便猜疑《阿Q正传》是某人作的,何以呢?因为只有某人知
道他这一段私事。……从此疑神疑鬼,凡是《阿Q正传》中所骂的,都以为就是他的
阴私;凡是与登载《阿Q正传》的报纸有关系的投稿人,都不免做了他所认为《阿Q
正传》的作者的嫌疑犯了!等到他打听出来《阿Q正传》的作者名姓的时候,他才知
道他和作者素不相识,因此,才恍然自悟,又逢人声明说不是骂他。”(第四卷第
八十九期)
我对于这位“某人”先生很抱歉,竟因我而做了许多天嫌疑犯。可惜不知是谁,
“巴人”两字很容易疑心到四川人身上去,或者是四川人罢。直到这一篇收在《呐
喊》里,也还有人问我:你实在是在骂谁和谁呢?我只能悲愤,自恨不能使人看得
我不至于如此下劣。
第一章登出之后,便“苦”字临头了,每七天必须做一篇。我那时虽然并不忙,
然而正在做流民,夜晚睡在做通路的屋子里,这屋子只有一个后窗,连好好的写字
地方也没有,那里能够静坐一会,想一下。伏园虽然还没有现在这样胖,但已经笑
嬉嬉,善于催稿了。每星期来一回,一有机会,就是:
“先生《阿Q正传》……。明天要付排了。”于是只得做,心里想着“俗语说:
‘讨饭怕狗咬,秀才怕岁考。’我既非秀才,又要周考真是为难……。”然而终于
又一章。但是,似乎渐渐认真起来了;伏园也觉得不很“开心”,所以从第二章起,
便移在“新文艺”栏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