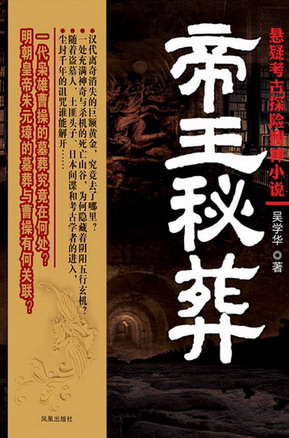二月河.帝王系列(全本txt)-第48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生。
现下看这顶帽子再好,已经不是自己的了……到底是哪一处出了漏子呢?盐税,是“整顿”重新建帐时,先从里边扣除了没收的私盐银子,数目只有三十四五万两,老帐簿子一火焚之。他有这个权,就是神仙也对查不出来。“官卖私盐”,其实是官店里官私盐两头收帐,下头人和盐商勾手,从里头抽头孝敬上来。三百万,不但抵了历年亏空,还落下一百二十多万。这是下头君子交易,根本没帐,空口白说查个屁!……那么是卖铜出了事?……本来已经向朝廷交待清楚了的事,偏是钱度在云南铜矿当官时要当清官,一个子儿没捞,离开铜政司才知道那差使肥得放屁流油,要在户部任上把吃过的亏捞回来,交待清了更不肯罢手,和安徽铜陵使合伙盗运,铜陵使又和自己合伙倒腾私盐,连铜陵观察御史、铜陵县令,一伙儿又弄盐又弄铜还倒卖木材人参,孝敬来的银子要是不收,翻了脸连盐务上的事都一兜儿网包漏蹄……高恒越想头越大,越觉得是钱度的事发牵连了自己。但乾隆的旨意也太含糊了,“荒淫”二字早有定论,如今谁不“荒淫”呢?“贪婪”,怎么说?别人送、自己要,坑蒙拐骗撞木钟说官司都是“贪婪”,教人从哪里入手去认罪?事到其间,他才真领教了乾隆的天威不测,才真知道下贼船要多难有多难……
驮轿一顿,停住了,濛濛细雨中,高恒戴着那顶假帽子下轿,打发了轿夫,已见薛白娘子带着两个丫头欢天喜地说笑着,从影壁后迎出来。拍手笑道:“我这眼皮子嘣嘣直跳,就想着爷不会在那里吃午饭。叫丫头张着,果然爷就回来了!”两个丫头是钱度的外宅曹寡妇代买来的,年可十五六间,也都十分清秀,都还没见过宅主高恒,怯生生地跟在薛白身后向他蹲了两个万福。
“唔。”高恒神情恍惚,阴郁的目光扫视了一下这座青堂瓦舍里外崭新的三进大院,说道:“给我烫酒,随便吃点什么吧。”说着便往里走。那婆娘哪知他此刻心境,高高兴兴跟着,口说手比道:“这边就是比扬州好!瘦西湖虽说美,难比玄武湖这般儿阔爽。你看,对面鸡鸣寺,雨里头看过去,云雾半遮着,真跟人家说的画儿上画的仙山楼阁似的,出门杨柳两岸,平湖映山,小水上飘儿打鱼船……哪找这地方去?——爷这边走,那边过了月洞门是水榭子花园。曹家嫂夫人在屋里张罗着等您呢!”
曹氏在二进院正厅屋里正在摆酒布菜,听见他们进院,满脸堆笑迎了出来,揩手弹衣蹲膝请安,活似天上掉下个元宝拾了起来般欢喜,说道:“哎呀呀!好我的高爷哩!我们钱爷说你七月半就来的,我还撺掇几个戏行姊妹给你预备唱戏接风,哪里晓得在扬州叫薛妹妹拌住脚了呢?快进屋来,雾星雨儿透衣裳,这天气最容易着凉的……”一头说,一头将高恒往里边让。她虽已年过四十,开行院出身的惯家积年会梳妆,已巴髻儿头油黑漆亮,光可鉴人,刀裁鬓角黑鸦鸦的,白生生的面庞因作养得好,隐隐带着红晕,腻脂似的,不细看,连眼角的鱼鳞纹也不甚清晰,颦眉秀目,笑靥可人,仍旧是楚楚婷婷一个少妇模样儿。
高恒暗地里与她也有一脚的,但此刻却半点情致也没有了。他走了定神,打起精神敷衍,跟着两个女人进屋,一边思量着问钱度近况,忖度着该不该把坏事讯儿透给她们,坐在桌前,由着丫头斟酒。举杯笑道:“——今日有酒今日醉,莫问明日是与非——来,碰了,干!”“啯”地一口咽了,亮杯底儿,给曹氏和薛白一人夹一著菜,自己也吃,笑问“如今有多少张织机了?听说又并了两个机坊?”
“那还不是托了爷的福?名声在外说是‘千机曹’,其实开机织绸只有不到六百张机。”曹寡妇鸨儿出身,什么眉高眼低看不出来?早见高恒神色不宁,却不急着问,柔荑般的手把定了酒壶,只情殷勤相劝“这是贺你和薛姑娘乔迁之喜的,高爷您干了,薛家妹子陪着……宁绸利息大,除了贡绸,一多半都运葡萄牙红毛国法兰西去了,咱们中国百姓,曰南交址爪哇国,还是土布、市布。说是我并了人家的坊倒不如说是人家入了我的股。一来我的绸子织得匀细,扬州府专门染坊染的,颜色质料谁也没个比,好卖;二来开机坊的,工人里头病多,都挤在一搭搭儿,一个传瘟就不得了,叫歇的砸机子的,吼天吼地在坊子里闹,投毒放火地害业主。你往东走二里,那里现在一片白地,原来可是机坊连机坊呢。方家机坊业主一死十二口,还烧死二十几个工人,那个可怜哪,石头人见了也伤心落泪啊……”
薛白睁大眼听她说话,不由的问道:“并到您的名下,就不会有这种事儿么?”
“妹子你不懂,这里头有学问。”曹氏给他们酌酒敬劝,叹道:“待工人就我心里头,跟在行院行里待姑娘一样,一哄二打,小意儿妆裹不能省;人多了,用工头也是这几条,病了死了丧葬医药跟着,糟心事就少些;宫府里还得有人,这就是我方才说的‘托福’了,不然,死了童工,缫丝的风湿瘫了,一状告进衙门——真的判你输官司也还痛快,他不,不说长不说短,拿了人监候‘待审’,捉一大堆‘人诬’天天到衙磨问,论千论万的银子往里填还!再就是码头管事的机帮,相与好了,他们护你,没有痞子来骚扰;相与不好,他们自己就是痞子,进坊子里调戏女工,毁机子——我占了这三条,坊子安稳,别人投到我名下也不过图个清净。但机坊大了,事情也多,开销应酬也更多,里头的苦衷也是一言难尽啊……”她劝二人吃酒,夹菜添着口不停说,长篇大论讲诉,从购桑叶、暖蚕子儿、三眠成茧,到缫丝织绸发卖,怎样腾挪活钱银子,怎样调教工人收拢人心,真个也是一年到头五更黄昏地忙活,“……妹子说这里景致好,我还从来没有坐船到湖上逍遥一天呢!要论安闲消适,真不如原来开行院,哄得姑娘接客,姑娘客接得顺当接得好,雪白的大腿一撇拉银子钱就哗哗流进来……”她自己也吃了几盅,说话口没遮拦,露出婊子本色来。
高恒被她们左一杯右一杯只情灌起,他满腹愁肠的人,只索用酒去浇。此刻也混忘了东西南北,苦中作乐笑道:“真的是这样儿,你要是不在钱度跟前撇大腿儿,就能成石头城有名的富婆‘曹寡妇’了?”“你这人真是的!”曹寡妇指尖儿顶了一下高恒额角,“薛姑娘就在跟前呢!”高恒笑道:“只要钱度不在跟前,没得醋吃!”他突然心里一动,又想到自己眼下处境,因问道:“钱度眼下在哪儿?好长日子没见着他了。”
“去武昌了,昨个儿还来信儿,叫送三百匹缎子,漂白素色的——说有个洋鬼子要买。”曹寡妇瞟他一眼,“难道高爷还不知道?他帮勒中丞调度金川钱粮去了。”
高恒真的是不知道,皱眉苦思乾隆革自己职的诏旨日期,想想竟是没有宣读。因又问道:“钱度在故宫东首还有一处宅子,他来南京在那里办事接待人,你近来去过没有?”
“我刚才去过的。他两个儿子都住在那里。”曹寡妇想起自己的亲生儿子都不敢认,见了面一口一个“曹家的”叫自己,心里一酸,几乎落下泪来,忙别转脸擤了一下,回神笑道:“怎么忽拉巴儿问起这个——那宅子我三天两头去呢!两位少爷都还小,余下的都是老婆奶妈子丫头,连老鼠都是母的。”
高恒手抚脑门子,停了杯,长叹一声道,“都不是外人,我实话实说了吧!赶紧生法儿,把你两个宝贝拐着弯儿接到你身边,或者寄养到亲戚家——防着出大事!”说完只是发呆。
一句话说得两个女人都慌了神,曹寡妇紧间:“到底怎么了,好歹给我一句明白话!”薛白脸色煞白得没点血色,晃着高恒道:“高爷高爷!您甭只是愣神儿,好端端去了一趟尹制台那儿,回来就跟丢了魂似的——一进门我就看出来了,说给我们,也好一道拿个主意嘛……”
“连我也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情。”高恒喝了两口酽茶,苦涩地咽了,将方才尹继善宣旨,和自己一路想的一古脑儿讲说了,见两个女人唬得目瞪口呆,一笑说道:“我也宣旨剥过别人官职顶戴,别吓得这种熊屄样儿——旨意里训人,哪个不是狗血淋头?过后该没事的还没事!皇上现就在南京,兴许是他私访出来点影子闹出来的,也许是刘统勋老小一对王八蛋砸我的黑砖,老子不开口神仙难下手,提起来一条,放下一堆,叫他们勘问!刑部大理寺那起子贼官,有几个不吃黑的?他们也有把柄在我手里!曹老姑奶奶你听我说,安顿好你儿子,派妥当人去见钱度,赶紧收篷弥缝儿——不要写信!我的帐查不清,最终还是清楚不了糊涂了!”
“那我呢?”薛白没想到一来南京就挨这么一闷棍,头晕心慌身颤手摇,尽自高恒夸口,她也知道事情凶险莫测,由不得问道:“我该怎么办?”
高恒略带浮肿的眼泡儿掀了掀,苦笑道:“行李马搭子里头还放着些银票,几十两金子,满够你使的了。我封着子爵,爵位还在,进不了班房。要真的掩不住,兜底儿翻了,你别回扬州,在这里不显山不显水安生过活就是了……”
“我,我好……命苦……”
“你没吃什么亏。”高恒冷漠地看着门外风雨凄迷的院落,说道:“干净利落和我没瓜葛,要不然,你还得往养蜂夹道的狱神庙给我递送饭食呢——就算到南京跑了一趟赚钱买卖就是了………
“爷!您怎么这样儿看我?我虽然下贱,是真心要跟您,我不是那种人……”
高恒一声也不言语。
曹氏垂泣陪泪,良久叹道:“爷别说这些丧气绝情话……我们身子贱,论心,只怕比那些贵人们还要值钱些!”她猛地想起高恒的姐姐,急道:“事到如今,别人指望不上,难道贵妃娘娘也袖手旁观不成?还有爷的那些好朋友,傅相爷、桂相爷,正是用得着他们的时候,果不成里头连一个讲点义气的都没有?”
“你们不懂。这不是小门小户家亲戚样儿,舅爷姑奶奶说见就见。”高恒长吁一口气,尽力搜罗着想自己朋友里哪一位是“讲义气”的,一时竟连一个也想不出来,口中道:“就是见着她,也比你们强不哪里去。紫禁城各宫门前,世祖圣祖世宗爷都立有铁牌谕旨‘后妃干政者杀无赦!’——白教她着急而已!这种事,只可借她的势,不能用她的力——”他突然想起,临离北京时去见棠儿,棠儿说想给皇后送一块葱绣万字璇玑图压灾。他一直认为,棠儿对自己并非绝无情意,只是沾了乾隆身子自高身分,不便和自己有私情而已,填送棠儿那许多珍奇宝物,总不至于连点香火情分都没有——他突然打住,顺着这个思路,越想越觉有理,眼中放出光来。说道:“曹家的,记得你上次说,藏珍阁有一块万字璇玑蕙绣,贵得吓人,出手了没有?”
曹寡妇一怔,说道,“这会子爷怎的问起这个了?没呢!半月头里,藏珍阁老板来问,说情愿落点价,六千银子出手。我说你给我收着,蕙绣遍天下也只有十几块了,贱卖了你后悔。藏珍阁藏珍阁就是‘藏珍’的嘛……”高恒问,“他原价是多少?”曹寡妇道:“六千八百。”
“六千八就六千八。”高恒站起身来,“今明两夭就给我买过来,我有使处。”至门口望着外头出了一阵子神,说道:“薛白给我取一件夹袍,颜色素一点的。我到驿馆打个卯儿,该拜的客人还要访一下,看情形再说。”薛白便忙着打发人传轿子,替他挽衣裳,又让他含一块醒酒石,送他出门打轿而去。
屋里只剩下两个女人,面对满桌残杯剩菜,竟一时无话可说,渐浙沥沥的雨声中呆坐移时,薛白目视曹寡妇,恰曹寡妇也看过来,目光一对,都是一个苦笑。
“我们两个是一样的命,”许久,曹寡妇才道:“有道是同病相怜,想跟你说几句知心话。说错了,就当我没说。”
“嗯,婶子只管说。”薛白满腹心思点点头说道:“我心里很乱,想听听老人家的话。”
曹氏叹息一声,说道:“南京这地方,官道儿上是南京知府的天下,是尹制台的天下,黑道上是盖爷管着。你我都在教,又都有点子产业,其实是脚踩两只船。”
“这话再真不过。但盖英豪和易主儿并不一回事,盖英豪兴许是想自立门户,不大听号令,不然,易主儿这次就不来了。”
“盖英豪哪里是想自立门户!”曹寡妇细白的牙齿咬着嘴唇,说道:“他是甘凤池的大徒弟,甘凤池死后,接掌南京江湖道舵把子。原先,想投靠病去了的李制台,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