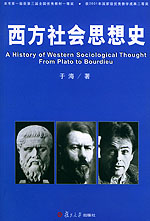自我认识思想自传-第3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比起旧制度的监狱,契卡的监狱制度更加难以忍受,比很多革命监狱的纪律更加严酷得多。 至于捷尔仁斯基,我的印象是:一个令人尊敬的和诚挚的人。 我想,他并不是不好的人,甚至按本性说并不是一个残忍的人。 这是一个狂热的人。 他给人的印象是:为某种情感所控制,在他身上有某种可怕的东西。 他是波兰人,身上有某种高雅的东西。 过去,他曾想成为天主教的修道士,他将自己狂热的信仰转向共产主义。在逮捕后过了一段时间,“策略中心”案进入诉讼程序,在被指控的人中,有些人与我有私人的关系。 诉讼过程给人以十分沉重的印象,这是戏剧性的表演,一切都是预先安排好的。某些被控者引起很大的尊敬,但是还有一些则是不值得尊敬的、屈辱的。 判决不特别重,是象征性的。一段时间里我的生活比较平静。从1922年春天情况开始改变。 形成了反宗教的阵线,开始了反宗教的迫害。1922年的夏天我们到兹韦尼哥罗德县去,它在巴尔维赫,在十分迷人的莫斯科河岸边,靠近阿尔汉哥尔斯克的尤苏帕维依,那时托洛茨基居住在那里。 靠近巴尔维赫的森林非常迷人,我们被成群的蘑菇所吸引,我们忘记了可怕的制度,在农村对它的感受较小。 有一天我回到莫斯科,这是整个夏天唯一的一次回莫斯科,我在自己的房子里过夜,夜里进行了搜查,并
…… 271
俄国革命和共产主义世界752
逮捕了我。 我被驱逐出苏维埃俄国,我被预先警告,如果再在苏联境内出现将被枪决。 这以后我被放了。 但是大约过了两个月(在这期间需要为出国作准备)
,整整一个作家、学者、社会活动家群体被驱逐出境,他们被认为没有希望转向共产主义信仰。 这是一个奇怪的标准,后来它没有再使用过。 我被驱逐出祖国不是因为政治上的原因,而是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当他们宣布要驱逐我时,我是很苦闷的。 我不想侨居,我与侨民有冲突,也不想与他们汇合,但同时我又感觉到,我将要去一个更加自由的世界,能够呼吸自由的空气。 我没有想到,我的流亡会长达25年。 德国大使馆很帮助我们,在德国入境处给被逐者个人办了签证,但是苏维埃政权拒给被逐者以集体的签证。 德国人给予我们一系列的服务。 有时我为了被逐事宜到格佩去,顺便说一下,我请求明仁斯基加快放逐。 有一次我在格佩等待管理被逐事宜的侦察员。 我惊奇地发现,在走廊及接待室里坐满了教士,他们都是(东正教)
新生教会教徒。这使我产生了很沉重的印象。对“新生教会”
我是否定的,因为它的代表人物是靠告密大牧首和大牧首教会起家的。我认为,它这种做法不是改革。在格佩接待室里,我遇见了安东尼主教,我过去在彼得堡见过他。 安东尼是最有才干和最进步的俄罗斯主教之一。 在宗教—哲学会议上他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在教会恢复中他起的作用是不美妙的,他经常恐吓和告密。 安东尼走近我,吻我,想和我进行隐秘的谈话,回忆过去。 我则向他表明,在秘密的格佩,这是不合适的,我与他之间也是非常冷淡的,这是我离开俄国时最后的印象之一,而且是不愉快的。在路上我感受到很多的痛苦,
…… 272
852自我认识
而且前面是什么在等待着我们也不清楚。 在流放中,我感到了某种天意,它决定了我的命运。
G在国外我写了很多论共产主义和俄国革命的文字。 我企图思考这不仅对于俄国的命运而且对世界的命运有着巨大意义的事件。 我作了思想上的努力,以便超越双方的斗争,清除情感因素,不仅看到共产主义的某种局限,而且看到它的真理。 观察俄国侨民的情绪时,我发觉,我是能从对共产主义的态度的偏见中解脱出来,不被自己与它的思想对立所左右的极少数人之一。 这也引起了对我的敌视。 我与共产主义相对立的首先是精神自由原则,对我来说,这一原则是原初的、绝对的,用世界上任何财富都不能出售的。 我与共产主义同样对立的另一原则作为最高价值的个性原则,它不依赖于社会和国家,不依赖于外在环境。 这意味着,我保卫的是精神和精神的价值。 俄国共产主义,正如它自身在俄国革命中所暴露出来的局限性,否定自由,否字个性。 我赞成在社会方面,即政治组织和经济组织方面采用共产主义,但是不赞成在精神上采用它。这完全不意味着,我是反社会主义者。我是社会主义的拥护者,但我的社会主义是个人的,而不是专横的,是不容许社会凌驾于个人之上的,是从每一个人的精神价值出发的,因为它是自由的精神,是个性,是上帝的模式。 我不容许个人良心的压抑,不允许将其转移到集体中去。 良心在个性的深处,人在那里与上帝交往。 集体的良心只是隐喻的说法。 当人的意识被集体崇拜所掌握时,它就完
…… 273
俄国革命和共产主义世界952
全改变了模样。共产主义中的社会内容可能是真理,是反对资本主义之恶、反对社会特权之恶的真理。 后来,对宗教的态度在苏维埃俄国发生了变化。 极权主义,作为极权的法西斯主义和民族的社会主义,要求抛弃宗教的和道德的良心,抛弃作为自由精神的个性的最高价值。 古代的神权国家是暴力的极权主义的典型,现代的极权主义则反映了宗教的需要,并且是宗教的代用品。 对于基督教来说,极权应当成为过去,它是自由的,而非强制的极权的。 自从神权国家的暴力极权主义崩溃以后,极权主义成了特殊的现象,它将精神驱赶到一个角落里,并将其从全部生活领域中排挤出去。 按实质说,极权主义成为也应该成为特殊的——国家、民族、种族、阶级、社会、集体、技术。 现代的悲剧的根源就在这里。有意思的是,宽大的和比较有文化的共产主义者K。,在我被逐出苏俄时对我说了一段奇怪的话(他是“艺术科学院”的主席,而我是成员)
,他说:“在克里姆林宫,人们都指望到西欧去。 您现在去那里,要站在真理的方面。”这应该意味着,我将走到非真理的资本主义世界去。 这些话只有克里姆林宫的老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才能说,而新的形态的共产主义者大概不会说。 为了明白资本主义世界的非真理性,我并不需要流亡到西欧去。 我一直明白这个非真理,我一直不喜欢资产阶级世界,在《创造的意义》中,比我所有的书都更有力地体现出这点。 到西欧之后,由于充满激情的内在原因,我恢复了年轻时的社会观点,当然是在新的思想基础之上。 这样就产生了两种精神的反动——反对周围的资
…… 274
062自我认识
产阶级——资本主义世界的反动;反对俄国侨民的情绪的反动。 我一直倾向于对周围环境的抗议,我决定反对它,然而这也就是依赖性。 我有很强的矛盾精神。 但我完全不指望克里姆林宫宣布我无罪,我坚持在精神上反对极权主义,不论在俄国,还是在西方。 也不和不学无术的和躁狂的侨民集团混在一起,他们认为我如果不是共产主义者,也是一个“共同体主义者”。实际上,从形而上的意义说,我比那些侨民不同流派的代表(他们的意识是由集体主义构成的,他们承认集体、社会和国家高于人性的原则)是更极端的共产主义反对者。 我一直是极端的人格主义者,承认个人良心的至高无上性。我是热衷于个人的一个性的、独特的东西的现实性,而不热衷于社会和集体。 但是,比起社会个人主义来,形而上学的人格主义的社会反应完全是另一样的。 我明白,人们按照已经建立起来的模式来了解这个是困难的。 翻转了现实性概念的人格主义是艰涩的形而上学学说。结果,我企图制定很艰难的历史观。 它完全利用对社会生活的观察,还利用历史书籍的阅读。 人们是周期性的,他们带着很大的热情唱道:“由热情激荡的、游手好闲的、被血染红了的手,引导我们走向为了伟大的爱的事业而死亡的营地。”
再往前延伸,带着可怕的祭品,献出自己的生命,但是,当他们取得胜利并庆祝时,很快又把自己变成“热情激荡的、游手好闲的、被血染红了的手。”那时,出现了新的人们,他们想离开“死亡营地”。历史的悲喜剧就是那样的没有尽头。只有千年王国凌驾于这一切之上。
…… 275
第十章流亡的年代
1922年9月被放逐的一群人从俄国出发,我们经过彼得堡,从彼得堡走海上到斯德丁(波兰)
,从那里去柏林。 被流放者近25人,连他们的家属大约75人。 因此,从彼得堡到斯德丁我们租用了整整一条船,轮船的名称是“OberburgerHmist-erHaken”。
当我们沿着苏俄的海疆航行时,谁也不相信他不会再返回来。 与进入更大的自由天地的感觉一起,我还有与祖国不定期的离别的忧愁感。轮船在波罗的海上航行,这种旅行使我们有诗意的满足。 天气美好,夜里有月亮,几乎没有颠簸。 我们,被放逐者,不知道未来是什么样的,但感到自己在自由中,将要开始新的生活。 到了柏林,德国的机关很殷勤地迎接我们。 尽管我一直和西方的资产阶级性相冲突,但我一直还是喜欢西欧,从童年起就常常来到国外,我在柏林行走,产生了不同世界的强烈的反差感。 我没有由于流亡而苦闷,但我在所有时间里都为俄国而忧愁。 德国那时很不幸,柏林充满了战争的残废者。 马克灾难性的贬值。 德
…… 276
262自我认识
国人说:“Deutschland
ist
verloren“
(“德国输光了”)。
整个世界的覆灭和新世界的诞生与我在生活中所观察到的相符合。我看到人们中存在异乎寻常的转换,第一的成了最后的,最后的成了第一的。我的第一个沉重感来自与侨民们的冲突,大部分侨民都遇到秘密派遣的和不友好的一小群流亡者,事情甚至是这样的,请允许我说,这些人不是流亡者,而是为了分化侨民而秘密派遣来的。 在我抵达柏林不久,进行了一部分流亡者和某些属于白色运动的侨民代表的会见。 这些白色侨民团体的首领是司徒卢威,我过去和他有老关系。 我和他彻底断交,不再见面,中断了一切来往。 只是几乎在他去世前我们才和睦地相见。 在我的住宅里与白侨的会见以完全破裂而结束,我激烈地大声斥责,以至房屋主人出来把警察叫来。 我对通过武装干涉而推翻布尔什维克的道路进行了完全的否定。 我不相信白色运动,对它没有好感。 这个运动向我推荐的是过去生活中失去了全部意义的甚至已经变成了有害的东西,是一去不复返的东西。 我希望的只是布尔什维克的内在的克服。 俄国人民要自己解放自己。 我期望进入崭新的历史阶段,“白色”侨民引起我极大反感,他们具有顽固的死不悔改性,缺乏自己的过错意识,相反,却具有占据真理的自傲意识。 我感到,侨民的右的倾向现在不能克服,他们仇视布尔什维克完全不是因为布尔什维克消灭了自由。 思想自由在这个侨民的圈子里并不比由布尔什维克俄国承认得更多一些。 侨民情绪的敌对性使我备受折磨,由于对现实的无能为力,这里的侨民通常都产生一种躁狂,他们不论讲什么事情,总是除了布尔什维克以外,就是处处看到布尔什维克
…… 277
流亡的年代362
的奸细。 这是真正的心理变态者的集合体,而且至今也没有治愈。在1922年我曾发表过这样的意见:西方国家应当在形式上承认苏维埃政权,这样,就可以停止苏俄的隔离状态,它将深入于世界生活之中,能够使布尔什维主义的坏的方面变得温和起来。 这个意见甚至使左派侨民的代表大吃一惊。 到国外的最初时间我决定避开与俄国侨民的来往,而和流亡者团体保持较多的交往。 只是到了巴黎我才开始和较广泛的侨民交往,但主要是和左派侨民交往,这些人我还比较能够忍受。 在快要抵达柏林时,在流亡者团体中(他们中知识分子的力量不小)
出现了一系列创举,人们表现出很大的积极性。在柏林的第一个冬天,我成了自己所描绘的那种积极的社会活动家,倡导了不同的创举。 不久便使我很疲劳,在后来的年代里,我则埋头于自己特殊的创造思维。在流亡者中有科学家、教授,这使在柏林建立俄国科学学院成为可能,我积极参与了这个学院的创立,成为它的部门主任,在很大的教室里讲俄国思想史和伦理学。 德国政府十分关心这个举动,对它的实现给予了很大的帮助。 总的应该说,德国人十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