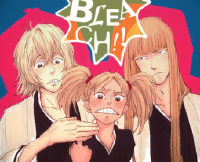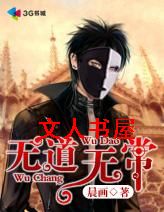������-��327��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а�̾����Ī�����պ�Ҳ����������һ�㣬�ڴ˹¿��㶡��һֱס�������սᣬ����������գ���
���������Dz����������и߰���������ƿһֻ����ƿ���켫�����ļ���Ȥ����ʵ�����ƿ��ˣ��������е�����Ҳ�Ǵ��������������������������������������֮ʱ�����Ǻεȵļ�į��
������������֮���������������˶�����Ȥ���㽫�κ�һ���¶���ͼ���þ��ƾ�������˲����д������ɴ������ģ�����į֮�飬�����������겻�ѡ�
������������ƿ֮��ԭ�����ɻ�һ�������ֻʣ��֦��Ҷ�ˡ���ǽ����ȥ��ԭ���ǻ����������������浹Ҳ��ʶ�õġ�
���������������ң������ǹ�ȥ��ȼ�����棬���ڷ���Խ��ʦ��δ���������档�ɴ������������˾���һλ����֮ʿ�ˡ�
����������������Ƿ���˫�ޣ�����Ҫ����λ���棬��Ҿ�ֹ����������������˸�����Ų����������֮�С�
��������ӭ��һ��ľ��������һ�ˣ��������£���Ų��ģ��������ݲ��䣬ȴ������ȥ��ʱ�������������ɽ��ʶ�������ȥ���꣬Ҳ�����ݲ��ģ����岻�ࡣ
���������������������֮��ס�����꣬Ҳ��������һ�η��꣬�������徻����֮�أ���ȻƬ�����������ʬ����Ҳ��Ƭ����Ⱦ���������¡�
����������������ǰ�ְ������ݣ�̾���������ޣ���Ԫ��δԶ��ֻ�ܵ����ң��������꣬��ٰ�ʮ�꣬����Ҳ�����ȥ�ˡ���
����������������ʿ����������Ҳ������������ˣ������г�һ������ħ������Ҳ�Ų������ꡣ
��������������⼫�ȿռ�֮�����У����������������ħ����˷��������屾��Ⱥ��֮�ԣ�������Ⱥ���Ӿ��ˣ���Ȼ������į֮�С�����ֻ֪��ʿ������ң��ȴ��֪��ʿ���еĿ��������ǿ���ľ�����������ʵ��������
��������Ҳ����������������������֮����������ȺDZ��ǧ���꣬Ҳ�����͵�ס������Ѱ������֮ʿ��ֻ����ͷ����ˡ�
����������������������������Ϊ���վ�δ���ɳ���֮�����ڴ��������ա�
�����������е���������Ǿ����Լ����³����������뵽�˴������ɾ��������ң��������֮�ж��Թ�������ǻ���ǧ��Ҳ�ã�������Ҳ�գ����ж������
������������һ���մ����Ǿ�����ʿԭ�����Σ�����������������ħ����˷��װ��ջ�������п���ʿȴ�����Ҫ��Ҳ�������ˡ�
������������֮�࣬���þʹ˰��֣�����Ѱ�������˴��������ˡ�
���������Һ�������������ᣬ��������һ˿��������ͷ��ȴ��ת˲���ţ�ͬʱ�����ְ������Ͼ��������ղ�������ʿ���������У�����ʵ������ħ����֮�ģ���������ʱ���ƴ������ħ����綾��һ�㣬����һ�ջ�������Ķ�־��
����������ʿ���Ķ��֣����������Լ��ģ����б������죬�����������ס�����ʿ��������㿼�飬�������ķ����ɽ磬������ͬ�ԣ�������ʿ��֪�ж���δ�ܿ�����ħ�����ʹ˳��١�
���������������Ƽ�����ʬ���ֳֹž�һ������������һ�룬�������ޱ��ǵ��������һϢ��Ҳ��������Ŭ�����������ɼ��߾��磬�����г�һ���뿪����
�������������氵����������ʿ��֪���˶����꣬Ҳ���ӳ����������������õ�����
��������������ͷҲ��һ����û��ֻ�����ܿ���뵽���㸹�еõ��Ķ��������ֻ�����ɵ��ɾ��磬�������һ�ԣ������˺��뿪�����������˱��������ɾ�ǿ�������ˡ�
���������������뵽�˴������Ƕ�־ӯ�أ�����������ʬ�����˸����Ž������йž�����ȡ�¡��ǹž����Ա�Ҷ�Ƴɣ��������ߣ�������â���á����������֣����dz����Ѫ������������ɰ��������ij����������֮Ѫ������־����֣����������˱ǡ�
�������������氵��������֪���������ģ�Ҫ����Щ�������ھ��ϡ���
���������Ӵ˾���ҳ���𣬺�Ȼ���������֡������֣�ʵָ����һ���滨���������������������һ�����������˾���������Ϊ��������Ȼ���Ƿ����ķ��е�һ�ˡ�
��������Ȼ�������滳�ź����ڴ�֮�ģ�ȥ����������ʱ��ȴ���Ǻ�������ԭ�����Ŀ�ƪд�����ף��������ߣ������滨��Ҳ���˻����в��֣�Ψ���ڷ��ӣ������ڼ���֮���������ޡ���
���������⾭����˵���������겻����Ψ�ȵ���٢��������ʢ�����ͺñ���������֮�£���������������֪���½����ӡ�
���������ɴ��������˾�������Ϊ��������ȡ���������һ֮��������˵����������������ޣ�����Ȱ�˲����Ըʳ��٣�Ҫ��Զ�������ġ�
��������������ղ��������⣬�ɲ�������˾������⡣
����������������ȥ����д����������������������Ϊ���ɾ����ɾ����ɾ����������������ɳɽ��ɴ��������֮����첻��֪���ʶ��������أ�Ψ���������֮ʿ����
��������������������ϲ�����������в��㣬����ϰ����֮�����������������ԣ����ɽ��ɴ�����ɲ��Ǿ����ӳ�����
������������ֻ���ɵ��ɾ��磬���������֮��������ӳ����죬��������������Ȼ�Ժ���˵��
������������æȥ�����г��裬�κ����˰��Σ��Ų��������������ģ��������������л��أ��������������������������������������պ�������Ѱ���ǡ�
�������������Ҵ������������ɣ����������ݣ�������������ǰ�Ļ��������ˣ�չ����Ҷ�������������С�
���������������ƣ��˲�����ȥ����֪�й�ȥ���˲���δ������֪��δ������˾��ģ����˾��������°빦��֮Ч��
���������������������룬�����������������������룬ֻ��ҡ��ҡͷ����������ȥ�������ֵ�������֮��������������������Ϊ�棬����Ϊ�٣������������Ϊ�棬�����Ϊ���ޣ�����ɫ����գ��ղ���ɫ����
������������ĸ��Ǽ��������ٰ�˼�������������֣��������е���ʱ�����֪������������������������һ�����ͣ��ǵÿ�˼ڤ�룬�������²��ɡ�
���������������������֮����������ħ���ķ���Ψ������һ��������������������ھ���֮�裬����֮�ѣ���Ҳ������������֮�С�����Ҳ�ã�ʮ��Ҳ�գ��������������֣������Ƽ���ϣ�����ڣ�����һ�գ����Ի��ɵ��ɾ��磬�ӳ�����
�����������ڳ�˼֮ʱ��һ���������������������������ž���һ�ˣ���һ���������磬��������������������⧲���������������һ�գ��������㱻����ȥ��
��444�¡��������гɣ�����
���������д����ܷ��ӳ�����ȫ���ⲿ������ʧ�˴˾�������Ҫ��������������ɥ�������к�����
���������Ƕ�ȥ������������ֻ��β��ȸ����������һ�������ݶ������˷����ƽ���������ƴ�����������ּ����ɶݣ����������������ԣ��ɶ�֮�٣��������������ݡ�
����������ȸ�������֮�����䱻��������ϣ�ȴ�ڿ���ת�۲�����һȸһ�����Ҹϣ�ɲ�Ǽ�����˲��ݡ�
������������ɽ��֮��ȸ���ɣ�������˿̵�Ҳ�����������������ж�������ȸ�ӵ�����ȥ������������Ѱ�������Ƴɣ�������٣�Ҳ�Dz��ס�
�������������ȸ�����ͬʱ�������ɼ����������ȸ���й�����Ī���ǰ�ȸ������������Ͻ��⾭����������֮�֣�
���������뵽������������ȸ���ѣ������ô����ݣ�ԭ���⣬������ͻ֮����������������
������������δ�䣬ֻ������¡��һ���������漱æ��ͷȥ�ƣ�ȴ��һ����ԭ���Dz�����Ȼ������ȥ���ͺ�����ֻ���δ��֣�����������һ�ţ�����������֧�����顣
���������������ߣ��������ڵ�ɽ��Ҳͬʱ���䣬��¡֮�������ڶ���Ƭ�̼����ɽ��ͳͳ�Ʋ����ˣ�ֻ¶��һ����ɭɭ�Ĵ����������ò����ġ�
���������������Ƽ����澰������Ҳ˵��������������������ͬɽ�ȣ���ǰ�������Ź֣�һֱ����ģ�����˿���ȫ�������ƺ�Ҳ�����������ס�
��������ϸ���Ǻڶ�������ɭɭ������ף������Ǽ�������֮�����������˴������������棬��ô˵�������ǰ�ȸ�ᾭ���������Ҫ������������ںڶ�֮���ˡ�
���������������������ȸ�����⣬�����ȸ��ȥ���Ѿ�ͣ��������һ��ϸĿ���������棬Ŀ�������⣬��ȴ�ǰ���ͦ�أ���̬�����ư���
�������������漱æҾ�ֵ�����ȸ�־���֮���������������ġ���
���������ǰ�ȸ��צһ�ɣ��������佫����������������ָȥ�������������������ȵ��������»ص����У��������Ƽ��˾���������������һ�������ǰ�ȸ��᳤�������طɽ�ɽ��֮�У��ܿ���ʧ������
�������������汾��ȥѰ���ȸ�ʸ����ף���ȸ����ͨ�飬�Լ���������������Ǻù�ͨ�ġ����Ƽ���ȸ���϶��ԣ��Լ�Ҳ������š������ȸ��̬������������û�����Լ��������С�
�������������氵���������ȸ�������������ж��꣬���ж��Dz��ף��ּ��Ҿ������δ���С�����ҡ�����֮ʿ�����Dz�����ӹ��Ϊ�顣��
�������������ȸ��ʧ֮��ңңһ�ݣ�������ԭ��ס����
�������������������������棬ֻʣ��һ����ĹǼܣ�������Ͼ���������������������֮�࣬Ҳ����¶�����⣬������Ǽ�Ϊ����ȡ��Щ��ľ֦Ҷ���ǣ��˿�ٲȻ���Σ��Ŀɾ��ˡ�
����������������ľ�ݵ����飬��������������ϡ�·�Ҳֻ�������������ˡ�
����������������������֣��������ٻĵ���ȥ���Լ���������������������ȸҲ�Ʋ����ˡ�
�����������¶��������У�ȡ����������������
���������ٽ����Ķ������飬���н�����ᡣ��֮������ȥ����֪��ȥ���������½������������ȥ���������ڣ��ʶ������䲻����������֮�£�ֻ����ѭ�������ã���Ȼ�����续��
���������ɼ���ȥΪ����Ϊ����
����������֮����δ������֪δ�����������֮������֮����δ���̲�����⣬�����Ӳ��������ѭ�����ñ��Լ������������������ܴ�ɵ��ɾ��磿�������ӳ������ˡ�
�����������δ���䲻��֪�������ʹ˳����ǰ����δ�����Ǻ���ϣ����
���������������������Ŀ�ƪ���ԣ�˵�ľ���������������Ȱ����ѧ֮�⣬���������棬���ɻķ��˹�����
����������������������ּ�����д�ϲ�����ŵ�ʤ֮�ƣ���ȥ������ġ�
������������֮��������������������Ϊ�棬����Ϊ�٣������������Ϊ�棬�����Ϊ���ޣ�����ɫ����գ��ղ���ɫ����
���������������������飬�ھ���˼�����������˵���Ϊ�������ɲ��Ǵ���������һ��һľ�������������У����ؾ������ˣ��Ѳ��������в�ȥ����أ���ر㲻���ˣ���ʵ����ػ��Ǻö˶˵����������
���������⾭��֮�У������ǡ�ɫ����գ��ղ���ɫ�����ѽ⡣��������˼�������գ�������������
��������������գ����������п�˼��ֻ��������ξ��ģ������������֣������������������⾭����ʵ�벻���ף�ÿ�����о����̻���������ʵ��ʹ�����
����������һ�����־���˼�������������ƣ��㵽�����߶�����֪����֮�У���������һ�����ڣ���һ̧ͷ���Ƽ��ǰ�ȸͣ��֦ͷ�ϣ���͵͵�������Լ���
�����������������ն��������ã���������������������ȸæһ��ͷ������ȴײ������ɽʯ������ɽʯײ����һ�롣�������Żţ�Ҳ�����ᣬ���Ҵҵؾ��߿��ˡ�
�����������˵ڶ��գ�������������������ʹ��������������������ֻ���Լ�������������ɽʯ��ײ������֪��ֱ�����շ��Ż���������
��������������ճյ�������磬�����������һ�����͵ش�е�������Ȼ�������������
��������ԭ����������ͨ���Լ���ɽʯ��ײ������֪�����е��������ζ��
�����������˶���صĸ��ܣ���������������ʶ���ˣ�������ʶ������غ��Ը�֪����ʶ��ɥ������ز����ӡ�
����������������ȥ����ر���һ�㣬�����˶���صĸ�����ȫ��ͬ���ɼ���صĴ��ڣ���ʵ���������˵���ʶ���ܰ��ˡ�
���������������֮������������أ�����ֻ���Ƽ��Լ����Ƶģ��ͺñ���ä���������ܿ���ȫò���ɴ�����������˵�����ã��Ѱ��
�����������д����Ǿ䡰ɫ����գ��ղ���ɫ����Ҳ�ǻ�Ȼ�����ˡ�
�����������������������Ϊɫ����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