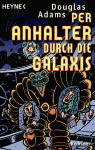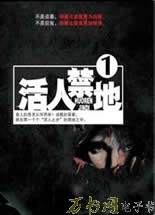细沙河-第1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秋信去姥姥家了,秋华舍不得,和妈妈商量几次,妈妈也有几分犹豫。秋智忙着和德福大爷写春联,也顾不上惹祸了。
明天就是小年了,根生妈妈回来了,从火车站走回来的,春兰陪着回来的。走到村头,大伙都看到了,都试探着和她打招呼。她挺明白的,边说话边走,春兰在后面跟着,她径直走到自己家,春兰放心了。她一进屋,把姐弟俩吓了一跳,真是又惊又喜。根生哇地哭了出来。
根生妈说:“哭啥,把鼻涕擤了,说你多少回了,这妈是离开几天,妈要是死了,你还不活了咋地。你小妹呢?”
春花说:“我大姑抱去了,过完年送回来。”
根生妈一听就急了,说:“明儿个就小年了,在姑姑家算咋回事,赶紧接回来,穷家也好,破屋子也罢,还是自己家。”这时,刘老师来了,拿来些东西。秋智妈也来了,拿来几卷豆皮。根生妈已经会抽烟了,坐在炕里面也不让别人抽。春兰把弟弟妹妹叫到外屋,嘀咕了一会儿进屋了。刘老师说:“二嫂,城里多好,你多待几天啊,这家里没事。”根生妈点着烟,抽了一口,也不吸,直接吐出来。
这个村子女人吸烟的不多,春花看着不舒服,刚要说话,根生妈说了:“大夫也说,过了年让我出院,我也没啥大毛病,就是神经性头疼,又快过年了,孩子们没人做饭。这么多年了,习惯看山了,还不得回来看山,你说是吧,刘老师。”秋智妈和刘老师对看一眼,听她说话还是病态,说着一些莫名其妙的话。春花想不让妈抽烟,看她说话前言不接后语,抽一口烟,低头想一会儿,嘴里嘀咕几句,忽然又笑了,自己又感觉不对,抬起头来对秋智妈说:“二嫂,让你想着,你家也不富裕,我二哥又才走,五七我们都没赶到家。根生,你爸呢?”
春兰抢着说:“妈,你又糊涂了,我爸不是和春生去口外赶马去了吗?来去得一个多月呢。”根生妈往炕沿挪了一下,扔掉还没抽几口的烟,使劲地咳了一下,一口浓痰吐在地上,几个人吃了一惊。
根生妈说:“这活牲口,找了一个好活,一准儿是他爷爷争的,一天十二分,六毛钱补助,每天还给一斤小米。这爷俩这一个多月挣不少,年在哪不是过啊,就是遭点罪,怕春生受不了,他爸倒是去了几趟了。看这样,这坏分子帽子是摘了,是吧,刘老师。”
刘老师一听,这说得太明白了,条理也清楚,赶忙说:“摘了,不然能让他去买马吗?这可是大队的差使。”
根生妈脸上放出光来,说:“我听春兰说了,好几个生产队的牲口都让濑歹掏了。要不咋又去口外呢!我知道七队的那俩骡子,头年赶回来的,这是咱们惹着濑歹了,都是看山的,各管各摊儿,就不能出这事。我给这死鬼说多少回了,他就说我是疯话,还训我,‘濑歹就是濑歹,啥他娘的山神。’你看看,啥也不懂。”
刘老师不敢顺着她的话题说了,岔过去说:“二嫂,我给你端过来一小簸箕黄米面,明儿个蒸年糕吧。这还有一刀肉,明儿个晚上辞灶,可不能用素饺子。我们走了,天也不早了。”根生妈要下炕送,两人不让。
刘老师和秋智妈走出来,刘老师说:“二嫂,这黄米面是他叔拿到厂子里用粉碎机粉的,用一分的锣(粮食粉碎机的计数方式),可好了,你看,这过年了,粉点啥不?我让老花拿厂子去。”
秋智妈正犯愁呢,说:“刘老师,又得劳动你公母两个,那感情好了。不用他叔带着,明儿个让秋仁送去。我也就是听说有这机器,还没见过。”
刘老师说:“厂子扩大了,从外地来了许多工人,现在厂子将近三千人了,说还不够。食堂就置办了粉碎机、碾米机。二嫂,你要碾小米,就让秋仁带着。现在老花是班长,没事的,别的光也沾不上。”秋智妈千恩万谢的,刚走出几步远。
刘老师说:“二嫂,还有一件事,就是刚才说的厂子事,他们要招临时工,你让秋义在公社给说一下,让你们老大去。我们老花也找一个,就安排春生吧,他家太可怜了。现在就是秋廉这关难过,我都告诉春生了。二嫂,我走了。”秋智妈答应着,看她渐渐走远了。虽然穿的有几分臃肿,好看的身材还是凸显出来,朝着落日的余晖走去,看上去整个人在放光,一片一片的闪着。“好人呐。”秋智妈心里感叹道。回去就和秋仁商量。秋仁高兴,说第二天碾米时再去找秋义。
第31章 真正的年味()
小年这天下午,各家各户都大烟小气的蒸年糕。秋智对这一天记得最清楚,这天的样子一年都在脑子里晃荡。在德福家,中午挂钟刚打过一点,秋智就回家了。到家时,妈妈正在搓黄米面,二姐在往灶里填木头。蒸年糕是个技术活,秋智妈是一把好手,还有蒸馒头也是拿手活。按理说,北河是不缺面粉的,他们这里是山地,不种麦子,只靠过年过节分的大米和白面,蒸一锅馒头也就太金贵,庄上很多人都来找秋智妈去蒸,根生妈也行。蒸年糕时,先把锅里添合适水,放好篦帘,帘上面铺上菜叶,菜叶上面铺一层芸豆,灶下大火烧着。满满的一大簸箕黄米面用温水拌匀,水的温度很关键,太凉,年糕夹生,太热又烫死了。拌的既不能干又不能涝,拌匀后,一层层往锅里撒,最后又撒上一层芸豆。然后盖上两层锅盖,如果锅盖密封不好,还要在锅边再捂上毛巾,还要把大簸箕挡在门口迎风的地方。秋智妈放好后,说:“大智和秋信把门关严,去屋里等着。”就是怕锅封闭不严,冷气进入。秋华也进屋了,秋智妈在烧火。兄弟俩什么也做不下去,贪婪地嗅着年糕味儿。实际上,年糕味才是真正的年味。
秋仁去公社了,大嫂在照看孩子,怕这时节过来闹。过了一会儿,秋智妈进来,用门帘子擦了一下脸,怕热气进屋,擦了一下就快放下。几个孩子看到,妈妈脸上全是汗。秋华问:“头遍火烧完了?”秋智妈点头。
秋华说:“二遍火我烧,这活有啥难的!你总得教会我们吧。”
秋智妈说:“以后上你婆家学去吧,这是你大娘送的黄米,加上你大哥家的柜底子(剩余的最后一些),我可不敢糟践了。”
秋仁在窗子外说:“妈,我回来了,先把粮食放外面了。”他看关着门,知道现在不能进去。
秋智妈说:“行,你先回去,过二十分钟都过来,让你媳妇做菜。”秋仁答应着走了。过了一会儿,秋智妈又烧了一遍火,热气渐渐消了下去。打开门,一股热气喷出去。
秋仁一家四口进来了。秋仁家的把立武、立雯放到炕上,去洗菜切菜,麻利的放在锅里。秋智妈把锅边毛巾拿掉,掀开一层锅盖,热气有气无力的往上冒着。只等菜熟,年糕就揭锅了。秋智早就下炕了,里外走着。秋信也直喊饿。秋仁家的说:“妈,菜好了。”秋智、秋信已经进屋了,这时“噌”地又跑了出来,秋华搬桌子、拿碗筷。秋仁想起粮食还在外面,都拿了进来。秋智妈掀开锅盖,一股年糕的香气迅速飘进每个人的鼻孔里,年糕上的芸豆红彤彤的,又大又鼓。秋华拿着两个大盘子走了过来。秋智妈说:“先拿碗,用铲子蘸上凉水,一块块切在碗里。”秋仁已经把红糖化成了糖水。秋信、秋智自己端着碗上炕了。还没等倒上红糖水,两个孩子已经吃掉半块儿,秋华直喊别烫着。秋仁心里不是滋味。
锅里烧着火,把菜盛到大盆里,下一锅在西锅蒸。秋义在家住,也好热炕。秋智妈说,“秋华,看下你二哥回来没。”
秋仁接过话头说:“他说了,中午回来吃年糕,都快三点了,也该回来了。”正说着,外面响起洋车铃声。秋义走了进来。秋智、秋信撂下碗筷,盯着二哥的大袋子。秋义把袋子放在地上,说:“瓜子、榛子、糖块。”看着两个兄弟盯着自己看,装作看不见,脱鞋上炕吃饭了。秋信问:“二哥,没有了?”
秋义装糊涂:“啥啊?”秋智和秋信互看了一眼,沮丧地接着吃年糕。秋义笑了,说:“两个傻小子,鞭炮有往屋拿的吗?”秋信没听明白,秋智高兴了:“我说嘛,二哥,多少?”
秋义说:“我不说过吗!多了一挂小鞭,都是二百头的。一挂年午黑夜放,一挂送年用,一挂你们俩散拆着玩。”
秋智妈说:“咋才回来,大伙儿都等你呢。”秋义想要说啥,咽了下去。吃完饭,秋智妈去蒸年糕。秋仁媳妇把蒸过的年糕切开,拿过一个筐,一块块放进去,过年再吃了。然后准备晚上辞灶。秋义说:“哥,刚才我去了大哥家,要不早回来了。”
秋仁说:“妈还正想等你回来告诉你呢,你倒先去了。大哥咋说,都说他这方面差劲,不至于亲叔兄弟都拦着吧?”
秋义说:“看大哥那样挺为难,咱们是叔兄弟,你别忘了,还有秋洁、立世呢。他倒是没一口回绝。”
秋仁说:“这么多年,谁不知道谁啊!那年咱们这儿接电,全县招架线工人,咱爸都打上门了,他也没放我,这你是知道的。不管咋说,秋礼能去当兵了,他这也算一点兄弟情义。现在你在这位置上,他有点怵你是真的,要不然早说死了。”
秋义说:“大哥,你不知道,秋廉这人吧,特别奸,全国在清查‘三种人’,就是打砸抢的。他还看不透我是不是属于这种人。”
秋仁着急了:“那你是不是啊?”
秋义说:“大哥放心,我肯定不是。今儿个我去厂里说你的事,直接找团委的,我们认识。我们还核计了我的情况,他也说不沾边。”
秋仁说:“这么说,我的事你都和厂里说好了。”
秋义说:“说好了,就看大队了。”
秋仁说:“这次他再拦着,不出手续,我把他脑袋打碎了。”
太阳快落山了,根生妈在切肉。切了一小碗做饺子馅,只放点葱花。根生最喜欢吃妈妈做的肉馅饺子,只不过是一年只有一次,就是今儿个晚上,饺子馅里的肉块切的也多一些,放上葱蒜,浇上酱汤,在锅里轻微的炒一下。每次只包十几个,多也就是二十几个。因为是两顿饭,中午年糕吃的饱饱的,晚上也就是吃两三个。
第32章 上天言好事()
这时刘老师来了,没进屋,春兰和根生迎了出去。刘老师告诉春兰,刚才,秦秋廉去她家了。说起招工的事。是老花前几天找的他,告诉他和厂子说好了,大队出手续就行,过了年就能上班了。秋廉原话是“刘老师,你们公母俩是热心肠,我不止一次说过。现在大队一个招工指标不外放,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再说,何平的事定性到底是啥,公社也没有明确指示。”老花开始还好言理论,最后红了脸,说了难听话。春兰心里也不平,耐心地听刘老师说:“春兰,我听说你爸他们年前回来,要回来让你兄弟自个去找。不回来就让你爷爷去找。不管咋说,这个机会不能错过。”说完就走了。春兰说:“根生,和我去队部找爷爷。”
秋智妈也在犯堵,刚才秋仁哥俩的话,她断断续续的听到一些。中午又是吃的年糕,就感到心口难受。这要能进工厂,就有转正吃红本的机会,就是转不了正,工资每月就有十八元五,再加几个班,每月二十多块,他们一家四口,吃香的,喝辣的。她打定主意,明儿个去找秋廉。
到了晚上,全家人都回来了。秋仁媳妇在灶王牌位前放上桌子。上面摆上两双碗筷,放上香炉,在里面烧上三炷香。旁边放着一个大茶缸,茶缸上写着“为人民服务”,秋智也不知道说的是为谁服务,摆到灶王爷爷和灶王奶奶这儿,肯定说的是他们。茶缸里放着一个白瓷酒壶。秋智妈走过来,取下酒壶上的两个酒盅,倒上酒,屋里飘着高粱酒那刺鼻子的辣味。秋仁媳妇拿勺子盛饺子,秋智妈双手捧起碗,接过饺子,把碗放下,毕恭毕敬地做了一个揖。秋仁媳妇又盛了两碗放上,每个碗里放三个饺子,又在每个碗里浇上些饺子汤,也过来做了揖。拿火柴把酒盅里的酒点上,酒盅里跳动着蓝色的火苗,飘起细细的青烟,一股似酒似醋的怪味飘了起来,人们下意识的用手在鼻子前扇几下。
秋智妈妈理了一下头发,用围裙擦了一下刚刚洗过、已经擦干的手,说:“灶王爷爷、灶王奶奶,这一年过去了,你们受累了,家里的饭都做得熟熟的。这要上天见玉帝了,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保佑我们这些孩子旺蹦旺跳的。让天下太平,有个好收成。多吃点,喝好了,也好动身。”
秋智开始憋着,实在憋不住了,刚刚要笑出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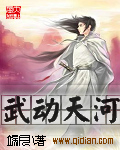

![[星河] 时空死结封面](http://www.34gc.net/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