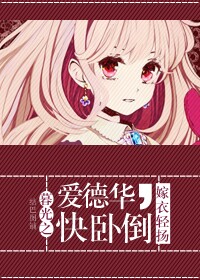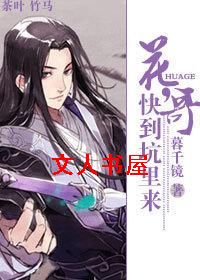思考,快与慢-第5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悔的行动存有偏见;我们虽然不能界定对玩忽职守和拿人钱财之间的区别,却也能够将两者区分开来;我们不会不停地做事,因为责任感总是因人而异的。奖励和惩罚带来的最终价值通常会使人有情绪反应,这是一种精神上的自我交易,而当个人成为某个机构的代理人时,就不可避免地会与该机构发生利益冲突。
你会卖掉赢利的股票还是亏损的股票?
理查德·泰勒多年来一直对会计行业与心理账户的类似之处很感兴趣。心理账户是我们用于组织和经营生活的账户,它有弊也有利,并且有多种来源。现实生活中,我们可能会将自己的钱存在不同的银行账户里,而有时我们仅仅是将钱存在了不同的心理账户中。我们有零用钱和普通存款,也有支付孩子教育费用或急诊的预留存款。该用哪些存款来满足现在的资金需求,我们有明确的先后顺序。就像为家庭开支作预算、限制每天喝黑咖啡的数量或是增加锻炼时间一样,存款也是为了自我控制。通常我们会为了自我控制而付出代价,例如,一面把钱存入储蓄账户,一面却透支信用卡。理性代理模式下的经济人并不依赖心理账户:他们对结果的看法是经过综合分析得来的,是受外部诱因驱使的。对于人类来说,心理账户是窄框架的一种形式;他们通过有限的大脑使所有事情都得到掌控,易于管理。
心理账户在记录得分上应用广泛。回想职业高尔夫球手在避免击出超过标准杆的球而不是小鸟球时,往往打得更出色。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优秀的高尔夫球手会为球场上的每个球洞都创立账户,他们不会将整体的成功押在唯一的账户上。泰勒在此前的一篇文章中阐述的一个颇具讽刺意义的例子就很好地说明了心理账户是怎样影响行为的:
两个狂热的球迷计划到离他们约64公里远的地方看篮球赛。其中一个人买了门票;另一个人在买票的途中遇见了一个朋友,免费得到了票。现在,有预报称比赛当晚会有暴风雪。这两位持票的球迷谁会更愿意冒着暴风雪去看比赛?
答案很明显,我们知道买了票的那个球迷更有可能会去。心理账户也为此提供了解释。假设两个球迷都为这场比赛开设了账户,而错过比赛就是在负差额(逆差)的情况下关闭了这两个账户。那么无论是怎样得到门票的,他们都会很失望。但是,关闭账户对于买票的那个人来说影响更为消极,因为现在他的钱没有了,还不能看比赛。对这个人而言,待在家里是个更糟糕的选择,所以他更愿意去看比赛,也就更可能会冒着暴风雪开车去看比赛。这是系统1自动对情绪平衡作出的内在分析。在标准的经济学理论中,人们由心理账户引发的情绪并没有得到普遍认可。经济人可能会意识到这张票已经付了钱,而且已经不能退换。票的成本已经“沉没”了,这位经济人不会再在意这张球赛门票是自己买的还是朋友赠的(如果该行为人有朋友的话)。想要实施这个理性行为,系统2应该会考虑反事实的(指在不同条件下有可能发生但违反现存事实的)可能性:“如果我的票是从朋友那儿得来的,我还会冒着暴风雪驾车吗?”但只有积极的、受过相关训练的大脑才会想到提出这样的难题。
当个人投资者将他们的证券投资组合中的一些股票卖掉时,犯一个错误也会使他们痛苦不堪:
你需要钱来操办女儿的婚礼,所以想卖掉一些股票。你记得自己每一只股票的买进价,也能分辨出某只股票是“赢利股”(即当前价值高于你的买进价的股票),或是亏损股。在你所有的股票中,蓝莓牌瓷砖是一只赢利股;如果你在今天将其售出,就会得到5000美元的收益。你持有蒂芙尼电机相同的股份,现值是5000美元,但低于你的买进价格。你更有可能出售哪一只股票?
作出这个选择的可行方法是:“我会关闭蓝莓牌瓷砖股票账户,记录下一笔成功的投资。或者,我可以关闭蒂芙尼电机股票账户并记下失败的一笔。我更愿意怎么做?”如果将这个问题看做是在给你带来的快乐和给你造成的痛苦中作选择,你肯定会卖掉蓝莓牌瓷砖,以享受成功投资的乐趣。可以预料,金融研究中已经记录了大量人们售出自己的赢利股、保留亏损股的偏好,这被视为一种偏见,关于此还有一个晦涩难懂的名字:处置效应。
处置效应是窄框架的一个例子。投资者为她买的每一只股票都开设了账户,并想在关闭每一个账户时都能获利。理性的代理人会对证券投资组合有一个整体的看法,会售出最无可能在未来赢利的股票,而不是去考虑它是赢利股还是亏损股。阿莫斯跟我说了他与一名财务顾问的谈话。这名顾问询问阿莫斯他的证券投资组合中所有股票的相关信息,包括每只股票的买入价格。当时阿莫斯温和地问:“难道这个问题很要紧吗?”这个顾问当时看起来非常吃惊,他显然一直认为心理账户的状态是值得考虑的因素。
阿莫斯对这个财务顾问的观念的猜测可能是对的,但他将买入价视为无关紧要的却是错误的。即使对经济人来说,买入价也很重要,应该将其考虑在内。处置效应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偏见,因为对于售出赢利股还是亏损股这个问题,答案很明确,但并不是说选择卖哪只股票都无关紧要。如果你在意的是自己的财富,而不是直观感受,就会售出蒂芙尼电机这只亏损股,保留蓝莓牌瓷砖这只赢利股。至少在美国,税收能给人很大的刺激:你会意识到,卖掉亏损股可以减免税赋,而卖掉赢利股就必须得纳税。全美国的投资者都知道这个金融方面的基本事实,这个事实还决定了他们所做的一个决策,投资者会在12月卖掉更多的亏损股,因为这个月的税赋一直令他们忧心忡忡。一年中每个月都有税收优惠,但是在其他11个月份中,心理账户在人们心中的分量都重于金融常识。另一个反对出售赢利股的论据是对市场反常现象的详细记录,即最近升值的股票有可能还会继续升值至少一小段时间。这个净效应很大:预计卖掉蒂芙尼股而非蓝莓股的税后额外回报率在第二年是3。4%。在赢利的情况下关闭心理账户会令人心情愉悦,但这种愉悦是你花钱买来的。一个经济人不会犯这样的错误,在这一点上,那些运用系统2的经验丰富的投资者比新手更容易犯这种错误。
理性的决策者只会对当前投资的未来结果感兴趣,经济人不会去考虑纠正先前的错误。当有更好的投资项目时,对亏损账户进行额外投资的决策被称为“沉没成本悖论”,这是一个代价高昂的错误决策,在大大小小的许多决策中都能看到其身影。由于买了门票而冒着暴风雪开车去看演出就是一种沉没成本悖论。
设想一家公司已经在某个项目中投入了5000万美元。现在,这个项目误了工期,其最终回报的预计收益也没有最初计划的那样好。如果想要实现这个项目的最初目标,则需要6000万美元的额外投资。另一个提议是将同样的资金投入到一个新的项目中,且这个项目似乎可以带来更高的回报。这家公司会怎么做呢?通常的情况是,像冒着暴风雪开车那样,受到沉没成本影响的公司会继续将钱砸在那个不好的项目上,因为关闭这个项目的账户就相当于承认自己的失败,这是一种耻辱。这个情景属于四重模式中右上角那一栏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在必然的损失和不利的风险中作出选择,这样做通常是不明智的。
从公司的角度来看,向失败的尝试增加投入是个错误做法,但对“拥有”这个前景并不明朗的项目的高管来说,却未必如此。撤销这个项目会给这个高管的履历上留下难以抹掉的污点,只能依靠该组织的资源再赌一把才能最大限度地保住个人利益,才有希望收回投资成本,至少可以尝试着延长清算日期。在沉没成本的状态下,高管的动机与公司的目标以及股东的利益都会不一致,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代理问题中常见的类型。董事会非常清楚这样的冲突,所以当某位执行总裁因受困于先前的决策影响而不愿避免再造成损失的话,董事会就会将其替换掉。董事会成员不见得认为新的执行总裁比原先的更有能力,但他们知道新的总裁不会有与原总裁一样的心理账户,在评估当前机会的选择时,他也就更容易忽视过去投资的沉没成本。
沉没成本悖论导致人们在不被看好的事情上浪费了太多时间,例如不幸福的婚姻、没有希望的研究项目等。我常注意到,一些年轻的科学家宁愿苦苦挣扎于注定会失败的项目,也不会选择放弃,重新开始。不过,好在有研究表明这样的悖论至少在某些情况下是可以克服的。在经济学和商贸学的课堂上,沉没成本悖论也被视为一种错误理论。这样做显然会产生积极影响,有证据表明,这些领域的毕业生比其他人更有可能放弃会失败的项目。
哪种选择会让你更后悔?
后悔是一种情绪,也是一种自我惩罚。人们做出的许多决策都是因为不想后悔(“不要这样做,否则你会后悔的”是个非常常见的警告),现实生活中我们也有很多后悔的事。有两位荷兰的心理学家对这种情绪状态作了很好的描述,他们注意到,后悔“总是与一个人本该更加了解的情感、不祥的预感以及对做错的事或失去的机会念念不忘等情绪形影相随,与严厉自责和改正错误的倾向形影相随,与‘此事如果没有发生该多好’或是‘如果再有一次机会该多好’之类的想法形影相随”。当你想象自己正在做某事而不是在想曾经做过的事情时,就会感到强烈的悔意。
后悔是由替代现实的可用性引发的反事实情绪。每架飞机失事后,都会有关于一些乘客“本不应该”在那架飞机上的特别报道,他们有的是在最后几秒才订到的位子,有的是从另一条航线转机过来的,还有的理应早飞一天,但不幸延迟了才上了这架飞机。这些令人痛苦的事例有个共同特点,即它们都属于反常规事件。与正常事件相比,人们更容易凭想象搞砸这些反常规事件。联想机制包含了正常世界的典型及其规则。反常规事件会吸引人的注意力,还会使人们认为在相同情况下这些事件也应该是正常的。
为了理解后悔与常态的关系,请思考下列情境:
布朗先生几乎从不让旅行者搭便车。昨天他让一个男人搭了便车,然后他被抢了。
史密斯先生经常让旅行者搭便车。昨天他让一个男人搭了便车,然后他被抢了。
这两个人谁更可能感到后悔?
答案不出我们所料:有88%的受试者认为布朗先生会更后悔,12%的受试者认为是史密斯先生。
后悔与责备并不是一回事。实验人员问了其他受试者与上述事件相关的一个问题:
谁会受到他人更严厉的责备?
结果是:认为是布朗先生的占23%,认为是史密斯先生的占77%。
与常态的对比可引起后悔和责备,但相关的常态是不相同的。布朗先生和史密斯先生体验到的情绪主要是由他们平时对待旅行者的方式决定的。让旅行者搭便车对于布朗先生来说是一件反常规事情,因此,大多数人认为他会更后悔。然而,带有批判性的观察者会将这两个人的行为与合理行为的传统常态相比较,更可能会批评史密斯先生,因为他总是习惯性地承担这种不可预知的风险。我们会忍不住说,史密斯先生是自食其果,布朗先生是走了霉运。但布朗先生更应被指责,因为他在这件事上的做法与他平时的性格不符。
决策制定者容易感到后悔,而痛苦的情绪则对很多的决策制定都有影响。后悔的直觉非常一致,而且还很明显,下面这个例子就说明了这一点。
保罗在A公司持有股份。在过去一年里,他想要将股份转移到B公司,但最终决定还是不那样做。现在,他了解到,如果他当时将股份转到了B公司的话,可以多赚1200美元。
乔治在B公司持有股份。在过去一年里,他将股份转移到了A公司。现在,他了解到,如果他当时坚持保留B公司股份的话,可以多赚1200美元。
谁会更后悔呢?
结果很明显:8%的受试者说是保罗,92%的受试者说是乔治。
这很令人好奇,因为从客观上来说,这两位投资者的情况是一样的。他们现在都拥有A股,而且如果拥有B股可多赚同样多的钱。唯一的区别在于,乔治没能赚更多钱是因为他采取了行动,而保罗则是因为没有采取行动。这个小事例说明了一个大道理:人们对由于不采取行动而导致的结果,会比因行动而产生的结果有更为强烈的情绪反应(包括后悔)。这个观点在赌博的情

![[来自星星的你]叫兽,快迎接你母星的小伙伴!封面](http://www.34gc.net/cover/18/1862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