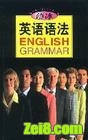国学知识大全-第6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耳。故曰:“良知之发,更无私意障碍,即所谓充其恻隐之心,而仁不可胜用。常人不能无私意,所以须用致知格物之功。”又曰:“知得善,却不依这个良知便做去。知得不善,却不依这个良知,便不去做。这个良知,便遮蔽了。”又曰:“天理即是良知。良知愈思愈精明。若不精思,漫然随事应去,良知便粗了。”然“学以去其昏蔽,于良知之本体,初不能有加于毫末”,此义亦不可不知。
知是知非之良知,不能致即将昏蔽,于何验之?曰:观于人之知而不行,即知之矣。盖良知之本体,原是即知即行。苟知之而不能行,则其知已非真知,即可知其为物欲所蔽矣。“徐爱问:今人尽有知父当孝、兄当弟,却不能孝、不能弟,知行分明是两件。曰:此已被人欲间断,不是知行本体。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圣贤教人知行,正是要复那本体。故大学指个真知行与人看:说如好好色,如恶恶臭。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只见好色时,已自好了;不是见后又立个心去好。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只闻恶臭时,已自恶了;不是闻后别立个心去恶。(龙溪曰:“孟子说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止曰知而已;知便能了,更不消说能爱能敬。”)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故曰:“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〇龙溪曰:“知非见解之谓,行非履蹈之谓,只从一念上取证。”)古人所以既说知,又说行者?只为世间有一种人,懵懵懂懂,任意去做;全不解思维省察;只是个冥行妄作;所以必说个知,方才行得是。又有一种人,茫茫荡荡,悬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实躬行;只是个揣摩影响;所以必说一个行,方才知得真。此是古人不得已补偏救弊的话。”“此已被私欲间断,不是知行本体”一语最精。好好色、恶恶臭之喻尤妙。“见好色时,已是好了,不是见后又立个心去好;闻恶臭时,已自恶了,不是闻后别立个心去恶。”人之所知,一切如此,岂有知而不行之理?见好色而强抑其好之之心,闻恶臭而故绝其恶之之念,非有他念不能然。此即所谓间断也。良知之有待于致,即欲去此等间断之念而已矣。
真知未有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故欲求真知,亦必须致力于行。此即所谓致也。故曰:“人若真切用功,则于此心天理之精微,日见一日;私欲之细微,亦日见一日。若不用克己功夫,天理私欲,终不自见。如走路一般。走得一段,方认得一段。走到歧路,有疑便问;问了又走,方才能到。今于已知之天理不肯存,已知之人欲不肯去;只管愁不能尽知;闲讲何益?”
知行既系一事,则不知自无以善其行。阳明曰:“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两件,故有一念发动,虽是不善,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人之为如何人,见于著而实积于微。知者行之微,行者知之著者耳。若于念虑之微,不加禁止,则恶念日积,虽欲矫强于临时,必不可得矣。大学曰:“小人闲居为不善。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正是此理。凡事欲仓促取办,未有能成者。非其事之不可成,乃其败坏之者已久也。然则凡能成事者,皆非取办于临时,乃其豫之者已久也。欲求豫,则必谨之于细微;欲谨之于细微,则行之微(即知)有不容不措意者矣。故非知无以善其行也。故曰:知行是一也。
知行合一之理,固确不可易。然常人习于二之之既久,骤闻是说,不能无疑。阳明则一一释之。其说皆极精当。今录其要者如下:
“徐爱问:善只求诸心,恐于天下事理,有不能尽。曰: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爱曰:如事父一事,其间温凉定省之类,有许多节目,亦须讲求否?曰:如何不讲求?只是有个头脑,只就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讲求。此心若无人欲,纯是天理,是个诚于孝亲之心:冬时自然思量父母寒,自去求温的道理;夏时自然思量父母热,自去求清的道理。譬之树木:这诚孝的心便是根;许多条件,便是枝叶。须先有根,然后有枝叶。不是先寻了枝叶,然后去种根。”阳明此说,即陆子所谓先立乎其大者也。“温清定省之类,有许多节目”,最为恒人所质疑。得此说而存之,而其疑可以豁然矣(阳明曰:“圣人无所不知,只是知个天理。无所不能,只是能个天理。天下事物,如名物度数、草木鸟兽之类,不胜其烦。虽是本体明了,亦何缘能尽知。但不必知的,圣人自不消求知。其所当知者,圣人自能问人。知得一个天理,便自有许多节文度数出来。”此说与朱子“生而知之者义理,礼乐名物,必待学而后知”之说,似亦无以异。然朱子谓人心之知,必待理无不穷而后尽。阳明则虽名物度数之类,有所不知,而仍不害其为圣人。此其所以为异也)。
枝叶条件,不但不必豫行讲求也,亦有无从豫行讲求者。阳明曰:“良知之于节目事变,犹规矩尺度之于方圆长短也。节目事变之不可豫定,犹方圆长短之不可胜穷也。舜之不告而取,岂舜之前,已有不告而取者,为之准则邪?抑亦求诸一念之良知,权轻重之宜,不得已而为此邪?武之不葬而兴师,岂武之前,已有不葬而兴师者,为之准则邪?抑亦求诸一念之良知,权轻重之宜不得已而为此邪?后之人不务致其良知,以精察义理于此心感应酬酢之间,顾欲悬空讨论此等变常之事,执之以为制事之本,其亦远矣。”悬空讨论变常之事愈详,则致其良知之功愈荒。致其良知之功愈荒,则感应酬酢之间,愈不能精察义理。以此而求措施之悉当,是却行而求及前人也。故曰:“在物为理,处物为义,在性为善,因所指而异其名,其实皆吾之心也。吾心之处事物,纯乎天理,而无人欲之杂,谓之善。非在事物上有定则可求也。”(又曰:“良知自然的条理,便谓之义;顺这个条理,便谓之礼。知这个条理,便谓之智。终始这个条理,便谓之信。”)
第70章 理学纲要(22)()
学所以求是也。以良知为准则,以其知是知非也。今有二人于此,各准其良知,以断一事之是非,不能同也。而况于多人乎?抑且不必异人,即吾一人之身,昨非今是之事,亦不少也。良知之知是知非,果足恃乎?阳明曰:“凡处得有善有未善,及有困顿失次之患,皆是牵于毁誉得丧,不能实致其良知耳。实致其良知,然后知平日所谓善者,未必得善。”或谓心所安处是良知。阳明曰:“固然。但要省察,恐有非所安而安者。”又谓“人或意见不同,还是良知有纤翳潜伏”。此说与伊川“公则一,私则万殊。人心不同如面,只是私心”之说,若合符节。盖良知虽能知是知非,然恒人之良知,为私欲蒙蔽已久,非大加省察,固未易灼见是非之真也。
然则现在之良知,遂不足为准则乎?是又不然。恒人之良知,固未能造于其极,然亦皆足为随时之用。如行路然。登峰造极之境,固必登峰造极而后知。然随时所见,固亦足以定随时之程途也。故曰:“我辈致知,只是各随分量所及。今日良知见在如此,便随今日所知,扩充到底。明日良知又有开悟,便随明日所知,扩充到底。”故曰:“昨以为是,今以为非;己以为是,因人而觉其非,皆良知自然如此。”有言童子不能格物,只教以洒扫应对。曰:“洒扫应对就是物。童子良知,只到这里,教去洒扫应对,便是致他这一点良知。我这里格物,自童子以至圣人,皆是此等工夫。”真可谓简易直截矣。
致知既以心为主,则必使此心无纤毫障翳而后可。随时知是知非,随时为善去恶,皆是零碎工夫,如何合得上本体?此则贤知者之所疑也。阳明亦有以释之。传习录:“问:先生格致之说,随时格物以致其知,则知是一节之知,非全体之知也,何以到得溥博如天、渊泉如渊地位?曰:心之本体,无所不该,原是一个天。只为私欲障蔽,则天之本体失了。心之理无穷尽,原是一个渊。只为私欲窒塞,则渊之本体失了。如念念致良知,将此障蔽、窒塞,一齐去尽,则本体已复,便是天渊了。因指天以示之曰:如面前所见,是昭昭之天。四外所见,亦只是昭昭之天。只为许多墙壁遮蔽,不见天之全体。若撤去墙壁,总是一个天矣。于此便见一节之知,即全体之知;全体之知,只一节之知;总是一个本体。”盖零碎工夫,皆系用在本体上。零碎工夫,多用得一分,即本体之障蔽,多去得一分。及其去之净尽,即达到如天如渊地位矣。此致良知之工夫,所以可在事上磨炼也。
以上皆阳明所以释致良知之疑者。统观其说,精微简捷,可谓兼而有之矣。梨渊曰:“先生闵宋儒之后,学者以知识为知。谓人心之所有者,不过明觉,而理为天地万物之所公共;必穷尽天地万物之理,然后吾心之明觉,与之浑合而无间。说是无内外,其实全靠外来闻见,以填补其灵明。先生以圣人之学,心学也;心即理也。故于格物致知之训,不得不言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以知识为知,则轻浮而不实,故必以力行为工夫。良知感应神速,无有等待;本心之明即知,不欺本心之明即行也,不得不言知行合一。”龙溪曰:“文公分致知格物为先知,诚意正心为后行,故有游骑无归之虑;必须敬以成始,涵养本原,始于身心有所关涉。若知物生于意,格物正是诚意工夫,诚即是敬,一了百了,不待合之于敬,而后为全经也。”蕺山曰:“朱子谓必于天下事物之理,件件格过,以几一旦豁然贯通。故一面有存心,一面有致知之说。非存心无以致知,而存心又不可以不致知。两事递相君臣,迄无把柄,既已失之支离矣。至于存心之中,分为两条:曰静而存养,动而省察。致知之中,又复分为两途:曰生而知之者义理,礼乐名物,必待学而后有以验其是非之实。安往而不支离也?”此朱学与王学之异也。
良知之说,以一念之灵明为主。凡人种种皆可掩饰,惟此一念之灵明,决难自欺。故阳明之学,进德极其勇猛,勘察极其深切。阳明尝谓“志立而学半”。又谓“良知上留得些子别念卦带,便非必为圣人之志”。又曰:“凡一毫私欲之萌,只责此志不立,则私欲即退听。一毫客气之动,只责此志不立,则客气便消除。责志之功,其于去人欲,有如烈火之燎毛,太阳一出,而罔两潜消也。”此等勇猛精进之说,前此儒者,亦非无之。然无致良知之说,以会其归,则其勘察,终不如阳明之真凑单微,鞭辟入里;而其克治,亦终不如阳明之单刀直入,凌厉无前也。阳明之自道曰:“赖天之灵,偶有悟于良知之学,然后悔其向之所为者,固包藏祸机,作伪于外,而心劳日拙者也。十余年来,虽痛自洗剔创艾,而病根深痼,萌蘖时生。所幸良知在我,操得其要,譬犹舟之得舵,虽惊风巨浪,颠沛不已,犹得免于倾覆者也。”寄邹谦之书包藏祸机,谁则能免?苟非以良知为舵,亦何以自支于惊风巨浪之中乎?良知诚立身之大柄哉?
“心即理”一语,实为王学骊珠。惟其谓心即理,故节文度数,皆出于心;不待外求,心本明即知无不尽。亦惟其谓心即理,故是非善恶,皆验诸心;隐微之地有亏,虽有惊天动地之功,犹不免于不仁之归也。阳明曰:“世人分心与理为二,便有许多病痛。如攘夷狄、尊周室,都是一个私心,便不当理。人却说他做得当理,只心有未纯。往往慕悦其所为,要来外面做得好看,却与心全不相干。分心与理为二,其流至于霸道之伪而不自知。故我说个心即理。要使知心理是一个,便来心上做工夫,不去袭取于义,便是王道之真。”阳明此说,即董子“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之真诠。持功利之说者,往往谓无功无利,要道义何用?又安得谓之道义?殊不知功利当合多方面观之,亦当历长时间而后定。持功利之说者之所谓功利,皆一时之功利,适足贻将来以祸患。自持道义之说者观之,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