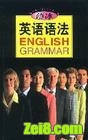国学知识大全-第6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度,运用作为,魄则不能。故人之死也,风火先散,则不能为祟。皆据旧说推度而已矣。
朱子论性,亦宗程子“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之说。其所以谓论性不论气不备者?盖以确见人及禽兽,其不善,确有由于形体而无可如何者也。语类曰:“论万物之一源,则理同而气异。睹万物之异体,则气犹相近,而理绝不同(谓万物已禀之而为性之理也)。气相近,如知寒暖,识饥饱,好生恶死,趋利避害,人与物都一般。理不同,如蜂蚁之君臣,只是他义上有一点子明;虎狼之父子,只是他仁上有一点子明;其他更推不去。大凡物事禀得一边重,便占了其他的。如慈爱的人少断制,断制之人多残忍。盖仁多便遮了那义,义多便遮了那仁。”(案此即无恶、只有过不及之说)又曰:“惟其所受之气,只有许多,故其理亦只有许多。如犬马,他这形气如此,故只会得如此事。”此犹今之主心理根于生理者,谓精神现象,皆形体之作用也。惟其然也,故朱子谓人确有生而不善者,欲改之极难。语类曰:“今有一样人,虽无事在这里坐,他心里也只思量要做不好事。如蛇虺相似,只欲咬人。他有什么发得善?”又曰:“如日月之光,在露地则尽见之。若在蔀屋之下,有所蔽塞,则有见有不见。在人则蔽塞有可通之理。至于禽兽,则被形体所拘,生得蔽隔之甚,无可通处。”朱子之见解如此,故曰:“人之为学,却是要变化气质,然极难变化”也。此等处,朱子以为皆从气质上来。盖朱子以全不着形迹者为理,而谓性即理,则性自无可指为不善。语类曰:“气之精英者为神。金木水火土非神,所以为金木水火土者是神。在人则为理,所以为仁义礼智信者是也。”又曰:“人生而静以上,即是人物未生时。人物未生时,只可谓之理,说性未得,此所谓在天为命也。才谓之性,便是人生以后,此理已堕在形气之中,不全是性之本体矣。”夫如是,则所谓性者,全与实际相离,只是一可以为善之物,又安得谓之不善。故朱子将一切不善,悉归之于气也。气何以有不善?朱子则本其宇宙观而为言曰:“人所禀之气,虽皆是天地之正气,然滚来滚去,便有昏明厚薄之异。”又曰:“天地之运,万端而无穷。日月清明,气候和正之时,人禀此气,则为清明浑厚之气,须做个好人。若是日月昏暗,寒暑反常,皆是天地之戾气。人若禀此气,则为不好的人。”此朱子谓气不尽善之由也。“性无气质,却无安顿处。”自朱子观之,既落形气之中,无纯粹至善者。(“或问:气清的人,自无物欲。曰:也如此说不得。口之欲味,耳之欲声,人人皆然。虽是禀得气清,才不检束,便流于欲去”)若不兼论形气,则将误以人所禀之性为纯善,而昧于其实在情形矣。此所谓论性不论气不备也。
其谓论气不论性不明者?则以天下虽极恶之人,不能谓其纯恶而无善。抑且所谓恶者本非恶,特善之发而不得其当者耳。朱子论“恶亦不可不谓之性”,曰:“他源头处都是善,因气偏,这性便偏了。然此处亦是性。如人浑身都是恻隐而无羞恶,都羞恶而无恻隐,这个便是恶德。这个唤作性邪?不是?如墨子之性,本是恻隐。孟子推其弊,到得无父处。这个便是恶亦不可不谓之性也。”然则论气不论性,不但不知恶人之善处,并其恶性质,亦无由而明矣。夫犹是善性也,所以或发而得其当,或发而不得其当者,形质实为之累,此所谓论性不论气不备。然虽发不得当,而犹是可以发其当之物,则可见性无二性,理无二理。故语类譬诸隙中之日,谓“隙之大小长短不同,然其所受,却只是此日”;又谓“蔽锢少者,发出来天理胜;蔽锢多者,发出来私欲胜;便见本源之理,无有不善”也。此而不知其同出一源,则于性之由来,有所误会矣。此所谓论气不论性不明也。
善恶既同是一性;所谓恶者,特因受形气之累而然。夫形气之累,乃后起之事;吾侪所见,虽皆既落形气之性,然性即是理,不能谓理必附于形质。犹水然,置诸欹斜之器,则其形亦欹斜,不能因吾济只见欹斜之器,遂谓水之形亦欹斜也。故世虽无纯善之性,而论性则不得不谓之善也。
性既本善,而形气之累,特后起之事,则善为本质,而不善实非必然。故曰:“人生都是天理。人欲却是后来没把鼻生底。”此说实与释氏真如无明之说,消息相通(朱子所谓善者,不外本性全不受形气之累。本性全不受形气之累而发出,则所谓天理。而不然者则所谓人欲也。所谓天理者,乃凡事适得其当之谓,此即周子之所谓中。朱子曰:“有个天理,便有个人欲。盖缘这天理须有个安顿处,才安顿得不恰好,便有人欲出来。”安顿得恰好,即周子所谓中;守此中而勿失,则周子所谓静也。故朱子之学,实与周子一脉相承者也。〇安顿得恰好者,朱子曰:“饮食,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设喻最妙)。
第63章 理学纲要(15)()
朱子论性之说如此。盖其所谓善者,标准极高,非全离乎形气,不足以当之,故其说如此。因其所谓善者,标准极高,故于论性而涉及朱子之所谓气者,无不加以驳斥;而于程、张气质之说,程子性即理之言,极称其有功于圣门,有补于后学。盖论性一涉于气质,即不免杂以人欲之私,不克与朱子之所谓善者相副;而朱子之所谓性者,实际初无其物,非兼以气质立论,将不能自圆其说也(朱子评古来论性者之说:谓“孟子恐人谓性元来不相似,遂于气质内挑出天之所命者,说性无有不善。不曾说下面气质,故费分疏。荀子只见得不好底。扬子又见得半上半下底。韩子所言,却是说得稍近,惜其少一气字,性那里有三品来?”“以气质论,则凡言性不同者,皆冰释矣。”“气质之说,起于张、程,极有功于圣门,有补于后学。”又谓“程先生论性,只云性即理也,岂不是见得明?真有功于圣门。”〇朱子之坚持性即理,而力辟混气质于性,亦由其欲辟佛而然。故曰:“大抵诸儒说性,多说着气。如佛氏,亦只是认知觉作用为性。”知觉作用,固朱子所谓因形气而有者也)。
人之一生,兼备理气二者,其兼备之者实为心。故朱子深有取于横渠“心统性情”之说,以为颠扑不破。又详言之曰:“性者,心之理。情者,性之动。心,性情之主。”又譬之曰:“心如水,性犹水之静,情则水之流,欲则水之波澜。”(又曰:“心如水,情是动处,爱即流向去处。”又以“心为大极,心之动静为阴阳”)孟子所善四端,朱子谓之情,曰:“性不可言,所以言性善者,只看恻隐辞逊四端,如见水流之清,则知源头必清矣。”心兼动静言,则动静皆宜致养。故朱子曰:“动静皆主宰,非静时无所用,至动时方有主宰。”又谓:“惟动时能顺理,则无事时能静。静时能存,则动时得力。须是动时也做工夫,静时也做工夫也。”
朱子论道德,亦以仁为最大之德,静为求仁之方。其仁说:谓“仁者仁之本体。礼者仁之节文。义者仁之断制。知者仁之分别。信以见仁义礼智,实有此理。必先有仁,然后有义礼智信。故以先后言之,则仁为先;以大小言之,则仁为大。”又谓“明道圣人以其情顺万物而无情,说得最好”。(语类曰:“动时静便在这里。顺理而应,则虽动亦静;不顺理而应,则虽块然不交于物,亦不能得静。”顺理而应,即所谓以其情顺万物而无情也)至于实行之方,则亦取伊川“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二语。而于用敬,则提出“求放心”三字;于致和,则详言格物之功。实较伊川言之,尤为亲切也。
中庸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龟山门下,以“体认大本”,为相传指诀。谓执而勿失,自有中节之和。朱子以为少偏。谓“才偏便做病。道理自有动时,自有静时。学者只是敬以直内,义以方外,见得世间无处不是道理。不可专要去静处求。所以伊川谓只用敬,不用静,便说平也。”又云:“周先生只说一者无欲也,这话头高,卒急难凑泊。寻常人如何便得无欲?故伊川只说个敬字,教人只就这敬字上挨去。庶几执捉得定,有个下手处。要之,皆只要人于此心上见得分明,自然有得尔。然今之言敬者,乃皆装点外事,不知直截于心上求功。遂觉累坠不快活。不若眼下于求放心处有功,则尤得力也。”此朱子主敬之旨也(又曰:“敬有死敬,有活敬,若只守着主一之敬,遇事不济之以义,而不活。熟后敬便有义,义便有敬。静则察其敬与不敬,动则察其义与不义。敬义夹持,循环无端,则内外透彻”)。
其论致知,则尽于大学补传数语。其言曰:“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数语,谓理不在心而在物,最为言阳明之学者所诋訾。然平心论之,实未尝非各明一义。至于致知力行,朱子初未尝偏废。谓朱子重知而轻行,尤诬诋之辞也。今摘录语类中论知行之语如下:
语类曰:“动静无端,亦无截然为动为静之理。且如涵养致知,亦何所始?谓学莫先于致知,是知在先。”又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则敬亦在先。从此推去,只管恁地。”是朱子初未尝谓知在先、行在后也。又曰:“自家若得知是人欲蔽了,便是明处。只这上,便紧紧着力主定。一面格物。”是朱子实谓力行致知,当同时并进也。又曰:“而今看道理不见,不是不知,只是为物塞了。而今粗法,须是打叠了胸中许多恶杂,方可。”则并谓治心在致知之前矣。又曰:“方其知之而未及行之,则知尚浅。既亲历其域,则知之益明,非前日之意味。”则知必有待于行,几与阳明之言,如出一口矣。又朱子所谓格物致知,乃大学之功,其下尚有小学一段工夫。论朱子之说者,亦不可不知。朱子答吴晦叔曰:“夫泛论知行之理,而就一事以观之,则知之为先,行之为后,无可疑者。然合夫知之浅深、行之大小而言,则非有以先成乎其小,亦将何以驯致乎其大者哉?盖古人之教:自其孩幼,而教之以孝悌诚敬之实;及其少长,而传之以诗书礼乐之文;皆所以使之即夫一事一物之间,各有以知其义理之所在,而致涵养践履之功也。及其十五成童,学于大学,则其洒扫应对之间,礼乐射御之际,所以涵养践履之者,略已小成矣。于是不离乎此,而教之以格物以致其知焉。致知云者,因其所已知者,推而致之;以及其所未知者,而极其至也。今就其一事之中而论之,则先知后行,固各有其序矣。诚欲因夫小学之成,以进乎大学之始,则非涵养践履之有素,亦岂能以其杂乱纷纠之心,而格物以致其知哉?故大学之书,虽以格物致知,为用力之始,然非谓初不涵养践履,而直从事于此也;又非谓物未格、知未至,则意可以不诚,心可以不正,身可以不修,家可以不齐也。若曰:必俟知至而后可行,则夫事亲从兄,承上接下,乃人生所一日不能废者,岂可谓吾知未至,而暂辍以俟其至而后行之哉?”读此书,而朱子于知行二者,无所轻重先后,可以晓然矣。
偏重于知之说,朱子亦非无之。如曰:“讲得道理明时,自是事亲不得不孝,事兄不得不弟,交朋友不得不信。”论前人以黑白豆澄治思虑(起一善念,则投一白豆于器中。起一恶念,则投一黑豆于器中)曰:“此则是个死法。若更加以读书穷理底工夫,则去那般不正底思虑,何难之有?”皆以为知即能行。(惟此所谓知者,亦非全离于行。必且力行,且体验,乃能知之)盖讲学者,大抵系对一时人说话。阳明之时,理学既已大行。不患此理之不明,惟患知之而不能有之于己,故阳明救以知行合一之说。若朱子之时,则理学尚未大行,知而不行之弊未著,惟以人之不知为患,故朱子稍侧重于知。此固时代之异,不足为朱子讳,更不容为朱子咎。朱子、王子,未必不易地皆然也。读前所引朱子论知行之说,正可见大贤立言之四平八稳,不肯有所偏重耳(在今日观之,或以为不免偏重。然在当日,则已力求平稳矣。必先尚论其世,乃可尚论其人。凡读先贤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