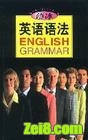国学知识大全-第3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最高,出乎本能以外之行动最多,故名母猴曰“为”。其后遂以为人之非本能之动作之称。故“为”字之本义,实指有意之行动言;既不该本能之动作,亦不涵伪饰之意也。古用字但主声,“为”“伪”初无区别。其后名母猴曰“为”之语亡,“为”为母猴之义亦隐,乃以“为”为“作为”之“为”,“伪”为“伪饰”之“伪”。此自用字后起之分别,及字义之迁变。若就六书之例言之,则既有“伪”字之后,“作为”之“为”,皆当作“伪”;其仍作“为”者,乃省形存声之例耳)荀子谓“人性恶,其善者伪”,乃谓人之性,不能生而自善,而必有待于修为耳。故其言曰:“途之人可以为禹则然,途之人之能为禹,则未必然也。”譬之足,可以遍行天下,然而未有能遍行天下者。夫孟子谓性善,亦不过谓途之人可以为禹耳。其谓“生于人之情性者,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后生;感而不能然,必待事而后然者谓之伪”,则孟子亦未尝谓此等修为之功,可以不事也。后人误解伪字,因以诋諆荀子,误矣。
荀子之言治,第一义在于明分。王制篇曰:“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胜,平声。物,事也)“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离则弱,弱则不能胜物。”“君者,善群也。群道当,则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富国篇曰:“天下害生纵欲。欲恶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矣。故百技所成,所以养一人也。而能不能兼技,人不能兼官;离居不相待则穷,群而无分则争。穷者患也,争者祸也。救患除祸,则莫若明分使群矣。”又曰:“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礼节用之。”“量地而立国,计利而畜民,度人力而授事。使民必胜事,事必出利,利足以生民。皆使衣食百用,出入相掩,必时臧余,谓之称数。”夫总计一群之所需,而部分其人以从事焉,因以定人之分职,大同小康之世,皆不能不以此为务,然而有异焉者:大同之世,荡荡平平,绝无阶级,人不见有侈于己者,则欲不萌,人非以威压故而不敢逾分,则其所谓分者,不待有人焉以守之而自固。此大同之世,所以无待于有礼。至于小康之世,则阶级既萌,劳逸侈俭,皆不平等。人孰不好逸而恶劳?孰不喜奢而厌俭?则非制一礼焉,以为率由之轨范,而强人以守之不可。虽率循有礼,亦可以致小康,而已落第二义矣。此孔子所以亟称六君子之谨于礼,而终以为不若大道之行也。荀子所明,似偏于小康一派,故视隆礼为极则,虽足矫乱世之弊,究有惭于大同之治矣。
大同之世,公利与私利同符,故其趋事赴功,无待于教督。至小康之世,则不能然,故荀子最重人治。天论篇曰:“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循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寒暑不能使之疾,妖怪不能使之凶。”“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舍其所以参,而愿其所参,则惑矣。”其言虽不免有矜厉之气,要足以愧末世之般乐怠敖者也。
荀子专隆礼,故主张等级之治。其言曰:“夫贵为天子,富有天下,是人情之所同欲也。然则从人之欲,则势不能容,物不能赡也。故先王案为之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是夫群居和一之道也。故仁人在上,则农以力尽田,贾以察尽财,百工以巧尽械器。士大夫以上至于公侯,莫不以仁厚知能尽官职,夫是之谓至平。故或禄以天下而不自以为多,或监门御旅,抱关击柝,而不自以为寡。故曰:斩而齐,枉而顺,不同而一。夫是之谓人伦。”(荣辱)其言似善矣。然岂知大同之世,“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则虽出入鞅掌,而亦不自以为多;虽偃仰笑敖,而亦不自以为寡。既无人我之界,安有功罪可论?又安有计劳力之多寡,以论报酬之丰啬者邪?
第40章 先秦学术概论(12)()
隆礼则治制必求明备,故主法后王。所谓后王,盖指三代。书中亦屡言法先王,盖对当时言之则称先王,对五帝言之则称后王也。非相篇曰:“欲观圣王之迹,则于其粲然者矣,后王是也。”“五帝之外无传人,非无贤人也,久故也。五帝之中无传政,非无善政也,久故也。禹、汤有传政,而不若周之察也,非无善政也,久故也。传者久则论略,近则论详。(韩诗外传“论”作“愈”)略则举大,详则举小。”此其法后王之故也。有谓古今异情,治乱异道者,荀子斥为妄人。驳其说曰:“欲观千岁,则数今日。欲知亿万,则审一二。欲知上世,则审周道。”此似于穷变通久之义,有所未备者。殊与春秋通三统之义不合。故知荀子之论,每失之狭隘也。
其狭隘酷烈最甚者,则为非象刑之论。其说见于正论篇。其言曰:“世俗之为说者曰:治古无肉刑而有象刑。是不然。以为治邪?则人固莫敢触罪,非独不用肉刑,亦不用象刑矣。以为轻刑邪?人或触罪矣,而直轻其刑,然则是杀人者不死,伤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轻,庸人不知恶矣。乱莫大焉。凡刑人之本,禁暴恶恶,且征其未也。杀人者不死,而伤人者不刑,是谓惠暴而宽贼也,非恶恶也。故象刑殆非生于治古,并起于乱今也。治古不然。凡爵列官职,赏庆刑罚皆报也,以类相从者也。一物失称,乱之端也。”“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未有知其所由来者也。刑称罪则治,不称罪则乱。故治则刑重,乱则刑轻。犯治之罪固重,犯乱之罪固轻也。书曰:刑罚世轻世重。此之谓也。”案尚书大传言:“唐虞上刑赭衣不纯,中刑杂屦,下刑墨幪。”此即汉文帝十三年除肉刑之诏,所谓“有虞氏之时,画衣冠异章服以为戮,而民弗犯”者,乃今文书说也。古代社会,组织安和,风气诚朴,人莫触罪,自是事实。今之治社会学者,类能言之。赭衣塞路,囹圄不能容,乃社会之病态。刑罚随社会之病态而起,而繁,乃显然之事实,古人亦类能言之,何莫知其所由来之有?荀子所说,全是末世之事,乃转自托于书说,以攻书说,谬矣。此节汉书刑法志引之。汉世社会,贫富不平,豪桀犯法,狱讼滋多。惩其弊者,乃欲以峻法严刑,裁抑一切。此自救时之论,有激而云。若谓先秦儒家,有此等议论,则似远于情实矣。予疑荀子书有汉人依托处,实由此悟入也。
荀子书中,论道及心法之语最精。此实亦法家通常之论。盖法家无不与道通也,管子书中,正多足与荀子媲美者。特以荀子号称儒书;而其所引道经,又适为作伪古文尚书者所取资,故遂为宋儒理学之原耳。然荀子此论,实亦精绝。今摘其要者如下:天论篇曰:“天职既立,天功既成,形具而神生。好恶喜怒哀乐臧焉,夫是之谓天情。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谓天官。心居中虚,以治五官,夫是之谓天君。财非其类以养其类,夫是之谓天养。顺其类者谓之福,逆其类者谓之祸,夫是之谓天政。”“圣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备其天养,顺其天政,养其天情,以全其天功。如是,则知其所为,知其所不为矣,则天地官而万物役矣。”此从一心推之至于至极之处,与中庸之“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同理。道家亦常有此论。此儒道二家相通处也。解蔽篇曰:“故治之要,在于知道。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虚壹而静。”“虚壹而静,谓之大清明。万物莫形而不见,莫见而不伦,莫伦而失位。”“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无所受令。自禁也,自使也,自夺也,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故口可劫而使墨云,形可劫而使诎申,心不可劫而使易意,是之则受,非之则辞。故曰:心容,其择也无禁,必自见。其物也杂博,其情之至也不贰。类不可两也,故知者择一而壹焉。农夫精于田而不可以为田师。贾精于市,而不可以为市师。工精于器而不可以为器师。有人也,不能此三技而可使治三官,曰:精于道者也故君子壹于道而以赞稽物。”“故道经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几,惟明君子而后能知之。故人心譬如架水,正错而勿动,则湛浊在下,而清明在上,则足以见须眉而察理矣。微风过之,湛浊动乎下,清明乱于上,则不可以得大形之正也。”此篇所言治心之法,理确甚精。宋儒之所发挥,举不外此也。然此为荀子书中极至之语。至其通常之论,则不贵去欲,但求可节(见正名篇),仍礼家之论也。
第八章法家
法家之学,汉志云:“出于理官”,此其理至易见。汉志所著录者有李子三十二篇,商君二十九篇,申子六篇,处子九篇,慎子四十二篇,韩子五十五篇,游棣子一篇。今惟韩子具存。商君书有阙佚。慎子阙佚尤甚。管子书,汉志隶道家,然足考见法家言处甚多。大抵原本道德,管子最精;按切事情,韩非尤胜。商君书精义较少。欲考法家之学,当重管韩两书已。
法家为九流之一,然史记以老子与韩非同传,则法家与道家,关系极密也。名、法二字,古每连称,则法家与名家,关系亦极密也。盖古称兼该万事之原理曰道,道之见于一事一物者曰理,事物之为人所知者曰形,人之所以称之之辞曰名。以言论思想言之,名实相符则是,不相符则非。就事实言之,名实相应则治,不相应则乱,就世人之言论思想,察其名实是否相符,是为名家之学。持是术也,用诸政治,以综核名实,则为法家之学。此名、法二家所由相通也(世每称刑名之学。刑实当作形。观尹文子大道篇可知。尹文子未必古书,观其词气,似南北朝人所为。然其人实深通名法之学。其书文辞不古,而其说则有所本也),法因名立,名出于形,形原于理(万事万物之成立,必不能与其成立之原理相背),理一于道(众小原则,统于一大原则),故名法之学,仍不能与道相背也。(韩非有解老喻老二篇,最足见二家之相通)
韩非子扬榷篇,中多四言韵语,盖法家相传诵习之辞。于道德名法一贯之理,发挥最为透切。今试摘释数语如下:扬榷篇曰:“道者弘大而无形,德者核理而普至,至于群生,斟酌用之。”此所谓道,为大自然之名。万物之成,各得此大自然之一部分,则所谓德也。物之既成,必有其形。人之所以知物者,恃此形耳。形万殊也,则必各为之名。名因形立,则必与形合,而后其名不囗。故曰“名正物定,名倚物徒”也。名之立虽因形,然及其既立,则又别为一物,虽不知其形者,亦可以知其名。(如未尝睹汽车者,亦可知汽车之名)然知其名而不知其形(即不知其名之实),则终不为真知。(一切因名而误之事视此。人孰不知仁义之为贵,然往往执不仁之事为仁,不义之事为义者,即由其知仁义之名,而未知仁义之实也)故曰“不知其名,复修其形”也。名因形立,而既立之后,又与形为二物,则因其形固可以求其名,因其名亦可以责其形。(如向所未见之物,执其名,亦可赴市求之)故曰:“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吾操是名以责人,使效其形;人之效其形者,皆与吾所操之名相合,则名实相符而事治;否则名实不符而事乱矣。故曰“形名参同,上下和调”也。臣之所执者一事,则其所效者一形耳。而君则兼操众事之名,以责群臣之各效其形,是臣犹之万物,而君犹之兼该万物之大自然。兼该万物之大自然,岂得自同于一物?故曰“道不同于万物,德不同于阴阳,衡不同于轻重,绳不同于出入,和不同于燥湿,君不同于群臣”也。然则人君之所操者名,其所守者道也。故曰:“明君贵独道之容。”抑君之所守者道,而欲有所操,以责人使效其形,则非名固末由矣。故曰“用一之道,以名为首”也。万物各有所当效之形,犹之欲成一物者,必有其模范。法之本训,为规矩绳尺之类(见管子七法篇。礼记少仪:“工依于法。”注:“法,谓规矩绳尺之类也。”周官掌次:“掌王次之法。”注:“法,大小丈尺。”),实即模范之义。万物所当效之形,即法也。此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