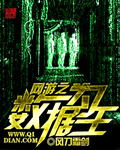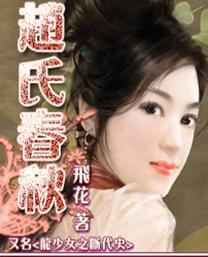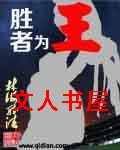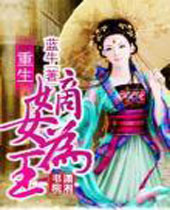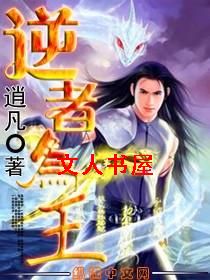赵氏为王-第4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后,做牛做马,来报答你的活命之恩。”
司马喜面色微动,沉吟许久缓缓说道;“是呀,一转眼都二十一年了。那年我才二十四岁,满腔抱负的来到中山国想要一展所长,如今却已经快到知天命的年龄了。”
孟石苦涩一笑,道;“谁说不是呢,主上你和我一样,都已经老了,不服不行。这二十一年来我从未对您的交代我的事情问过一句‘为什么’,也从未怀疑过你做的任何决定,但凡你吩咐的,我都尽力去做到最好,从来不问原因。因为我这条命是你给的,而且主上你这么聪明,所想所行的事情自然是有道理的事情,所以我也不需要去多想,只要老老实实的去做。”
“可如今我真的看不懂了,主上,你究竟是怎么想的,难道就没考虑过自己的后路吗?所有的人都看出来主上您再这样下去只有死路一条,难道你就没想过这些吗?所以我才忍不住想问你,因为我真的很担心你退无可退,最后落得个惨淡下场。”
第六十四章 中山狼(二)
PS:更正一下,中山的王姓是姬,而不是之前我以为的易。中山国的开国君王文公自诩黄帝后裔,以周室的姬姓为姓,故而后世皆以姬为姓,此时为中山六世王姬尚。
“那依你之见我当如何?”
孟石咬了咬牙,说道;“依小人的遇见,中山能保则报,不能保不如以城降赵。我听说赵主父那人心胸宽广,是人中之龙,主上如果降他,便不用担心自己的安危了,虽未必能得以重用,但性命可以保全,最不济做个富家翁。”
司马喜微微吃惊,有些诧异的望着孟石道;“你可是白狄族人,却劝我投降赵国?”
“小人不知什么白狄,只知道效忠主上。主上能立于中山小人自当以中山为国,如若不能,我也随你叛出中山!”
司马喜心中一阵感动,却不知如何说出。便不再言语,只是紧紧的看着孟石的脸,许久才问道;“孟石,你可信任我?”
孟石深深的低下了头,谦声道;“主上,小人的命是你给的,别说信任您,就算你需要我命的话也可以随时拿去。”
“好,既然如此那请你就不要再问我原因了,我做事自然有我的打算,你无须担心,如此可好?“
孟石见司马喜一脸的言之凿凿,心中虽然还是不知道司马喜的打算是何,但无奈之下也只好点头答应。
“夜色深了,主上你还是早些休息吧,要是耽误了明天的早朝,就罪过大了。”
“恩,好,那你先退下吧。”
“诺!”
……
第二日早朝,中山国的文武百官仍然像往常一样整装来朝,一个爆炸性的消息却在朝会上得到了证实,之前传的沸沸扬扬的中山军大败原来是真的,朝堂上顿时议论纷纷。
惟独司马喜却是面色如常,丝毫不见慌乱,这个消息他早在所有人之前就已经得知。如今在中山,身为相邦的他权倾朝野,深得姬尚的宠信,凡是奏请中山王的,都是先经他过目再决定送不送予姬尚一阅。就连军情也不意外,昨晚他已经得到了前线军报,却将消息压下了一晚,直到第二日早上才奏与中山王。
在得知石邑和缟城两城降于赵人后,姬尚先是暴跳如雷,在朝堂上当着众大臣的面破口大骂了起来,下令举国四处搜查这两名叛徒的族人。旋即又深深的害怕了起来,心想二城一失,中山国的南面就无险可守。
姬尚眼巴巴的看着台下的诸多臣子,面带慌乱之色大声问道:“如今赵军大军压境,诸位爱卿可有什么好的办法化解此次危机,但说无防。寡人洗耳恭听。”
“大王无须慌张。”一名须发尽白的老年人大步出列,一身白色的儒袍在身显得格外的引人注目。
那人却浑然不觉,仍然自信满满的自顾说道;“臣敢担保,赵军必将入从前一样无功而返。”
“哦?”姬尚面色露出兴奋之色,连忙问道;“文大夫为何如此肯定?”
那文大夫哈哈一笑,迎着众人的目光说道;“赵军有二败之理,其一,赵国师出无名,无名而伐我中山,军中将士必然多有抱怨;其二,赵雍此人性情暴戾,为人性情乖张,竟然脱去华夏衣冠去像那些胡人一样穿着简陋的衣服,此举无疑是倒施逆行,赵国国内反对他的人一定如过江之鲤,相反我们中山国尊崇先王之道,行的是仁治。赵国以不仁伐仁义之师,焉有不败之理?”
此言一出,满朝竟有一小半的人出言附和,皆口称极是。
司马喜在一旁听着心中冷笑不止,心想这便是腐儒误国,明明死到临头了,却还满口先王之道,满口仁义之说。宋襄公到是仁义,可是却惨败给了不仁义的楚军,最后身死为天下人所笑。(宋襄公,春秋宋国国君,国小却欲继承齐桓公的霸业,不切实际地空谈古时君子风度,为了守迂腐的信条在政治军事斗争中处处被动,并且把仁义滥用在敌国甚至是敌军身上,以至数次受辱,最后在泓水之战中败于楚军)
不得不说中山国是个奇怪的国家。当初他们的先祖披荆斩棘,与晋国以及其后的赵国纠缠苦战了数百年才创下如今的基业。中山曾亡于魏将乐羊之手,其后中山桓公却靠着顽强的意志和族人坚韧不拔的精神,带领着白狄族人打败了魏军,重新夺回故土立国,并迅速强盛起来,实力让七雄不敢小觑。
桓公随后的成公以及如今的中山王姬尚,却不能居安思危,反而毫无进取之心。中原诸国为了富国强兵,皆推行变法,改革弊政,壮大国家的实力,惟独中山国抱成守旧,不但不积极革新,反而一直在倒退。更让人觉得匪夷所思的各国皆以法家之学为治国之术,惟独中山国信奉的却是儒家和墨家的学说,醉心于仁义和兼爱之说,儒墨两家的信徒大量充斥在朝堂之上,窃居着中山要职。
儒家和墨家思想是为了拯救当时战乱频繁、生灵涂炭的社会国难所开的良方,换句话说就是号召诸侯停止兼并,实行王道和兼爱。这两种学说虽然在民间有着大量的信徒,尤以儒学为甚,但其可用性却大大不足,换而言之儒墨所学的经义完全是理想主义,适合天下太平时虽推行的,在愈演愈烈的诸侯兼并战中,这两种理想主义无疑是天方夜谭。
这就是为什么孔子周游列国,诸侯待之若上宾,却无人敢用他;墨翟一生以非攻、兼爱为己任,在民间有着大批的追随者,可列国统治者却视墨家为洪水猛兽。归根到底,这两种学说并不适合当时的乱世,所以在列国中没有市场,相反以富国强兵为任的法家则大行其道,争先为各国所追捧。
列国都在奖励耕战,中山国却别出心裁的推行“贵儒学而轻壮士”政策,致使“战士怠于行阵、农夫惰于田”,白狄人血脉中的尚武精神很快就迅速消融,中山国也出现了“兵弱于敌,国贫于内”的局面,实力迅速衰退,到了姬尚手中时,中山国已经再无半点当年强盛之国的风貌了,只是在赵国的不断蚕食下残喘延续。
当然最重要的一点,儒学和墨家之说在中山大行其道的根本原因,正是司马喜一手促成的。他在得到姬尚的信任后,不断潜移默化的改变着姬尚的想法,提拔了大批华而不实,只会夸夸其谈的儒生进入朝堂,执掌中山国。
所以司马喜虽然心中不屑,却装出附和道;“文大夫所言极是,大王确实不用过于担心,赵军虽然势大,却不能长久,一旦长久,齐魏必出兵其后以牵制赵国。”
姬尚最为信任的就是司马喜,他见司马喜也这么说,自然也就相信了,这才面色稍霁,松了口气道;“如此寡人就放心了,当真是虚惊一场,只是那季辛实在可恨,只可惜他满门已经被抄斩,否则寡人倒是可以一解心头之恨。”
司马喜笑着说道;“大王尽管放心,以后有的是机会。”
又想起什么,面色一沉忧心忡忡的说道;“不过大王仍然不可大意,赵军如今势大,灵寿城内又兵微将寡,若是赵军强行攻打灵寿,我们倒是棘手。不如快马传书丹丘华阳的歌关城,令他们火速刷主力军返回灵寿增援,与我们大军合兵一处,这样依托灵寿的城高池深,必然可以万无一失。”
“那就如爱卿所言,你自去安排就是。”
“微臣遵旨。”
第六十五章 中山狼(三)
原野之上,大队的骑兵立马静静的待在原地,虽有五千余众,却几乎听不到任何人马喧哗。
这些骑兵身着短襟胡服,外套简易的皮甲,远远望去装束与一般的胡人士兵几乎没有任何差异,只有那头盔上高高竖起的“雉羽”才能证明他们是中原大国赵国的骑兵。
待见到骑兵们所佩戴的武器,高地优劣之分便一目了然。赵国骑兵无论是长弓还是短剑,其制作之精良,都远非胡人所能比的。马上的骑士们一脸的精悍之色,身材远较普通士卒高大许多,胯下的坐骑也多是高头大马,膘肥体健,一些要害之处用皮甲紧紧护住,
显而易见,相比于胡人那种上马即可为兵的骑兵,赵国的骑兵无论是在素质上还是装备马匹上,超过的都不止一点半点,这也是为何赵人以胡人为师学习弓马骑射,却能将他们击败的原因所在。
在中原各国还习惯于车兵混杂步兵的进攻方式时,赵人已经率先发动了一系列的军事改革,抛弃了沉重繁冗的车兵,而采用了更为机动灵活的骑兵部队,在战术思维上远远将各国甩在其后。这也是赵国之所以能在“胡服骑射”后短短的几年内迅速兴盛起来,军事实力与秦齐相媲美的根本原因所在。
穷则变,变则通。正是面临着绝境才会想着抛弃过去的一切旧的思维束缚,大力倡导新的变革,从而富国强兵。当年的秦国商鞅变法如此,如今的赵国的胡服骑射亦是如此。而昔日强盛的中山国,正是因为安于享乐、不思进取,才会沦落到今日山穷水尽的地步。
这支赵国骑兵在原地等待了大半个时辰,人尚未有事,胯下的坐骑倒是渐渐按耐不住,不断有马打着响鼻,不耐烦的刨着草地。在骑士不断伸手轻抚鬃毛的安抚下,这才止住了骚动。
赵章一马当先,在队伍的最前列,探头不断的望向远处,手中的马鞭不断挥起又放下,脸色露出不耐烦的神色。身后的田不礼想比则要安静许多,正坐在马上闭目养神,一副没精打采的样子。
虽是夏日午后,天气却是阴天,所以并不太炎热。田不礼这些年习惯了锦衣玉食,再加上年事渐高,如今在赵国行伍之间倒是吃足了苦头,整日腰酸背痛昏昏欲睡的。不过他人到也硬气,这些日子来都是强咬着牙一声不吭,每日只是跟着赵章不断奔波劳碌,短短十几天下来,倒是晒黑了许多,人也清瘦了不少。
远处一骑飞快驰来,朝着赵章防线快马加鞭而来,正是赵军的斥候。赵章见此忙打起精神,催马迎了上去,不待那斥候停马便迫不急问道;“如何?”
那斥候猛的一拉马缰,骤然停下啦马势,拱手禀道:“报公子,伍长遣我来报,向东三十里内未发现敌情。”
赵章有些失望的挥了挥手,“继续探查。”
“诺。”那斥候迅速跳转马身,又飞快离去,只留下一脸烦躁的赵章在原地。
赵章又耐着性子等了一会,终究还是忍不住开口问道田不礼,“先生,你说父王让我来此究竟适合原因?”
田不礼缓缓睁开眼睛,赵章一脸不耐的神色正印入眼中,心想这个赵国大公子无论是长相还是脾气,都似足了赵雍,惟独这心计和耐性上,却是要差上许多。
脸上却微微一笑,道;“公子稍安勿躁,既来之则安之,心急又有何用,倒不如耐心等待。”
赵章一拉马缰,坐骑高扬起前蹄长嘶一声,又转身过来与田不礼并肩而停,脸色有些不善的说道;“稍安勿躁,说的好听,我们可是等了足足一个时辰了,别说中山大军,就连一只兔子也没见着。”
“先生,你说父王究竟什么打算,莫名其妙的让我来这里阻击中山军。如今中山军都是龟缩在城中不敢外出,哪里还会有这么胆大的在野外行军,我看父王也是老糊涂了,简直莫名其妙。”
说道最后赵章忍不住口中生出抱怨,埋头说道。田不礼却是面色一紧,小心的看了一眼在身后远远隔着的军士,低声叮嘱道:“公子,这等抱怨的话在我面前说说也就罢了,在别人面前千万不要说起。赵国骑兵是主父一手带出来的部队,军中的耳目和崇拜者多不胜数,若是不满之情不小心让主父得知,那就大为不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