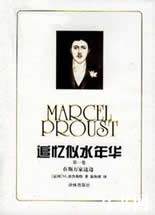灼华年-第23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花厅里早些时笼着淡淡的百合香,如今依旧炉香微篆,香气还未散去。何子岑记得这是陶灼华最爱的味道,便低低开口道:“你的习惯到从来未变,难道现如今还是夜里睡不踏实?”
夜色绵绵,窗外的琼华如霜,到似是瞧见了多年以前的月光。
初至大阮时,陶灼华自然夜夜睡不安宁,一时记挂着与何子岑的爱恨情仇、一时又是后宫间的步履维艰,还要想方设法与远在大裕的瑞安缠斗,便只得靠着百合花的香气安眠。
后头放下了心结,陶灼华的心情愈来愈好,已然极尽平和。笼一炉百合香不再为得安心睡去,只不过成为一种习惯。
她浅浅而笑,揭开了香炉盖子,又搁了块百合香进去,这才在两兄弟的对面落坐,云淡风清地说道:“不过是早些年的习惯成了自然,如今嗅着这味道觉得亲切些,到不是为得睡不好觉。打从明日始,换些安神宁气的檀香试试。”
第四百八十一章 剖心
一把百合香的习惯虽未曾改变,何子岑从陶灼华素日淡然的笑意间却分明觉出了岁月沧桑,他们一个一个都不复从前的旧模样。
而从前的记忆里,陶灼华尤其喜欢碧绿的衣衫,时常着一件天水碧的裙衫,在芙蓉向日的荷花丛间,是那样的明艳无方。
后宫中又无人旁人与陶灼华争宠,但凡新晋的蜀丝、贡缎,何子岑都是挑了各色浓碧浅绿的颜色一律赐下,由得她每日似嫩柳抽条,莹莹新碧美艳动人,浑然春日的色泽四季不褪。
如今瞧着伊人身上浅浅的玉簪白,虽有浅紫的绘绣繁朵点缀,却总归是极素的颜色。何子岑想着几次三番地照面,陶灼华十次里到有八次都是着了月白的裙裳,纵然上头绘绣几枝鲜亮些的花枝,总是难掩那一抹素淡带来的哀愁。
何子岑目光复杂地望着她,轻轻问道:“这几年里,怎得穿衣着装到换了喜好?灼华,你从前不似这般喜欢素色。”
四十年洋溪湖畔的守望里,陶灼华不肯原谅自己,亲手纺织、亲手浣洗的白衣是唯一的寄托。陶灼华生怕何子岑难过,才待开口掩饰几句,何子岱却仰头将茶饮进,闷闷出了声道:“兄长,这个问题我来回答。”
现如今的陶灼华沧桑过后,已然浸润着半身清风半身明月的淡然,从她脸上寻不出一丝曾经国破家亡的哀愁。
而当初那四十年的雨露风霜,却是世间鲜少有人所能忍受的凄苦,何子岱一直是那个悄然躲在远处,想帮她一把,却又半分无能为力的人。
他看着她采桑养蚕,看着她抽丝织布,再看着她纺线成纱,最后变成无数块相同的白布。白袄白裙、白衣白裤,四十年里,那便是她身上唯一的色泽。
她终其余生,都在为何子岑穿孝,算做对自己无心之失的救赎。
何子岱忽然撩起衣襟何子岑面前一跪,低低泣道:“兄长,是我当年辜负了你的托付,将嫂嫂丢在瑞安那贱人的府门口,葬送了你们的亲骨肉。”
一段话压在心里多年,何子岱已然不堪重负。而伴随着何子岱的讲述,又将三个人的记忆重新拉回到国破城亡的那一日。何子岱深吸一口气,抹去脸上的泪水,努力让自己平静地述说下去,将昔年逃命的一幕点点滴滴说给何子岑听。
多少不堪回首的画面,其实在陶灼华心间已经变得模糊。唯有想起那骨肉剥离的痛苦,才体会到什么叫做锥心刺骨。陶灼华不自觉地将手抚上自己的小腹,方才拭净泪水的双眸霎时又变得湿漉。
“灼华、灼华”,听得她小产之后被瑞安抛到府外,险些命悬一线,何子岑疼惜地不知该说什么才好。他不顾何子岱在旁,将陶灼华紧紧紧箍在自己怀中,一声一声唤着她的名字,两行泪水顺着脸颊直直滑落。
本已为早便尸骨无存,何子岑不曾想青州府里还有自己的衣冠冢,更不曾想到陶灼华以四十年的缟素做为对自己的忏悔。一个明明毫无过错的人,却甘愿背负了四十年的包袱,一直生活在沉重的负罪感里,埋葬了大好年华。
陶灼华扬起泪眼迷离的脸,对前世屈服于瑞安的淫威感觉无比痛心,亦对何子岑真心实意说了一句对不住。
“灼华,我当日若有一星半点怪你,又如何会叫子岱救你远走?”何子岑伸手将她的唇掩住,想起那一夜自己的决绝,懊悔得无以复加。
他紧紧抓住陶灼华的手,哽咽着说道:“大阮国灭,与你一个女子何干?我早便想得通透,自己当年的确疏于政务,这罪责在我并不在你。”
前世里不曾做一个好皇帝,总是想要过份安逸,何子岑深深忏悔自己的过错,认真剖析着往日的点点滴滴,亦对陶灼华走遍地说了一声歉疚。
何子岱跪在地下始终不肯起身,冲着两个人深深拜道:“苍天有眼,许我何子岱重新归来。从前我虽然做了些糊涂事,也想要拆散过你们今世的姻缘,往后却必定以哥哥与嫂嫂马首是瞻,再不敢故做聪明,肆意揣测他人。”
各怀心思,自然不如敞开心扉。何子岑一把拽起何子岱,在他胸口重重擂了一拳,却又哭又笑地揉了揉他的头顶。
亲弟弟从前虽然对陶灼华颇有防备,后头又铸成大错,却已然花费了四十年的时间守护在陶灼华身畔,并不算是完全辜负了何子岑的托付。
陶灼华虽不与他照面,洋溪湖畔却多承他的照料。两人之间并没有苦恨连天的深仇,陶灼华对何子岱虽有怨恨,也早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湮灭。
瞧着懊悔万分的何子岱,陶灼华又何必在他心口洒盐?此时悠悠一叹,想得更多的是前世里何子岱对何子岑的万般维护。兄弟如手足,二人的真情毋庸置疑。
她向何子岱叹息着说道:“往事已矣,前头各人都有错在身,我并不怪你。”
陶灼华悄然起身打了热水,将拧好的毛巾分别递给柯子岑与何子岱,自己也拿帕子覆了覆眼睛,这才怆然笑道:“只怪从前的自己糊涂,与瑞安交易便是与虎谋皮,我不但害得子岑你心生猜忌,更害得陶家人身首异处。子岱从心里对我防御,原也没有什么错误。”
三个人将所有的经历凑到一起,有些谜题却依然解不开。何子岑提及那只向自己横空射来的红绫羽箭,又提及临终的那一刻那无比熟悉的笑声,始终不晓得真正蛰伏在自己身边的敌人是谁。
四十年间,陶灼华不与外界为伍,连大裕的改朝换代都置若罔闻,更何谈能晓得那幕后之人。她将从前与苏梓琴的谈话合盘托出,请两兄弟帮着参详。
及至听得苏梓琴也是重生之人,何氏兄弟哑然失笑。
何子岱轻轻叹道:“果然是上天待咱们不薄,晓得前世里个个抱憾而终,特意给了机会重新补偿。照嫂嫂这般说,那李隆寿与苏梓琴也是一对可怜人。”
第四百八十二章 抽丝
白驹过隙,时光宛若重又倒流。听得何子岱再次以“嫂嫂”相称,陶灼华脸上添了些娇酡醇粉,似窗外簇簇的榴火。碍于此时此刻,却只得低低嗔道:“子岱,千万别如此称呼,只怕叫旁人听去。”
到是何子岑轻咳了一声,制止何子岱道:“你知我知,莫要胡乱称呼,败坏灼华的清誉,且把你对她的尊重放在心间便好。”
何子岱这几年的心情也是跌宕起伏。头前陶灼华初至,他生怕兄长再与她走到一起,重新为瑞安所治,更怕何子岑为了陶灼华荒废政务,不止一次在两人之间使绊子。及至瞧着叶蓁蓁总想接近何子岑,他又下意识地排斥,其实心里还是想将这对前世的小夫妻凑在一处。
后头瞧着陶灼华与瑞安公然作对,在宫里混风生水起,又一味替何子岑铺路,极为小心地避开了前世的艰难险阻,他便又疑心她亦是转世重生。
瞧着这个也不对头、瞧着那个也颇为奇怪,何子岱到有些草木皆兵,恨不得身边能有个人商议。今夜三人重新相认,何子岱自是长嘘了一口气,那两声“嫂嫂”却是发自肺腑,比前世里更加诚心。
三个人也顾不得月影早便西斜,就着说不完的话将一壶大红袍喝得没什么颜色,陶灼华便唤着娟娘,请她重新再泡一壶。
娟娘瞧着夜色越来越深,总觉得男女授受不亲,一颗心悬在半空里七零八落。她就着换茶的空当轻轻扯一扯陶灼华的衣袖:“小姐,时辰不早了,两位殿下在这里总归引人注目,有什么话明日再说可好?”
“娟姨,我们长话短说,再叙几句便就散了。”陶灼华心间梗着不少谜团,此时方能畅所欲言,自是不甘心半途打住。
何氏兄弟也是这般意思,都觉得有满腹的话想要倾吐。何子岑便起身冲娟娘一揖道:“娟姨,您不必担心,我与子岱都有分寸。我们的确是有些要紧话要说,如今不吐不快。您放心,赵五儿守在外头,这青莲宫附近半个身影也没有。”
娟娘听得何子岑频频如此称呼,晓得这里头颇有几分爱屋及乌,只碍着两人并没有名份,到更添了忐忑。她反驳不得,只得客气了几句方悄然出去。
几个人将所有的事情凑在一起,矛头自然是直指谢贵妃与整个宣平候府。
若不是前世里钱将军忽然被杀,何子岩被仁寿皇帝急召回京之中再不起用,那个太子之位大约落不到何子岑的头上。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仁寿皇帝避而不谈,只打从那日起身子一日千里,显然受了极重的打击。
仁寿皇帝没有褫夺何子岩亲王的封号,而是不顾谢贵妃的一再阻拦,将他贬谪到遥远的蜀地,并且下了命令无召不得回京。
前世里仁寿皇帝对册立谁为东宫太子明显一直摇摆不定,如今细细想来,他该是对这几个儿子都不大放心。最终选择交给何子岑,亦不过无奈之举,何子岑晓得自己最大的弱点便是性子太过温吞,并没有何子岩的杀伐决断,也不及何子岱的神勇无敌。
那个时候何子岩已经被贬谪出京,仁寿皇帝望望留在面前的二子,只是郁郁叹息,选择将某些东西带进棺材里也不吐露分毫。
何子岩即位之初,自是勤政爱民,后头渐渐觉得安逸,就有些疏于政务。何子岱到是绝无二心,一味忠心耿耿耿辅佐着兄长,负责天下军队的调动,替何子岑分着大半的辛劳。
何子岕因为只领着郡王的虚衔,何子岑又得仁寿皇帝嘱托要暗中照拂他们姐弟,便没有将他外放出京,而是在宫外赐了座郡王的府邸,乐得他逍遥自在。
何子岑的印象里,当时三兄弟感情还算不错。兄友自然弟恭,何子岕每月入宫那么几回,三个人一起下棋饮茶,也能共叙天伦。
唯有远在蜀地的何子岩气焰越发嚣张,俨然在蜀地自立为王。他不见得对何子岑有多么尊重,更多的是阴奉阳违。以至大裕兵临城下时,何子岩也不出兵相助,而是遥遥观望,想要坐收渔翁之利。
后宫里显然也不太平,中宫位置虚悬,贵为宸妃娘娘的陶灼华受制于瑞安,自是担不起后宫之主的责任,便唯有劳动已然稳做太后之位的德妃娘娘。
谢贵妃昔日份位高于德妃,如今两人一为太后一为贵太妃,乍然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转变,自是意难平。她仗着宣平候府的得势,平日便没少阴阳怪气,背后整出不少幺蛾子。
德妃与何子岑都是仁善之人,主张家和万事兴,两人一味的忍让不仅没有叫谢贵妃与何子岩消停,反而助长了他们嚣张的气焰。纵然如此,何子岑也未曾想到谢贵妃和何子岩能做出通敌卖国之事,自是留了极大的隐忧。
而如今能够确定的是,谢贵妃这些年明面上与瑞安面上势同水火,实则经由高嬷嬷、许长佑等人牵线搭桥,早便是一丘之貉。两人打从多年前便存了不轨之心,意图祸乱两国的朝纲。
只是这几个人都太过熟悉,里头并没有最后拿着红绫羽箭谢向何子岑的那一位。何子岑始终觉得当时那声音极为熟悉,好似时常能够听到,偏就与身畔这些人对不上号,一直郁闷至极。
他沉吟着望着何子岱说道:“依理推断,谁从中得利最大,谁便是最该怀疑的人。只是我早便身死,灼华又是多年不闻世事。子岱,你来回想一下,大阮城破之后,谢贵妃与何子岩何得了什么好处?”
这些正是何子岱心间的未解之谜。他摇头追忆道:“若她们往后的日子锦上添花,亦或大阮国灭之后,何子岩得了什么名头,也便做实了与瑞安里外勾结的罪名。偏这母子二人没有捞着半分好处,何子岩闻得京城攻破,率蜀军千里杀回,反被瑞安的人在途中诛杀,等同全军覆没。而谢氏,却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