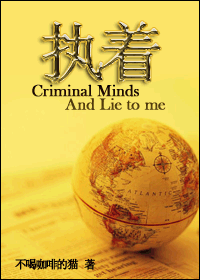SOTOPIA:人造伪神-第2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杰奎琳依旧凝视着墓碑上的照片,没有在意史蒂文和莫斯克维奇的目光。许久,她才轻声说道:“我很羡慕她,以及你们——在结束一切之后,还能有一个公开的葬礼。可我们就连死亡都不能为人知晓。”
史蒂文和莫斯克维奇看不清她的表情,倒也能大致猜到那会是一种落寞与哀伤的混合。她或许不会哭,但无法哭泣有时会比酣畅淋漓的发泄更难以忍受。
“这场车祸……确实只是意外吗?”莫斯克维奇谨慎地问道。
杰奎琳点点头,视线仍旧没有从墓碑上移开:“一场彻头彻尾的意外。”过了几分钟,她才站起身,缓缓说道:“我的手上还有不只一份无法公开的讣告。”
史蒂文只是摇头:“我已经不在FBI了。”
“这样啊。”杰奎琳的声音听起来毫无生气。
离开时,史蒂文注意到她的背影微微颤抖,瘦削的肩膀紧绷着,脚步并不坚实。她终于还是哭了出来。
他看了看身旁的莫斯克维奇,轻轻搂了下后者的肩膀:“……我们走吧。”
“史蒂文,”莫斯克维奇突然开口说道,“我还是去见一见伊莲娜——雷诺夫人吧。”
史蒂文先是一愣,很快又恢复了寻常的表情:“你改变主意了?”
“是她们让我改变了主意。我害怕自己不会有第二次机会。”
“好吧,我会保护你的。”形同表白的话语在这位前探员口中,却是那么稀松平常、理直气壮。
阴郁的天色和冰冷的雨幕依旧笼罩着洛杉矶,细密的水流在玻璃窗上肆意流淌。
梅纳德站在窗前,面向窗外铅灰色的都市丛林,眼神没有焦点,正像他两年前看着西奥多离开一样。而在他身后,电视上正播送着国际快报,女主持的声音受雨声的影响显得模糊不清。
“——一架国籍不明的米…26‘光环’直升机在叙利亚边境被地面火力击落,机上人员全部丧生。据知情人透露,死者包括参与地区临时和谈的叙利亚、约旦、土耳其等国的军方要员,以及北美地区某安全顾问公司高层人员,此次飞行目的地为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目前尚无组织声称对此次袭击负责。”
这个无情的男人终究还是为自己的理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一切都是理所应当,悲剧的发生只是时间问题。梅纳德这么想着。
而在梅纳德意料之外的是,几天后,他收到了西奥多的遗物。
准确说,那只是一个普通的深蓝色行李箱。梅纳德记得,西奥多离开时拿的就是那个。送箱子的人穿着铁蓝色制服,长着不容易让人记住的大众脸,面无表情地说明了来意:“参与和谈的人基本都写了遗书,并确定了遗物转交的对象。不过也有例外:西奥多·拉克斯,他作为这次和谈雇佣的安保负责人,只交代了要把他的东西送给谁。”
梅纳德看着手中的信笺,上面没有遗言,只有自己的地址。事实上,他不觉得愤怒,也没有痛哭的冲动,只是突然感到心脏像被重锤敲击一般,仿佛下一秒就会猝死在自己家门口。
“……就只有这些吗?”梅纳德发现自己的声音沙哑得可怕。
报丧者摇摇头,脑袋微垂着表示哀悼。
“他没有另外说什么?”他不死心地小声追问。
“非常抱歉,没有。这已经是他留在驻地的全部东西。”
再问下去也无济于事。即便有什么回答,也未必是自己想要的结果。
目送着对方离开,梅纳德把行李箱提进了房间。份量很轻,想必只是衣物之类无关紧要的东西,各种重要文件恐怕已经被回收,或是在空难中销毁。打开箱子,里面的物品也确实如梅纳德所料,都是适合中东气候的简单服装,以及从美国带去的剃须刀之类的日用品。西奥多很注重仪表,这一点梅纳德印象深刻。
他翻遍了行李箱的每一个夹层,把每一件衣服拎起来仔细搜索,始终没找到半张有用的纸片,更别提西奥多留给自己的话。最后,梅纳德颓然地倒在自己的床上,手里还攥着西奥多的西装外套。
那是他离开洛杉矶前定做的。西奥多自己说过,他喜欢这样的质地和款式,就连内衬的针脚都一丝不苟。这件从遥远的叙利亚加急运回的遗物上还带着雪茄与古龙香水混合的轻微气味,衣领上有安全顾问公司小小的徽章。
“——下地狱去吧。”梅纳德喃喃自语。眼眶还是干涩的,喉咙深处却已经泛起腥甜的味道,胃部隐隐作痛。他蜷起身体,把脸埋在死者的衣服里,仿佛在回味若干年前匡提科基地凌晨时分的缠绵。“我们本应一块儿下地狱……”
第45章 第四十三章 母亲
2011年将要过去,洛杉矶的冬天却依旧没有什么冬天的感觉。史蒂文突然发现,比起之前共同生活的时候,莫斯克维奇越来越沉默了。
虽说他本身就带着一种独特的疏离气质,对于大多数人也仅是礼节性地报以社交式的矜持微笑,说起话来常千回百转的令外人摸不着头脑。可与现在沉浸于颓丧和失落的悲哀神情,有时甚至显得精神恍惚的状态相比,以往那种仿佛挑衅的作风明显要好得多。或许是凯伊死后无来由的危机感,或许是暴雨将至的可怕直觉,哪一种都可以作出一定程度的解释。
史蒂文看在眼里,采取的行动却相当有限。他深知自己应该做到哪一步,以及只能做到哪一步。
答应与雷诺夫人见面是莫斯克维奇作出的决定,主动与Sotopia方面联系的则是史蒂文。他留着罗萨的联系方式,给她发邮件时,眼角的余光还瞄着坐在沙发上捧着书强作镇定的莫斯克维奇。
史蒂文几乎能看见莫斯克维奇在想什么。
上次做到一半的时候,莫斯克维奇突然瞪大了双眼,怔怔地看着天花板,吓得史蒂文马上停下了动作,伏低身躯,轻轻拍了拍他还在发烫的脸颊,关切地低声问道:“怎么了?”
过了几秒,莫斯克维奇才缓缓将视线重新聚焦到史蒂文脸上,似乎作了很大的努力才确保自己的声音不至于颤抖。“我突然不想待在这儿了。”
史蒂文僵在了原处,□□掀起的热潮缓缓冻结。可他依旧很冷静——他看似毫无波澜地审视着莫斯克维奇隐忍的表情,哪怕心中已是翻江倒海。
“你想太多了。”史蒂文的声音很闷。他尝试着进行疏导:“这里虽然情况复杂,但要比你想象中安全。”可一想到意外身亡的凯伊以及近期高发的威胁公共安全的恶性事件,他自己都觉得这话缺乏说服力。
莫斯克维奇抬起腕,用手背挡住自己的双眼,干笑了两声。在史蒂文听来,这笑声比绝望的恸哭还要苦涩。
“我想活下去。”莫斯克维奇轻声说。“可你们值得更安全的生活。如果不改变现状,你被卷进来只是时间问题。”
史蒂文没让他再说下去——年长一些的男人直接用吻堵住了莫斯克维奇的口。他不想听到对方接下来要说什么,一半是因为他已经猜到了内容,一半是即便那些都是实话,他也无法顺其自然地接受。
“别再说了。”史蒂文在莫斯克维奇耳边喃喃道,但更像是对自己的暗示。“我说过,选择权在你。可总有一天,我也会作出决定。”
莫斯克维奇或许是哭了,嘴角却带着勉强的笑:“你的决定里会包括我吗?”
在“如果你希望的话”和“无论如何都会有你”二者之间,史蒂文选择了沉默的拥抱。
奥列格咖啡馆里,莫斯克维奇还是见到了自己好些年不见的“母亲”,史蒂文则坐在几桌之外默默观察。他们的样子很不显眼,极其自然地融入了普通客人当中。
“伊莲娜,”莫斯克维奇先是习惯性地称呼了这个名字,但又很快换成了史蒂文等人惯用的叫法。“雷诺夫人。”
坐在他对面的女人微笑着点头。
她已经老了。
克里斯汀·雷诺,原名伊莲娜·科莫罗夫斯基,曾是来自东欧的移民,近半个世纪前的暴力事件的受害者,而今则是剑走偏锋的社会学家。离开教坛、淡出学界之前,她就已经作为Sotopia学会的成员,在另一个“不见天日”的领域参与了若干实验性的科研项目。
而莫斯克维奇,正是她在洛杉矶市郊研究基地里观察过的实验体之一。
平心而论,莫斯克维奇并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判定雷诺夫人与自己的关系——她显然不是自己生物上的母亲,可就社会性而言,双方的关系也建立在难以言喻的研究与被研究过程中,这使得“母子关系”放在这儿也显得不伦不类。
莫斯克维奇缺少的不是睡眠,而是放松的精神状态。与长相比实际年龄年轻的雷诺夫人相比,他反而显得憔悴的多。对话过程中,莫斯克维奇也更多的保持了沉默。他并不厌恶眼前这位矜持优雅的女士,相反,他甚至十分感激她——正是幼年时那个关于“自由”的问题,成了他逃离囚笼的起点,虽然这也成了他此刻无尽痛楚的源头。
睿智成熟的雷诺夫人能够充分地理解这一点。她慈爱地注视眼前的青年,心里想着上次见到他还是在若干年前的地下基地,当时的莫斯克维奇还处在身体的成长期,长相正是变化过程中带着微妙阴柔气质的类型;尚年幼的罗萨那时还看不出和“兄长”如此相像,只是个再普通不过的漂亮小女孩。
再看看自己,从当时年轻的研究员到现在的学会高层,被掩藏的惨痛过往,走向学科巅峰的过硬资历,共同使她由无辜受害的东欧少女“伊莲娜·科莫罗夫斯基”变成了“克里斯汀·雷诺”,莫斯克维奇的存在,似乎正好成了她这些经历的一个见证。
“你有了名字。”她先开口说道。泛着灰白的浅金色头发梳理得很好,十分符合这个年龄的知识分子的典型定位。漫长的时间在使她苍老的同时,也慷慨地给予她与岁月相映的独特魅力。
莫斯克维奇盯着眼前的茶杯,手边的餐点没有动过。他点点头,低声说道:“身处外界,我总得有个名字。”他不知道自己该说些什么。
雷诺夫人没有拖沓地表达自己的情感,也没有为过去欠缺人道主义精神的洞察者计划作出冠冕堂皇的辩护——就这一点而言,莫斯克维奇的个人特质或许继承于她。相反,她低下头,从身边精致的提包里抽出了一个有些年头的档案袋,从它厚重的分量不难看出里面装了不少纸质材料。“我是来和你告别的。”
这句话让莫斯克维奇摸不着头脑,心底却再次泛起一种不祥的预感。
社会学家轻笑着,语气十分温柔,令莫斯克维奇不合时宜地想起了史蒂文的母亲——或许这正是母亲对孩子说话的语气。“史蒂文大概已经和你讲过我的故事了吧。他曾是梅耶夫妇的学生,我们在讲座上见过,我对他有些印象。”
莫斯克维奇迟疑着点头:“……说过一些,但不多。”
雷诺夫人呷了一口咖啡,眼角的皱纹仿佛流淌着怀念的神色:“不过那也不是什么美好的故事。好像就在古巴导弹危机的第二年吧,那也是我们家搬到美国的第四个年头。”座位靠窗,她侧头看着街道对面城市公园里闲散的游客,语气平淡的像在谈论别人的事。“大概是出于对外乡人的敌视,或是单纯的无法控制自己的犯罪冲动、就近寻找合适的下手对象,就在某个再平常不过的周末下午,我被几个住在附近的年轻人殴打并□□了。”
——这件事情,史蒂文曾隐晦地跟他提过,只是当时莫斯克维奇没想到那些双关语指向的事实就是如此的残酷。
“我的父兄没能如愿为我复仇,但有人替他们完成了愿望。痛苦与恐惧让我觉得自己无法在那继续生存,于是,离开医院没多久,我就独自离开了家。我跌跌撞撞地流浪到最近的城市,眼看没法活过那个寒冬,是雷诺先生收留了我。”此刻,雷诺夫人的眼神里满是对恩师的感激。
“皮耶罗·雷诺?”莫斯克维奇读过他的著作,把仿佛存在于书本之中的理论家与现实事件联系起来总有一些奇异的感觉。
雷诺夫人点点头:“他的孩子很早就因病夭折,我就成了雷诺夫妇的养女。他们不知道我经历过什么,也不曾过问,只是让我正常地上学、社交。直到成年,我才把自己的真相告诉他们。在那之后,追随养父走上学术的道路,以‘克里斯汀·雷诺’的身份生活,也就成了理所应当的事。我曾以为这个社会就是地狱,但他给我了生命的第二种可能。”
莫斯克维奇皱着眉说:“可在实验室里,你告诉我你叫‘伊莲娜’,那明明是你想要遗忘的过去的身份。”
她微笑着摇头,轻微地叹了口气:“确实,我曾经想要遗忘那起事件,甚至连带着遗忘自己的过去


![(天国王朝同人)[天国王朝同人]The Road To Jerusalem封面](http://www.34gc.net/cover/18/18723.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