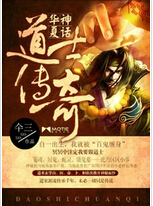宠逆_夏滟儿-第3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他念在心里,钢琴准备好,他坐下弹奏,开始唱起抒情歌曲:徐佳莹〈寻人启事〉,这是他在“歌战”海选唱的歌,那种渴望找到一个人的心情……
他把所有心意化作音符,传达给听众,台下则予以回报,有时鼓掌有时欢呼有时一并唱唱跳跳,有时仅是静静挥舞萤光棒。一切和谐,他以为自己无所求,可一想到未来即将离开,仍产生不舍。
和是否成名、能否赚钱无关,而是一种纯粹分享。
分享自己的人生、分享走过的一切、分享种种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在作品里,邀您共同徜徉。
这是所有演绎人的本质。
所以此刻,他们才会在这里。
最后一个琴键落下,苏砌恒深呼吸,忍住泪意。他没有任何遗憾了,甚而感谢,谢谢姊姊生下小熙,因为小熙,他阴错阳差走上这条路,遇见男人,产生自我,将之发散。要谢的人太多,所以──
那就谢天吧。
第54章 《宠逆》End。
在演唱会结束一个月后,毫无预兆,苏砌恒走了。
而一周前,他们还在屋子里做爱,苏砌恒回到最初的良和温顺,他们不谈任何不愉快,只享受性爱,唐湘昔很久未如此纵情恣意,有什么比枕边小情儿的柔从更令男人舒心痛快的?至少他是想不到。
他沉溺其中,决定暂时搁浅,不去深思二人关系。
两人趁孩子不在时机,在家里各处全做了,甚至包含男人办公室,苏砌恒简直怀疑他被淫魔上身,不管在哪儿见了他都得腿发软,男人发情次数更甚以往,演唱会后足足一周苏砌恒根本离不了他下头孽棍。
男人欲望如焰,焚他全身,细胞都被毁成灰烬,身体各部成了性器,敏感得随便一碰即有反应。
他羞耻极了,床笫间各种哭喊求放过,好在男人尚有理智,夜夜笙歌不早朝了一段日子,总算歇下。
唐湘昔预计出差去韩国一趟,原本想带青年一道,可对方以孩子为由拒绝了。
临行之际,苏砌恒给他煮了一壶姜汤,说让他带在路上,“据说韩国天气还挺凉的,重口的东西少吃点,烟……算了,总之你多注意身体。”
青年难得温情,一席话把唐湘昔熨贴暖了。
他不知道的是,在门掩上之际,青年眼里淌落了泪。
一周之后,唐湘昔大包小包,拎着各式礼物归来,屋里却无人烟。
苏砌恒来时简单,走时轻便,唐湘昔一时没觉察发生何事,只觉微妙,直到看见孩子房里的哆啦A梦玩偶不见了,才产生怀疑。
他足足佁了三分钟,继而冲进苏砌恒房里翻箱倒柜,确定人和证件等物件彻底消失,第一时间他问遍所有相关人员,尤其丁满,可无人知晓去向……青年蒸发了,带着孩子。
最终,他去了南洐事务所。
唐湘昔直接问:“……他在哪里?”
陆洐之淡定:“我们这边是律师事务所,不是征信社。”
唐湘昔气愤难平,整日未阖眼,导致双目充满血丝,看来赤红。“我会提告,第一他违约,第二他拐带小孩……”
“合约问题他已委托我帮他全权处理,第二个……”陆洐之眼神犀利:“拐带谁家小孩?罗家?还是……唐家?”
唐湘昔:“……”
苏砌恒知道了,孩子不是罗家的,是他大哥的。
唐湘昔点烟抽,整个人疲惫不堪,坐在那儿没有动弹。他迷惑苏砌恒怎会觉察,更不清楚苏砌恒如何确定,唯独可以推断,从一开始,他压根儿没相信过自己的说词。
他自以为布了个漂亮的局,然而狡兔三窟,兔子从另一个洞缝溜走──他不笨,甚而聪明极了。
想及这段时日来青年表现、在床笫间的体贴缠绵……温柔乡果然恐怖,惑乱他放松警惕,他想怒骂、想大吼、想歇斯底里摔尽眼前所有东西,彻底毁坏,可另一个声音淡淡告诉他:你没资格。
是他先塑造了谎言。
陆洐之早预料他会来,老神在在,把准备好的文件资料递到他面前,苏砌恒立了一本帐目,自他进唐艺以后的培训费,以及所有该归还给公司的资产,收入支出,罗列细密,估计给专业的会计师看,都看不出瑕疵。
陆洐之:“至于违约金部分,我会代替他打官司,待金额确定,他会以支票方式归还。”
唐湘昔笑了。
真的是,全部算得干干净净、清清楚楚,他当时要求自己确立帐目,倘若是为这一刻,那唐湘昔只能说从头到尾,他就低看了这只兔子。
外在看着傻呼呼的,实则目标明确,一击必杀。
那份表格,明白告诉他:我们之间,就是这么一回事。
从陆洐之这儿套不到有用消息,唐湘昔颓然离开,阳光刺目,天气渐暖,他遣司机离开,自己独步往前走了很久,走到脑袋空白。太多事禁不起深入,他下意识往口袋掏了掏,发觉药吃完了,于是叫计程车,去了孙文初诊所。
对于孙文初来讲,唐湘昔并不是个好患者。
当然病患不分好坏,可第一唐湘昔不遵医嘱,把他当药剂师;第二,唐湘昔……不,唐家人的尊严,不允许旁人刨根问底,就连他自己本身亦然,但不面对问题,谈何解决?
于是恶性循环,药物短暂发挥功效,周而复始,对医生来讲,没有比这更无力的事了。
孙文初这儿没有咖啡或茶,仅有薏仁浆,唐湘昔不喜,从来不碰,今日却道:“给我一杯。”
因为兔子赞过。他说:“孙医师的薏仁浆煮得好香啊。”
孙文初倒给他,唐湘昔举杯来饮,嗤了句:“什么玩意儿。”
孙文初:“……”
明白他情况不对,但孙文初亦无对策,只能随他沉默。
唐湘昔就像一只无生命的人偶,用同一姿势坐在那儿许久,他几度掀了掀唇,似乎想讲些什么,最终还是噎了回去。
如此反覆,教人苦闷。
孙文初叹息:“我想你需要抒发,把心里话说说……就算自言自语也可以。”
唐湘昔依旧没有说话。
孙文初起身,放出巴哈的〈G弦之歌〉,缓和气氛。“我想我还是离开的好,你好好放松,休息一会,自己一个人把话说出来,这里没摄相机,没人会知道。”
说完把灯调暗离去,独留唐湘昔一人。
〈G弦之歌〉旋律缓慢,悠扬柔和,唐湘昔闭上眼,把身体逐渐逐渐埋入沙发里,他像是浸入深海之中,意识迷离,遭受淹溺,被一种很深的倦怠捆绑住,难以脱身,更兴不起逃生之意。
孙文初让他说,可说什么?又有什么好说?
他缓缓启唇,开口:“……我没有错。”
他没有错。
为了家族声誉,为了大哥美满婚姻,为了……他们家该死的那一口气。
“我没有错。”他又说了一遍。
偏偏无力。
他按揉太阳穴,那儿一阵刺痛,这一生走至现在,早经不得承认任何错谬,他不是Gay,他可以和女人圆满成家,苏砌恒仅是他人生短暂光影,很快就会掠去,就像钟倚阳,他现今不也没把他放置心上?
会过去的。
所以……
“我没有错。”
他疲累不堪地说着,日光自窗户筛进,〈G弦之歌〉不停反覆,他放弃了思考,仿佛自我催眠般,一遍遍说着相同字句。天气好极了,他不用担心会着凉,更不缺那碗姜汤,孩子……是得想法子要回来,但此刻他无力,不想动,只能沉浸在旋律之中,净空一切。
“我没有……”
唐湘昔说不下去。
眼角传来一抹酸涩,在最后一刻,他想:他还是错了。
错失了。
※
历经一番舟车劳顿,苏砌恒离开台湾,踏上异国土地。
周围各色人种,说着种种不同语言,他先前曾因演艺工作出国,相较于当时的稀奇,如今倒没了新鲜感,反倒是小熙,抱着他大型哆啦A梦娃娃,对一切兴奋,哇哇大叫:“飞机好大~~喔喔,它动了耶!好酷喔!我们刚刚就是搭那个过来的,对不对?!”
在飞机上分明奄奄一息的,脚下踏地后倒是精力十足,在机场奔来跑去,四处探看。
苏砌恒微笑,看着孩子,心里的惆怅总算淡薄许多。
果然在那个地方,小熙太压抑了。
他对男人情感复杂,一路上尽管已收拾差不多,可内心里仍有一处是怎样也打理不来的,就像那些总觉得有朝一日会用上的物品,无论如何整理,就是扔不掉。
收件人那栏空白……罢,就留着吧。
或许总有一天他会发觉无用,舍得扔弃。
“好了,小熙过来,我们准备出关啰。”他唤回孩子,牵着他的手及抱着姊姊的骨灰箱,步步往前。
一个家,三个人。
只要三个人均在,那便是安身立命之所──
他的家。
离开那一片纷扰,苏砌恒人生里初次相信,自己做了个正确决定。
机场窗外一片湛蓝青天,未来坦荡。
他想,他是对的。
《宠逆》正文完
第55章 《宠逆》番外1之〈苏祈梦〉
她怀孕了。
医生是好友的老公,跟她有点交情,知晓她单身,并未道恭喜,而是公事公办的语气,宣布这项晴天霹雳的消息。
苏祈梦按着肚子,低头睇睐,眼下还不显怀,小腹仅有一点肉感,她月经三个月来一次已成家常便饭,这次若非弟弟坚持要她过来检查一趟,她嫌唐僧念经太啰唆,否则仅以为肚子不适,压根儿没想过这个可能性。
但,不是不可能的。
她已习惯面对风雨,对现实收受极快,不会哭天抢地,她问医生:“如果我想拿掉,现在来得及吗?”
医生没讲什么,就专业分析:“胎儿已经成形,孩子也有了心跳,你的身体……恕我直言,本身底基不够好,拿掉之后有一定风险,未来可能无法再怀孕。”
又是一道雷,霹得苏祈梦滋滋响。
她沉吟片刻,最终回覆:“让我想一想。”
……
走出医院,正值炎夏,外头一片大晴天。
她难得不怕太阳晒,一路踱至公车站,坐在候车椅上,刚才医院里的冷气有些冷,温差下她皮肤泛起一层疙瘩,她想起母亲,体质劳损,可仍坚持要给她生个弟弟,最终伤及本就不多的底蕴,早早患病而亡。
可是她说,她不后悔。
人世来一遭,总要留点什么。
公车来了,苏祈梦没搭,任其喷着废气走过。
那晚……她印象模糊,只记得抱拥她的那男人并不如想像中粗鄙,他一直关切她感受,连声说对不起,朦胧中她曾看见他胸前胎记,如绽开落梅,她被下了迷药,本该是憎厌不已的事情,却意外地没什么实感,大抵因神智太过模糊,像作了场梦。
当然,不可能喜欢,她没罹患斯德哥尔摩症候群。
当时她仅是很快接受了现实,匆匆离去,药物残留使她恍惚,加上种种打击使她脑中一片空白,当下只想洗净身体抛开一切大睡一场,压根儿忘了保留证据。等她终于平复情绪,吃了事后药,也做了性病相关检查,思前想后,决定把此事抛诸脑后,放弃深想。
他们底层人家,没有伤春悲秋哭天喊地的余力,隔日照样得上班赚钱,辛苦持家。那是唐家的家宴,来往仅有唐家人,不是她对付得起的人物,何况她的工作还得靠他们照拂。
很现实?很不堪?对,但这就是小老百姓的无奈。
若她仅一个人,那或然倾家荡产亦要讨个公道,问题她还有个甫成年的弟弟要照顾,她甚至不希望他知晓这件事。
结果不知哪儿来的蒙古药,孩子顽强留了下来,想想她一介平凡人怀着千金种,不禁有些苦中作乐,笑了出来。
笑着笑着,她笑出泪来,哽咽着抹去。
于情于理,她都该拿掉孩子。
可医生说此次手术,她未来或许不能再怀,她就有点儿犹豫。
她一直希望生两个,若弟弟愿意,就过继一个给他添伴,令苏家香火得以延续──她弟弟是Gay,这辈子没有与女性结婚成家的可能。
她坐在公车站,发了很久的呆。
没什么人生跑马灯,就是发呆。
她觉得生活里有些事,想得越清楚,越踟蹰,远不如别想。她这回搭上公车,回到家里,苏砌恒──她弟弟晓得她今日去医院,本欲作陪,却被苏祈梦挡下:“医院阴气重,少去为好。”何况他们家跟医院,太有缘了,想想就讨厌。
他听闻动静慌忙自房间走出,十八岁青春秀致的脸上满是担忧:“姊,怎样了?”
“边吃边说吧。”苏祈梦倒平静,进厨房发现弟弟熬了一锅鸡汤,尝了一口,不禁笑着捏捏弟弟脸皮:“不错啊,越发贤慧了,谁娶你谁有福。”
苏砌恒脸红了红,呐呐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