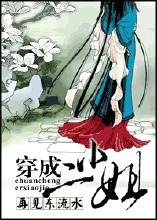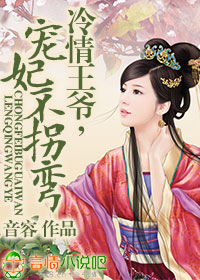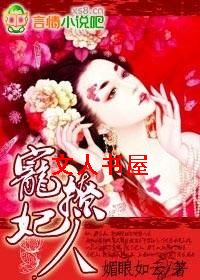穿成宠妃之子-第11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争这先后做什么,大家就不能一起来么?”梅子聆非常郁闷,他是这里面唯一一个既不在行知堂、也没有考入翰林院,还无从直达天听的那个,气恼道,“你们是欺负就我不能直接找陛下告状是不是,那我还可以找我爹呢,我爹最疼我了……”
“子聆,”梅子博笑着打断自己弟弟,“你没有听明白你书俞哥方才的意思么?这件事,如果殿下想私下告状,找陛下找太子殿下,都比找你我的强……之所以大费周章地先来找我们,重点在于威慑。”
“还是书俞兄请吧,”梅子博笑着道,“这桩公案之后,您就是朝野闻名、铁板钉钉的殿下的人了……我可不敢跟您争这个,怕累得您再少讨了一副画,回头再骂上了我。”
“不过,”梅子博含蓄笑道,“我娶妻秦氏,妻子娘家行十六,她的长姊,其丈夫,如今正任刑部右侍郎……愿为殿下引荐。”
第98章 不公 高下立现。
元夕过后; 官府开印,百姓复工。
只先前懒洋洋的气氛好像还并没随着逝去的佳节一并溜走,朝臣或多或少都带了些未尽的懒散情绪; 只预备按部就班地去上朝点卯……然而两件事的接连出现; 直接燃尽了所有人残留的懈怠情绪。
一是直到年后上朝,大多数臣子才将将得知——帝御小北园,遇险惊马; 负伤静养; 着太子暂代、总理朝堂一切事务; 非加急者不必报呈御前。
也就是说,年后大臣们上了朝,才发现皇帝没了; 出来主持的人是将将要加冠成人的东宫太子。
这下大家都好奇了起来,一时之间; 关于真宗皇帝在小北园究竟是怎么受的伤、伤得又有多重的流言五花八门,甚嚣尘上……群臣私下里讨论得热火朝天; 什么奇怪奇葩的说法都冒了出来。
裴无洙只偶尔听了一耳朵,心里都不由感慨莫名,一时只余一个想法,:古人之想象力……真是无穷无尽,古怪离奇。
不过第一桩尚好平定,毕竟,东宫太子此番并不是第一次奉旨监国。
虽然真宗皇帝人不至; 但有东宫太子在场; 还是能轻易从容地将朝中一切常规事务处理得妥妥当当、井井有条。
几天之后,体验到了太子监国那有过之而不及的压力后,众臣便已经对真宗皇帝遇险负伤、迁于小北园静养的态度反应趋之于平静了。
而就在这之后没多久; 第二个足以使得不少人听了之后立马“热血上头”的事情,马上就曝了出来。
——行知堂柳书俞上疏,参五年前进士及第的湖广籍士子、现外放任岳州府平江县县令的简宁陵徇私舞弊、德行不端,并附上了其曾经在科举考场上串通考务、指使他人代为答卷的所有人证、物证。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科举制绵延至今,早已成了天底下所有读书人心中一块不容丝毫玷染的圣地。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的诗词广为流传,吸引不少学子“老死于文场而无所恨*”,其中思想,早已深植于每一个士子,尤其是每一个出身普通甚至于贫寒、老老实实读书治学,一心只想着能依靠科举这一条通天青云路,一朝金榜题名、蟾宫折桂,能鱼跃龙门的读书人心中。
——旁杂世俗事上的出身高低烦扰也便罢了,世家与寒门间古来有之的不可磨灭的沟壑矛盾也罢了……但如果连心目中最后的一块净土,寒门士子唯一往上爬的通天青云梯,都那么被人大肆咧咧地轻易侵蚀污染了,难免激惹起他们心头的所有不平事,引得人愤郁难言。
如果行知堂行走柳书俞奏疏中的所参所列句句属实,那无异于狠狠地朝天下所有读书人的脸上打了一巴掌,直接讽刺嘲笑他们:你们十年寒窗苦读,又能算得了什么呢?
比不得人家投个好胎,有个好爹,直接高高在上地找个人替了……纵然是再学得十全文武艺,你也货不了帝王家!
他们读了这么些年的孔孟之学,学的是忠君报国,忠得是君,可那简宁陵又是个什么东西?他们满腔热血,也不是为这些名为世家的社稷蛀虫流的!
为了要赶上半年前的承乾宫选妃宴,简叔平与临安长公主一家专程回洛,虽然简琦玉人并没有被选上,但因为又正好逢吏部三年一考评,为简叔平计,他们一家又多在洛阳停留了些时日。
是而,柳书俞当朝上疏时,简叔平人尚在洛阳。
当时心里便咯噔一声,知道事情要坏。
简叔平清楚其中利害,加急写信,一一道明,禀于自家时任湖广布政使的父亲简隆。
令作一份,送至身在平江县的侄子简宁陵手中,敦促其早作准备,最好能将手头事暂时搁置,备齐自证清白之辞,尽早入洛当面陈情。
但事情从这里开始,就已经来不及了。
——或者说,早在裴无洙通过东宫太子之手,将五年前那桩舞弊案查了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并抢先逮住了重要人证杨石戴开始,简家就已经立于必败之地,败无可败了。
简叔平的反应不可谓之不快了,但即便如此,对于身在湖广的简隆而言,与简叔平的书信一起送到手的,还有已经沸沸扬扬地从北传南、缠在简宁陵身上洗不清的舞弊流言。
这一回,南北士子空前一致,朝野内外,凡敢出声者,必奔走高呼:愿万死以请彻查此案。
而消息之所以能从洛阳出去、流传得如此之广之快,真宗皇帝暧昧含糊、按下不表的态度要占很大一部分的原因。
东宫太子在收到柳书俞奏疏的第一时间,当日没有安排人代为转送,而是专程走了一趟小北园,禀明常规政务后,专而重之地将柳书俞的奏疏亲手奉到了真宗皇帝面前。
真宗皇帝看罢,半晌无言。
他不傻,前脚临安长公主给他送了个徐简氏过来,后脚简家子侄就出了事。
真宗皇帝多少有点不痛快,隐隐有种“太子大了,连朕要宠幸哪个女人都要插手管教一番么?”的不悦。
再想想之前东宫太子与孙氏那半道没走下去的婚事,当时太子不愿娶,真宗皇帝随了他;太子允孙氏别嫁,真宗皇帝也顺了他的心意。
乃至于后面直到现在,东宫太子都绝口不提自己再娶太子妃之事……真宗皇帝念他先前不顺,想着心有郁结也是正当,也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默许了。
如今二者对调,他这做老子的要幸哪一个女人,反还得轮到去看当儿子的脸色了?
真宗皇帝心里不爽,就把柳书俞的奏疏按了下去,暂时不想管。
谁能想到,这一个“不管”不要紧……如果当时当刻真宗皇帝的第一反应就是让人去查,可能后面还不至于拖到群情激奋、万人请命的地步。
自古以来,哪种东西最容易吸引人的兴趣?自然是上位者不想让你知道,你却偏偏已经知道了的事情。
所以古来闲书只要一被官府列为“禁书”,身家立刻翻倍狂涨,知名度在暗里大肆飙升。
在柳书俞参简宁陵这件事上,真宗皇帝就因为一时身心不愉,犯下了这个最后险些足以拖死所有简家人的错误。
柳书俞上奏当天,群臣震惊。
——资历老些、原先曾有所耳闻的还好,隐约能猜得到这是有人想对简家动手了……拿简宁陵的舞弊案做筏子,也是他们简家人夜路走多了撞上鬼,活该的。
但尚且年轻的那一批,却是立时错愕难言,震惊失语。
继而便是愤然挟怒。
柳书俞上奏第二天,所有人都在等着真宗皇帝的批示。
但真宗皇帝却并没有任何的反应,就仿佛压根没有听到过这件事一样。
——既不说要查,但却也没有丝毫勒令任何人严禁闲谈此事的意思……这就使得不少人的心思一下子莫名浮动起来了。
柳书俞上奏的第三天,一切如故。
其时已经有太学士子开始自发地聚集成群,到洛阳皇城的宫门外请命了。
甚至还有热血上头、读过两年书的地方游侠,气势冲冲地跑去拦柳书俞的轿子,直言自己愿誓死保护敢于“为天下士子言不可言之事”的柳大人……闹得柳书俞哭笑不得,连上朝下衙都得躲躲藏藏与人打游击战了。
而东宫太子瞧出了真宗皇帝当日神色间的不悦,这一回没有亲自过去,只暗示人将这些都一五一十地禀与了真宗皇帝。
真宗皇帝却并没有把这些当回事……毕竟,那只是一些太学的学生罢了。
学生,年纪轻容易冲动容易受人指使,动不动就要上来搞撞柱而死、为民请命的那一套……但真要让他们做些什么,却又是“书生造反、三年不成”了。
真宗皇帝确实是打心眼里不觉得这是多大点事。
——或者说,在他看来,问题的关键从不在简宁陵究竟有没有作弊、而科举舞弊这件事又到底有多恶劣上。
而是他现在身为一个皇帝,想要宠幸一个来历不明的女人,他儿子不高兴了,他这当老子的威风还立不立得起来了。
所以柳书俞上奏后的第四天、第五天……真宗皇帝对此事都从没有任何正面正当的批示反应,只做一切无事发生,全都照旧。
第六天的时候,洛阳一名久试不第的举子孤身上街,敲响了洛阳宫城外已经形同虚设多年的“鸣冤鼓”。
守门士兵惯常过去动手驱逐,那举子一时愤然,当众高喊一句:“余平生所恨,不公、不公、不公!”
然后一头撞死在了宫门城柱上。
东宫太子带着臣属赶到时,只来得及远远听到那举子口中最后喊得仿佛想要去震彻云霄的那个“不公”……拦都没有来得及去拦,就眼睁睁地看着人撞死在了身前。
当日下午,所有从宫城门外大街上走过、被鸣冤鼓吸引来的臣子百姓,都亲眼看见,东宫太子一掀下摆,跪倒在了那举子的撞得头破血流的尸首面前。
不在意袖间污染,亲手将人的眼睛一点一点合上,以一国储君之尊,亲手收敛了那举子的尸身。
群臣百姓随之齐跪,心中所思所想,无可明与外人道也。
事情到这一步,却是再也按不下去,一下子完全炸开锅了 。
是而,简叔平寄与湖广的家书还在路上时,简宁陵舞弊案的消息已经长了翅膀一般,飞快地从洛阳往大庄四境之内流传开来……跑得可比什么书信都快多了。
事到如今,就连裴无洙也愣住了。
——她是万万也没有想到,此案被真宗皇帝几番故意拖延,最后竟然还牵连了一条完全无辜之人的性命进去,结出了一个如此扭曲的苦果。
而随着那洛阳举子之死,以及他死前对天大喊的那三声“不公”……舆论哗然,发酵至此,原先在朝中保持缄默的几位重臣阁老也坐不住了,私下里互相各自讨论了一番后,不约而同地找到了小北园,齐劝真宗皇帝速速下旨彻查此案。
群臣走后,梁任单独留下,更是直言不讳地与真宗皇帝明言了。
“陛下若是想保简宁陵,更应该第一时间让人去查,查了才能去疑去嫌,才能钉死是柳书俞诬告诬陷,”梁任言辞恳切道,“而不是拖延到如今,人死灯灭……如若再不及时补救,于陛下的威严,却是难免会有些亏损。”
梁任没有敢说出口的是:事已至此,真宗皇帝在百姓臣子心中丢了的那份威严,被东宫太子当日当众那一跪……此消彼显,高下立现。
真宗皇帝也意识到事情闹大了,心里烦躁得很,叩了叩案几,心神不定道:“简宁陵、柳书俞……这个柳书俞不是行知堂的么?他闲得没事干去参那简家人作什么?”
梁任微微在心里叹了一口气,小心翼翼地提醒真宗皇帝道:“那柳书俞性情孤高,颇为醉心画道……听闻近来,非常喜爱五殿下的画。”
真宗皇帝听得愣住了。
——他一开始被惯性思维误导,以为柳书俞弹劾简宁陵是东宫太子的意思。
因为这件事在真宗皇帝看来,重点不在于是谁弹劾的,而是弹劾的是谁……换言之,东宫太子抛了哪一个人出来作马前卒,真宗皇帝都懒得去一一记下。
行知堂与翰林院每年走马观花地送走一批又一批的青年新秀,同时又不停歇地大量补充新鲜血液……那本就是设来给帝王作参谋智囊、以广博为著而裨补缺漏的地方,行知堂里一个小小的行走,真宗皇帝哪里能看在眼里、记到心上?
真宗皇帝先前一直关注的重点,是东宫太子亲手给他呈了一封参人的奏疏来,而其中所参奏的,正是刚刚给自己送了徐简氏的临安长公主的侄子。
——真宗皇帝是一个习惯以个人喜好来随意任免留用的人,以己度人,想当然地就把这件事的重点放小了,只当是父子俩之间互相别着劲置闲气呢。
如今事情闹大,眼看着不再好收场了,如梁任所提,简宁陵和柳书俞两个人里,真宗皇帝肯定是要杀一个、保一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