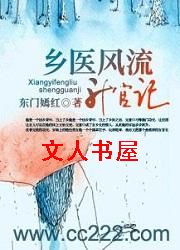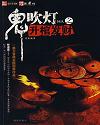升官发财在宋朝-第14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词赋中规中矩,挑不出什么差错来,但这两篇文论……
怎么透着股似曾相识的熟悉感?
陆辞乍一眼看去,因有些久远,于是只被唤起了模糊印象,顶多是感到有些微妙。
但在仔细读过几遍后,他就顺利在脑海中调出具体记忆,也肯定了第一眼时浮现的猜测。
陆辞不由失笑一声,摇了摇头,直接翻至行卷卷首,慢条斯理地将名姓记下,再起身到存放举人家状的小室中。
不过片刻,他就在吏人的帮助下,调取出了这人的家状。
行卷弊端丛生,已非新闻。但其最大诟病,便是常有人假借他人文字,或用旧卷装饰,重新书写,而起不到反应举子平时水平的作用。
哪怕是最简单的剽窃,因没有后世的网络查询,也不存在能阅遍天下人作品的神人存在,想要发现这点,也是难如登天的。
这位胆大包天的老铁,却是倒霉到家了。
——他恐怕还不知道,自己不但抄到了监试官的旧作头上,还刚巧被心血来潮做抽查的监试官发现了。
作者有话要说: 注释:
不好意思,我重新查阅了关于开封府解试的资料。发现宋初虽然跟诸路州府监军一样,也是从府官中抽调人选充当考试官,但是从988年开始,就因‘府事繁巨,始别敕朝臣主之。’一般是从馆阁中抽调人选,譬如直集贤院、直史官、太常丞、秘阁集贤校理、同修起居注、殿中侍御史等人,来考试开封府举人。
别头试的考官和监门官,就如文中所说的那般,也是从这些人中另外设置的。一般是两到三人。
但因为V章太难修改,我就只在这里知会你们一声这是BUG QAQ就不改前面的了。《中国科举制度通史…宋代卷上》p194 第四节 的开封府解试
第一百五十八章
陆辞还真料错了一点。
那就是铸下这一大错的那名倒霉举子李钧,非但已意识到了,当场被吓了个半死,整天还在家中惶惶不可终日。
从五月礼部颁布贡举诏书,到七月初各州府收纳行卷和登记家状,再到七月中旬落实考试官的具体名单、将人送入锁院之间,可是有段不长不短的时间差的。
李家人唯恐误事,在得到差官们已开始收纳家状、保状、公卷和试纸后,就立马催促李钧,让他早些将东西送去了。
因家人催得厉害,正愁公卷该选用哪篇旧作为好的李钧,愈发感到压力深重,让他难以喘过气来。
就在发愁时,他忽地就看向了桌面上,那被自己从一家小破书坊买来的一本自印盗刊。
据闻是密州泄出的原稿,为三年前一鸣惊人,未及冠便三元及第的那位文曲星在学院读书时,留下的一些作品。
陆辞极擅文论,篇篇读来皆是酣畅淋漓,感受得出笔者的挥洒自若,斐然文采。
相比之下,哪怕绞尽脑汁,都难选出几篇出彩作充当公卷的自己,就更显得一无是处了。
李钧目光微凝,鬼使神差地将已快翻烂了的书册拿起,心神不属地翻开几页后,内心满是挣扎。
横竖最后去留,还是由试时程文所定,行卷并不起评定艺业的作用,甚至都不见得会被考官过目。
在胡乱想了一通,李钧心里的那点挣扎和罪恶感,也就降至微乎其微了。
哪怕是陆辞本人看,也不见得就能记住自己的每篇旧作,更遑论是对其并不熟稔的其他考官?
若真被考试官看到了,那陆辞的文采,可是世人皆知的优异,绝对比呈上他那不堪入目的旧作要好。
那何不借那文曲星的文论一用?
动了这歪心思的李钧,却做梦都想不到,三年前还在贡院中奋笔疾书的陆文曲星,今年竟就摇身一变,成了开封府的监试官了。
当得知考试官名讳时,他还在赴一场雅集的路上。
听到陆辞被委任作监试官时,他脸色瞬间变得惨白,浑身如坠冰窟的寒冷。
这怎么可能!
雅集自是没心思去了,李钧心神大乱地回了家,反复找人确定过这消息无误后,就开始慌慌张张地在家中踱步。
完了,他要完了。
此后的日子里,他根本看不进书,也不愿见对此回贡举踌躇满志的同窗好友们,终日在东窗事发的恐惧中,犹如一个游魂。
李母和下人们都以为他只是初次下场,感到紧张忧惧,自是万分体贴,命人送多滋补羹汤,又软言劝慰,丝毫不知李钧内心煎熬。
还是阅历丰富的李父见他这失魂落魄的模样,很不寻常,不由起了疑心,特意将人召来书房,私下询问。
李钧本就濒临崩溃,尤其知这事后果极为眼中,之前一直不敢言,但在爹爹和颜悦色的询问下,一下就跟揪住救命稻草一般,把自己犯的大错一五一十地说了。
得知儿子一时糊涂,竟犯下这等荒唐的错后,李父眼前一黑,差点晕倒在地。
还好被李钧及时扶住,李父粗喘了好几口气,才缓了一缓,却恨不得昏过去算了,哆哆嗦嗦道:“逆子!这么多年的书,你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你怎么就这么鬼迷心窍啊!”
也真是太倒霉了!
李钧原还抱着些微侥幸,才和盘托出,不料爹爹都如此反应,更觉绝望,泪如雨下地瘫软在地,不住磕头。
李父抚着胸口,站稳之后,还是气不过,又将他劈头盖脸地骂了一顿。
之后,他虽无可奈何,还是不能放下不管。
谁让自己年过半百,却只得这么一根独苗呢?
若只是为一份原本无关痛痒的行卷,就被打上抄袭舞弊、还不幸抄的是当届监试官的旧作的污名,何其不值!
这一罪名真落实下来,因攘窃和代笔历来被视作科举至害,处罚也最为严苛。
就他所知的,上一位这么做的人,可是被罚铜之后,还编配到千里之外的州军去了!
哪怕那人是因在省试中寻人代笔,处罚才从重考虑,李钧的仅是公卷,不至于到充军程度,但殿举罚铜,却是绝无可能避免的。
李钧更必然将因这一大乌龙事件,而沦为笑柄,日后信心尽毁。
即使在耽误上十数年后再考,侥幸中了,也不可能过得去殿试那关,再无仕途可言。
这却太不公平了。
在行卷上做手脚的大有人在,假借他人文字者更是不计其数。
真要查,凭什么只查他家大郎?
不就是运气太过不佳,攘窃别人之作时,不巧就攘窃到了监试官头上么?
而陆辞的资历也好,德望也罢,甚至年岁,又有哪样符合担任考试举人的解试监试官该有的模样了?
本就是他趁了曾为东宫官的便宜,又搭乘了太子监国的东风,才得以这般得意的。
在朝堂中,李父与陆辞虽打过照面,但因他官阶比陆辞还低上两阶,加上职务上并无交集,是以敌意不大。
现大郎前程将毁,就因一时错乱,抄了此人旧作后,那股一直被压抑的怨气,就一下窜上来了。
他越想越是心寒胆战,遂下定决心,要将这事妥善善后,竭尽所能地瞒过去。
至于要如何瞒住……
尽管因开封府赴解举人众多、行卷多至上万,他大郎那一份不见得会有被考试官们过目的机会,且会被身为监试官的陆辞碰上的可能性,更是微乎其微。
但为保险起见,还是当设想好最坏的事态。
李父沉吟许久,当即让六神无主的李钧将近些年的手稿一概销毁,这剩下的半个多月中,也别再复习课业了,而将原手稿上的语句,用截然不同的字体,再抄录一次。
李钧死命点头。
哪怕临时练出一种新的字体极不容易,但与他前程相比,就完全算不得什么了。
对爹爹让他如此做的用意,他也能猜出来:这要能顺利的话,当人上门来核查时,他大可拿出不同字迹的诸多旧稿来自证自辩,以此证明那份行卷,并非出自李钧之手。
当然,这法子还算不上完美无缺:若不是李钧做的,又会是谁?
罪魁祸首一天不找到,大理寺丞就会四处排查走访,非要查个水落石出不可。
若是问到熟悉李钧字迹的其他友人头上,可不就得穿帮露馅了。
李父清楚,还得再找个可靠的人,做这名替罪羔羊。
于是又想方设法寻来一人——那还是他一位从商的友人家的郎君,虽有资格参加贡举,却无心仕途。
他忍痛割肉,付出一大笔钱财,才说服对方肯在最坏的情况下,认下‘冒名参举’的准备。
最后,李父还让李钧将与他同保的那三人寻来府上,轮番威逼利诱,串好口供了。
同保那三人固然震惊,但在李父言明利弊后,也清楚此事一旦暴露,他们作为同保人,哪怕自称不知情,少说也要被连累着殿上两举。
最后拿着李父给予的钱财补偿,才不得不捏着鼻子应下了。
就在李父将一切准备得完美无缺后,就开始在供奉天书的道观中祈福,盼着陆辞根本不会发现李钧的剽窃行径。
但希望还是落空了。
当转运司和提点刑狱司的吏员上门时,一直祈祷着这天不要到来的李父就紧绷了神经。
尽管如此,他面上却只流露出恰到好处的震惊,任人闯入了儿子李钧的书房进行搜查……
显然监司的人不曾料到,这家人会是有备而来。
在将李钧书房里的手稿收缴一空后,他们就先回去了。
由于这回是太子监国以来,主持的第一次贡举,上下对此都极为重视,现闹出开封府一举子公然舞弊,还剽窃到了监试官头上的戏剧来,自然惹人注目得很,连太子殿下都频频亲自过问。
往常要拖拉个十几天才派人着手的案子,次日就出了查验结果了。
——从李钧家中搜出的手稿字迹,与呈上的家状、公卷字迹,并不符合。
陆辞得知这一结果时,监司的人员已顺着李父事前布下的陷阱,朝错误的方向继续侦查去了。
“完全不符?”
陆辞蹙了蹙眉。
他的头个念头,便是这其中存有猫腻。
一是李钧的公卷送来的时间:那可是在太子下达诏令,任命他为监试官之前。
若是有心人的刻意陷害,那人又是如何比心血来潮的太子还早一步得知,他会是这场开封府解试的监试官的?
况且即使他是监试官,也不见得就会凑巧地翻阅到李钧的行卷,从而认出自己的旧作。
真要害人,也不该挑选这一时机。
二是,若李钧是被人冒了名,那他本人的家状和公卷呢?怎么不曾见到?
三则是,若此人真有意害李钧,又怎么会手段那般拙劣,用与正主截然不同的字体来陷害,而不稍微模仿一下呢?岂不是等着被人一眼看穿么?
……
他只粗略一琢磨,就察觉出无数疑点来,以至于这鲜明的证据摆在眼前后,反倒透着股欲盖弥彰的味道。
陆辞沉吟一阵,忽唤来吏人:“还请你跑去监司一趟,询问是否能将李钧书房中搜来的手稿,暂借一份予我一观?一日后我必将归还,定不会叫他们为难。”
不论是手稿的新旧,还是运笔的力道、笔划的角度等细节鉴定上,都可能会被匆忙查验的监司所忽略。
若李钧当真是被人害了,那他私下里做的调查,也只会在对方得还清白时,帮上一把。
若他怀疑不岔,真有人处心积虑,欲要瞒天过海的话……
陆辞莞尔。
那他可就能给将自己硬安排进这锁院里来的小太子,找点事情做了。
作者有话要说: 注释:
1。关于代笔之弊的惩罚,可参考985年的诏令:“如有倩人撰述文字应举者,许人告言,送本处色役,用不得仕进;同保人知者殿四举,不知者殿两举;受情者,在官停任,选人殿三举。”《中国科举制度通史·宋代卷上》第七章 p355
2。监司:即转运司,提点刑狱司,他们互相监察。
第一百五十九章
陆辞作为首个察觉,且及时上报了这桩舞弊案的监试官,话语还是颇有份量的。
虽有些不合规矩,监司的人还是爽快应承了他所派吏员提出的请求,将从书房搜来的李钧手稿一概借予陆辞一观。
接着,就继续去审问那顺藤摸瓜查出的陷害李钧之人了。
陆辞虽只知晓些字迹鉴定的皮毛,但在顺着笔画逐一划线,对比倾斜角度,再仔细观察过运笔的力道,所用墨砚和笔的质地,以及收笔时特有的回勾的习惯后,很快就确定了先前的猜测。
——尽管一眼看去,字体形态有异,但经过认真比对,不论笔墨材质也好,还是运笔的特点也罢,都绝对出自同一人之手。
只是陆辞也清楚,他所用的鉴定字迹的方法,与监司官员所采取的截然不同,要想说服后者,显然难如登天。
单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