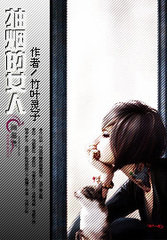恋爱中的女人-第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古迪兰对他羡慕得感到心痛。尽管这种与世隔绝的状况和对水的世界的占有只是短暂的时间,她也是那样的向往。她站在公路上,就感觉到自己像被打入了地狱!
“天啊,做个男人该多好啊!”她叫道。
“什么?”欧秀拉惊讶地问道。
“自由自在、为所欲为!”古迪兰大声说,兴奋得脸色红润。“如果你是男人的话,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你就不会有女人所遇到的那些数不清的麻烦和障碍。”
欧秀拉不明白在古迪兰的脑子里都在想些什么,竟说出这些话来。她无法理解。
“你想做什么?”她问。
“没什么。”古迪兰赶紧大声表示反对。“只是假设而已。假设我要在这水中游泳吧,可这不可能的。我不可能现在脱了衣服跳入水里,这是不可能的事。可这却是多么不合理啊,简直阻碍了我的生活。”
激动和愤慨使她满脸通红。这让欧秀拉觉得不知所措。
俩姐妹继续在路上走着,她们在肖特兰兹下面的树林中穿过。她们抬头看去,那座狭长低矮的房子在潮润的清晨里显得黯淡而有魅力。有几棵雪松树就斜斜地掩映在它的窗前。古迪兰似乎在认真地琢磨着这幅图景。
“你不觉得它很迷人吗?欧秀拉。”古迪兰问。
“非常吸引人。”欧秀拉说,“幽静迷人极了。”
“有很有风格,而且也有年代了。”
“什么年代?”
“是18世纪。确切地说,多萝茜·华兹华斯①和简·奥斯汀的年代!不是吗?”
①朵拉茜·华滋华斯(1771—1855),女批评家,威廉·华滋华斯的妹妹。
欧秀拉笑了。
“难道不是吗?”古迪兰说。
“可能吧。不过我觉得克里奇家的人跟那个时期不般配。我知道克瑞奇正在建一个电厂,为了给房屋照明。他正在进行最时髦的改造。”
古迪兰迅速地耸了耸肩。
“当然,”她说,“那是不可避免的。”
“绝对的。”欧秀拉笑道。“他总是一下子就做了几代人的事。人们因此都恨他。他总是强拎着别人的脖领子,牵着他们走。等他把一切能改进的都改进好,没有什么其它事可做了的时候,他就会活不下去了。当然,无论如何,他应该这么做。”
“当然,他应该这样。”古迪兰说,“说实在的,我还没见过一个男人像他这样有干劲。可惜的是他的干劲花哪儿了,结果又怎样呢?”
“噢,我知道,”欧秀拉说,“花在最先进的机器上去了。”
“就是。”古迪兰说。
“你知道他杀死了他的弟弟吗?”欧秀拉问。
“杀死他弟弟?”古迪兰叫道,好像难以置信。
“你还不知道吗?哦,是这样!我还以为你知道呢。他和弟弟一起玩一支枪,他让弟弟看着子弹上了膛的枪管,他开枪了,结果他弟弟的头被打开了花。多么可怕,是吧?”
“多可怕啊!”古迪兰喊道,“那是很久以前的事吧?”
“哦,是啊,他们还是孩子的时候。”欧秀拉说,“这是我知道的最可怕的故事。”
“不过,他并不知道枪里上了子弹,是吧?”
“是啊,那是一支在马厩里放了很久的老枪了。没人会想到枪会走火,更没人想象得到枪里还有子弹。这件事还是发生了,真是可怕。”
“可怕极了。”古迪兰叫道,“小时候发生的事,却要让人内疚一辈子。想想这事儿,两个孩子在一起玩耍——然后,这种灾难就莫名其妙地降临了——真是祸从天降。欧秀拉,这太可怕了!哦!这让我所无法承受。要是谋杀倒可以理解的,因为在它的背后有一定的动机。但这种事发生在某个人身上——”
“说不定在它背后也有一种藏在潜意识里的动机。”欧秀拉说,“这虽出于无意,但其中或许隐藏着一种原始的杀人欲望,你说呢?”
“欲望?”古迪兰以冷冷、生硬的口气说,“我觉得这连玩杀人游戏都算不上。我猜想是一个男孩对另一个男孩说,‘你看着枪管,我来扣扳机,看是怎么一回事。’我觉得这纯属偶然事故。”
“不,”欧秀拉说,“我是不会去扣扳机的,即使是枪中没有子弹,更不必说是还有人在往枪管里看了。凭直觉人们就不会去做的。——也不可能这么做。”
古迪兰沉默了一会儿,但心里十分不服气。
“当然,”她冷冷地说,“如果是个女人,并且已经成年,她的直觉会阻止她这么做。但这和两个小男孩在一起玩耍并不相同。”
她的声音冷漠而有些恼怒。
“是一样的。”欧秀拉坚持说。这时,她们听到一个女子在远处高喊:
“哦,该死!”她们走上前去,看到劳拉·克瑞奇和赫曼尼·罗迪斯正在篱笆那边的田地里。劳拉·克瑞奇正在努力想从门里出来。欧秀拉赶快上前帮她拉开了门。
“太感谢了。”劳拉说,满脸通红得象个悍妇,困惑地说,“门的铰链有问题。”
“是的,”欧秀拉说,“而且门也很沉。”
“你们好啊!”赫曼尼一边从田地里出来,一边唱歌似的打招呼,“天儿真好,你们来散步吗?是啊,这些嫩绿的叶子真是太美了——美极了!早上好——早上好,你们会来看我吗?十分感激——下星期,好,再见,再——见。”
古迪兰和欧秀拉站着,看她缓缓点头,缓缓地向她们挥手道别。她的微笑奇怪而做作。她那高大的身躯、古怪的样子,以及滑到眉际的浓密的头发,看着让人害怕。于是,姐妹俩就像卑贱的下属被人打发走了一样离开了,四个女人就此分手。
她们走出一段后,欧秀拉红着脸说:
“我觉得她太没礼貌了。”
“谁?赫曼尼·罗迪斯吗?”古迪兰问,“为什么?”
“她待人的态度毫无礼貌。”
“怎么了,欧秀拉,她哪里傲慢无礼了?”古迪兰平淡地说。
“她的全部举止——哼,她待人的态度简直让人难以忍受,纯粹是欺负人。一个傲慢无礼的女人,‘你们会来看我’,好像我们巴不得抢得这份恩赐似的。”
“我不明白,欧秀拉,你为什么这么生气”,古迪兰有些恼怒地说道,“人们都知道这些女人都是傲慢无礼的——这些从贵族的繁文缛节下逃离出来的自由女性。”
“可这完全没有必要了,庸俗!”欧秀拉嚷道。
“不,我并没有看出来。即使我发现了这一点,那么她对我而言也是微不足道的。我可不能让她对我傲慢无礼!”
“你觉得她喜欢你吗?”欧秀拉问。
“嗯,不,我可不这么认为。”
“那她为什么让你去布雷多利做客?”
古迪兰微微耸了耸肩。
“毕竟她也觉得我们不是普通人。”古迪兰说。“无论如何,她并不傻。而且,我宁愿去和那些我不喜欢的女人交往,也不愿意和哪些保守平庸的女人来往。从某些方面讲,赫曼尼·罗迪斯是敢于冒险的。”
欧秀拉对她的话回味了一会儿。
“我对此很怀疑。”她回答道,“其实她根本没有冒什么险。我认为她竟能请我们这些教员去作客,这点倒值得我们敬佩。但她这样做并不是什么冒险的做法。”
“太对了。”古迪兰说,“想想看,很多女人都不敢这么做。她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自己的地位,我想。实际上,如果我们在她的位置上,我们也会这么做。”
“不,”欧秀拉说,“不,那会让我感到厌烦。我才不会浪费时间去做她那种游戏,那太有失身份了。”
两姐妹就像一把剪刀,把碰到的每件事都剪得粉碎;或者像一把刀子和一块磨石,一个把另一个磨得锋利。
“当然,”欧秀拉突然大声说,“如果我们去访问她,那是她的福分。你是这样美丽绝伦,比她任何时候都漂亮千百倍,而且据我看,你穿得也比她漂亮好多倍。她看起来毫无新鲜感、不自然,像一朵要凋谢的花朵,那么老气横秋。而且,我们比大多数人都要聪明得多
。”
“一点不错。”古迪兰说。
“这是明摆的事实。”欧秀拉说。
“当然是。”古迪兰说,“不过,真正的优雅应该是绝对普通、绝对平凡的,就像街上的一个行人,那样你才是人类的一个真正的杰作。当然,并非真的变成大街上的一个行人,而是艺术创造中的人。”
“没错,”欧秀拉说。
“是的,欧秀拉,没有人能够超脱凡尘。”
古迪兰涨红了脸,并为自己的聪明见解而感到激动。
“趾高气扬,”欧秀拉说,“人人都想趾高气扬地,就像一只天鹅站在鹅群里。”
“没错,”古迪兰大声说,“鹤立鸡群。”
“可他们都在忙着扮演丑小鸭的角色,”欧秀拉嘲笑着说,“可我一点也不觉得自己是一只谦卑、可怜的丑小鸭,我觉得自己是鹅群中的天鹅。我情不自禁这么想,我并不在意别人怎么看我,我不在乎。”
古迪兰抬头看她,一脸古怪,说不清是羡慕还是厌恶。
“当然,惟一的办法就是不理睬他们,鄙视他们。”她说。
姐妹俩又回到家中,看书、闲谈、干活,等待着星期一的工作。欧秀拉经常感到疑惑,除了每个假日的开始和结束,自己还能等待些别的什么。这就是全部的生活啊!有时,当她觉得生命中没有更多的东西,就将这样被消磨掉时,她就感到极度的恐慌。但她从来也不愿意接受现状。她的精神是积极的,她的生命就像不断成长的幼苗,只不过还没有破土而出。
第五章 火车上
每年这个时候,伯基都要去趟伦敦。他没有什么固定住处,他在诺丁汉有住所,因为他主要在那个城市工作,不过他也经常在伦敦和牛津。他经常迁动,他的生活似乎飘忽不定,没有任何固定的节奏和计划。
在火车站的月台上,他看见了杰拉德·克瑞奇,他正在读报纸,很显然他也在等火车。伯基只是远远地站在人群里,他天生不喜欢去接近人。
杰拉德时不时地抬头四处张望,这是他的习惯。尽管他在认真地读报,但却很注意周围发生的事情,他头脑中似乎具有一种双重意识,能一边认真思考报上看到的新闻,同时又扫视盯着周围的世界,什么也逃不出他的眼睛。伯基注视着他,对他这种双重意识感到恼恨。杰拉德尽管社交举止异常温,和蔼近人,但他似乎总在防着别人,陷入与人作对的困境。
杰拉德看到了他,脸上马上露出悦色,走过来向他伸出手,杰拉德猛吃一惊。
“你好,鲁伯特,去哪儿?”
“伦敦,你也是吧?”
“是的——”
杰拉德好奇的眼光扫过伯基。
“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一起走。”
“你怎么不坐第一班车?”
“人太挤了。”杰拉德说,“第三班车就好多了,有餐车,我们可以去喝点茶。”
没什么可说的了,两个男人只好都把目光投向车站上的挂钟。
“报纸上说什么了?”伯基问。
杰拉德很快地把目光转向他。
“报上登的这些东西太有趣儿了。”他说,“这是两篇社论,”他拿出手中的《每日电讯报》,“全是些新闻行话——”他扫了一眼社论专栏,“还有这篇文章,我不知道该叫它什么,杂文吧,和社论登在一起,它声称,必须有个人站起来赋予事物以新的价值,给予我们新的真理,给生活以新的态度,否则几年之内,我们将会国破家亡。”
“我觉得这只是报纸上的空话。”伯基说。
“听起来那人很诚恳,跟真的似的。”杰拉德说。
“给我看看。”伯基说着,伸手要报纸。
火车来了。他们上了餐车,找了一个靠窗口的桌子,相对坐下来。伯基浏览一下报纸,抬头看了看杰拉德,杰拉德正在等他发表意见。
“我相信这是他的肺腑之言,相当坦率。”他说。
“你相信吗?你觉得我们真需要一种新的信仰吗?”杰拉德问。
伯基耸了耸肩膀。
“我认为那些标榜所谓新宗教的人,实际上是最难接受新事物的。他们需要的只是新奇。但是,如果不能正视这种我们否定的生活、彻底砸碎自己的偶像,那么接受新事物就只是自欺欺人。要想接受新事物,我们就需要彻底清除旧的东西,甚至旧的自我。”
杰拉德凝视着他。
“你认为我们应该打碎这种生活,同旧生活决裂?”他问。
“这种生活,对,我是这样认为,我们要彻底冲破它,或者令它从内部枯萎,重新生长。这种生活已经在无法发展了。”
在杰拉德的眼中流露出一种奇怪的笑容,神情镇定而好奇。
“那你打算怎样开始呢?我猜你的意思是要改造整个社会秩序吧?”他问。
伯基微皱起眉头,他对这种谈话感到不耐烦了。
“我绝不会提出任何建议的,”他回答说,“要想真的获得新事物,我们就需要砸掉旧东西。否则,任何设想或提议也只不过是些自以为是的人的鬼把戏而已。”
杰拉德眼中的微笑开始消失了,他冷冷地看着伯基说:
“你真把事情看得那么糟吗?”
“糟糕透顶。”
微笑又出现在杰拉德脸上。
“哪些方面呢?”
“所有的方面,”伯基说,“我们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