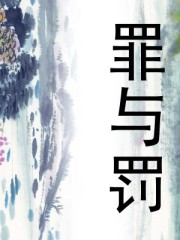规训与惩罚-第4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轻微的无纪律似乎也预示着,你将最终被送上囚犯船;严酷的监狱则向被判处终身监禁的囚犯说,我将记录下你的任何不规矩行为。18世纪的人曾在有关表象与符号的“意识形态”技术中寻求惩罚功能的共相。现在,各种“监狱机制”的复杂、分散但统一的扩展与物质构架,成为这种共相的依托。结果,某种重要的共相贯通了最轻微的不规矩与最严重的犯罪。它不是犯法,不是对共同利益的冒犯,而是对规范的偏离、反常。正是它纠缠着学校、法庭、收容院与监狱。它在意义与功能的领域中统一了“监狱”在策略领域中所统一的东西。社会的敌人取代了君主的对头,同时也被变成一个不正常者,他本身带有捣乱、犯罪与疯癫等多重危险。“监狱网络”通过千丝万缕的联系把惩罚与不正常这两个复杂的长序列联结起来。
2.“监狱”及其广泛的网络允许募用重要“过失犯”。它建立了“规训职业经历”。在这种经历中,经过各种排斥和遗弃后,就启动了一种纯粹的进程。在古典时期,在社会的禁区或空隙开辟出一个浑饨的、受到宽容的、危险的“非法者”领域,至少是逃避权力直接控制者的领域:这个不确定空间对于犯罪来说是一个训练场或避难所。在那里,贫困、失业、逃避无辜迫害,狡猾多诈、反抗权势,无视义务与法律、有组织的犯罪,都因各种缘由汇聚在一起。这是一个冒险领域,吉尔·布拉斯、谢泼德和曼德兰都以各自的方式栖身于此。19世纪的情况则不同:通过规训区分,构建起体系内的严格渠道。这些渠道借助相同的机制,培养驯顺状态,制造过失犯罪。这里有一种连续而强制性的规训“训练”,它有某种教育课程与某种职业网络。从中产生了安全的、可预知的、属于社会生活的职业经历:救济团体、寄宿学徒、劳改农场、训练兵营、监狱、医院、救济院。这些网络早在19世纪初已被规划出来:“我们的慈善机构是一个极其协调的整体,穷人从摇篮到坟墓无时无刻不得到帮助。观察一下不幸者的人生旅程,你会看到,他出生便遭遗弃,被送进育婴堂,然后进入孤儿院,六岁时进入小学,以后又进入少年学校。如果他没有工作能力,他就被列入地区慈善机构的名单,如果他病了,他可以在十二家医院中选择就医。……最后,当这个可怜的巴黎人接近生命的尽头,七家救济院在等待他,它们那有益于健康的制度使他的风烛残年得以延长,超过了富人的寿命”(MoreaudeJonn巨s,转引自Touque)。
“监狱网络”不会把不能消化的人抛进混饨的地狱。它是没有边界的。它用一只手把似乎要被另一只手排除的东西捡回来。它不愿意浪费即便是被它判定为不合格的东西。在这个用监禁把全身武装起来的全景敞视社会中,过失犯并不是在法律之外的,他从一开始就置身于法律之中,置身于法律的核心,至少是置身于各种机制的包围之中。那些机制以不易察觉的方式将个人从纪律转交给法律,从离轨转变为犯法。诚然,监狱是惩罚过失犯罪的,但是,大部分过失犯罪是在监禁中由监禁制造出来的。归根结底,是监狱使这种监禁得以无限延续。监狱仅仅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是那种循序渐进的等级中的一个高级阶梯。过失犯是一种制度产物。因此毫不奇怪,在相当多的案例中,犯人的履历中包括了所有那些被普遍认为旨在使人远离监狱的机制与设施。人们会在其中发现有关估恶不使的过失犯“形象”的标记:被判处苦役的犯人是按照统一的“监狱体系”的作用方向从在教养所度过的童年中精心制造出来的。反之,赞美边缘状态的抒情诗兴则可以在这种“非法者”形象中,在这个游荡在一个驯顺、怯懦的秩序的边缘的庞大社会流民群中找到灵感。然而,犯罪不是在社会的边缘通过连续的放逐而产生的,而恰恰是借助于在愈益强化的监视下的愈益严密的嵌入,通过规训强制的积累而产生的。总之,“监狱群岛”保证了在社会深层基于微妙的非法活动的过失犯罪的形成,过失犯罪与非法活动的迭盖,某种特殊犯罪的确立。
3.但是,“监狱体系”及其远远超出合法监禁的外延的最重要的后果也许是,它成功地使惩罚权力变得自然与正当了,至少人们对刑罚的容忍尺度放宽了。它趋向于消除惩罚实施中代价太大的因素。它是通过使两个领域相互对抗来实现这一点的。这两个领域是法律的司法领域与超法律的规训领域。实际上,贯穿于法律及其判决书的“监狱体系”的宏大连续性,给予规训机制及其所实施的决定与裁决一种合法的认可。在这个包括许多相对独立自主的“局部”机构的网络中,司法模式本身与监狱形式一起广泛扩散,乃至无所不在。规训机构的规章条例可以照搬法律,惩罚方式可以效仿陪审团的裁决与刑事惩罚,监视方式可以遵从警察模式。凌驾于所有这些衍生机构之上的是监狱这种最纯粹的形式。它给了它们某种正式的认可。“监狱”是一个以囚犯船或苦役到各种轻微限制的广泛等级。它传送着某种由法律所肯定的、被司法当作最得心应手的武器的权力。当纪律与在纪律中运作的权力完全运用司法本身的机制时(甚至是为了减轻这些机制的强度),当权力的效果被统一起来,权力被传送到各个层面,从而使它可以避免过分严厉时,纪律与权力的运作怎么可能显得是专断的呢?“监狱”的连续性以及监狱形式的聚变,使得规训权力有可能合法化,或者说,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为规训权力正名。这样就使规训1权力不可能具有任何过分或滥用的因素。
然而,反之,“监狱金字塔”给实施合法惩罚的权力提供了一种背景,在这种背景下它似乎不再具有任何过分与暴力性质。在规训I机构及其所包含的连续“嵌入行动”的精密等级序列中,监狱并不表示另外一种权力的释放,而仅仅表示一种机制的补充强度,而那种机制从最早的合法惩罚形式产生以来就一直在运作着。下述两种机构的差异几乎是(而且应该是)难以察觉的:一种是为了使人悬崖勒马、避免入狱而将人收容进来的最新的“康复”(rehabiltation)机构,另一种是人在犯了明确罪行后被送进去的监狱。这里有一种严格的经济机制。它具有极其谨慎地提供统一的惩罚权力的功效。这里没有任何因素能使人想起君主权力在用自己的权威对即将处死者的受刑肉体进行报复时的那种过分性质。监狱对于那些交付给它的人继续进行着在其它地方已经开始的工作。而这种工作正是整个社会通过无数规训机制对每个人所做的工作。借助于一个“监狱连续统一体”,做出判决的权威渗透进其它所有从事监督、改造、矫正、改良工作的权威机构。甚至可以说,除了过失犯的独一无二的“危险”性质,除了他们偏离正常行为的严重程度以及仪式方面的必要严肃性之外,没有任何东西能把上述权威机构区分开。但是,就其功能而言,惩罚权力实质上与治疗权力或教育权力并无二致。它从它们那里,从它们的较次要的任务中,获得来自下面的认可。但这种认可并非不重要,因为这是对技术与合理性的认可。正如“监狱”使技术性规训权力“合法化”,它也使合法的惩罚权力“自然化”。“监狱”在二者同质化时,消除了其中一个的暴力性与另一个的专横性,减轻了二者都可能引起的反抗后果,从而使二者都不必有多余的目的,并且使同样精心计算的、机械的与谨慎的各种方法得以在二者之间流通。在这种情况下,“监狱”就使伟大的权力“经济”得以贯彻——在18世纪有关人的积聚与有效管理的问题首次出现时,人们曾努力探索这种“经济”的公式。
通过在社会各层面的运作,通过不断地将矫正艺术与惩罚权力混合,“监狱”的普遍性使惩罚之变得自然与可接受的标准降低了。人们经常提出一个问题,在大革命前后,惩罚权利是如何获得一种新基础的?无疑,答案应该在契约理论中寻找。但是,更重要的或许是提出相反的问题:民众是如何被造就得能够接受惩罚权力,更简单地说,民众是如何被造就得能够容忍被惩罚?契约理论仅仅能够用下述虚构来回答这个问题,即合法成员赋予他人以权力,这种权力对他行使他本人所拥有的对他人的权利。但更有可能的情况是,宏大的“监狱连续统一体”造成了规训l权力与法律权力之间的沟通,并且从最轻微的强制不间断地延展到时间最长的刑事拘留,从而建构了与那种胡诌的授权相反的具有直接物质性的技术现实。
4.由于有了这种新的权力经济,作为其基本手段的“监狱体系”就能够促成一种新形式的“法律”的出现:这是一种合法性与自然性、约定俗成与章程的混合,即规范(norm)。这就产生了一系列的后果:司法权力至少是它的功能运作出现内部错位;审判日益困难,似乎人们羞于做出判决;法官方面强烈地希望对正常与非正常进行判断、估量、诊断与辨认,声称有治疗与使人康复的能力。从这一角度看,是否相信法官有良心,甚至无意识的良心,是无意义的。他们“对医学的(无限)偏爱”(这一点不断地表现出来——从对精神病专家的诉诸到对犯罪学的说法的关注)体现了这样一个重大现实,即他们所行使的权力已经“变质”;它在某种层面上是受法律支配的,而在另一个更基本的层面上它是作为一种规范性权力运作的;正是他们行使的权力的机制,而不是他们的顾忌或人道主义的机制,使他们做出邮疗性”判决,提出“使人康复”的监禁期限。但是,反之,即便法官愈益不情愿为判罪而判罪,审判活动也已经扩大到规范权力所扩展的程度。这种审判完全是由于无所不在的规训机制而产生的,是以所有的“监狱机构”为基础的。它已成为我们社会的主要功能之一。对是否正常进行裁决的法官无处不有。我们生活在一个教师一法官、医生一法官、教育家一法官、“社会工作者”一法官的社会里。规范性之无所不在的统治就是以他们为基础的。每个人无论自觉与否都使自己的肉体、姿势、行为、态度、成就听命于它。在现代社会里,“监狱网络”,无论是在严密集中的形式中还是分散的形式中,都有嵌入、分配、监视、观察的体制。这一网络一直是规范权力的最大支柱。
5.社会的“监狱结构”确保对肉体的实际捕获与持续观察;由于本身性质的缘故,惩罚机构基本上能够适应新的权力经济,适应形成满足这种经济所需要的知识的手段。它的全景敞视运作使它能够起到这双重作用。由于它具备固定、划分与记录的方法,它一直是使人的行为客体化的无穷尽的检查活动得以发展的最简单、最原始、最具体但或许最必要的条件之一。如果说在“刑讯”司法时代之后我们进入了“检察”司法的时代,如果说检查方法能够以一种更一般的方式广布于整个社会并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关于人的科学,那么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各种繁多而相互重合的监禁机制。我并不认为人文科学源出于监狱。但是,如果说它们(人文科学)能够形成,能够在“知识型”(episteme)中造成如此之多的深刻变化,那是因为它们是通过一种特殊而新颖的权力渠道而传送的,即一种关于肉体的政策,一种使人的群体变得驯顺而有用的方法。这种政策要求把确定的知识关系包容进权力关系,要求有一种使征服与客体化重合的技术。它本身就带有新的造成个人化的技术。这种权力一知识造成了人文科学的历史可能性,而“监狱网络”则是这种权力一知识的盔甲之一。可认识的人(灵魂、个性、意识、行为等等)是这种分析介入、这种支配一观察的对象一效果。
6上述这些无疑可以解释监狱这个从一开始就受到诋毁的小发明为何极其牢固。如果它仅仅是一个为国家机器服务的镇压或排斥工具,那么它会比较容易地改变自己赤裸裸的形式,或寻找更容易被人接受的替代方式。但是,因为它植根于权力的机制与战略之中,所以它能以巨大的惯性力量来应付任何改造它的尝试。有一个事实很能说明问题:当改变监禁制度的问题被提出时,反对意见不仅出自司法机构本身。阻力不是出自作为刑事制裁的监狱,而是出自具有各种决断、联系与超司法结果的监狱,作为处于一个普遍的纪律与监视网络中的中转站的监狱,在一种全景敞视制度中运作的监狱。这并不意味着它是不可改变的,也不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