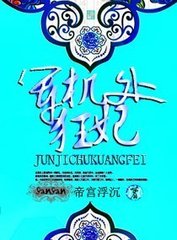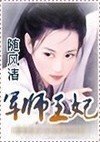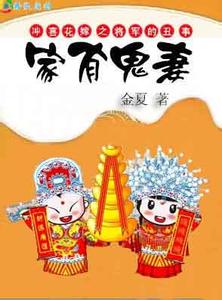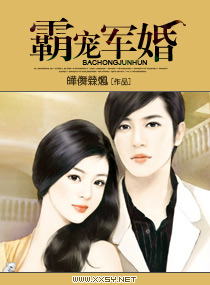青年近卫军-第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你是不会跳下来的,你就怕别人把你甩下!”刘勃卡说的时候没有提高嗓门,毫不生气。“一路平安,德拉普金同志!”她的小手从容而随便地挥动了一下,向那个气得脸色发紫的民警队长作别,他果然没有从已经开动的卡车上跳下来。
要不是她的蓝眼睛里流露出这种天真无邪的神情,要不是她的批评大部分都是有的放矢的话,旁人听到她的这种言论,看到她的这副打扮,再加上周围的人们都在逃跑而她却站在那里安然不动,一定会把她当做最狠毒的反革命,等待德国人到来而嘲笑苏维埃人的不幸。
“喂,那个戴帽子的!瞧你把多少东西叫老婆拿着,自己反而空着手!”她大喊着。“瞧,你老婆是多么瘦小。你头上还戴着帽子!……我瞧着你就别扭!……”
“老太太,你怎么在偷吃集体农庄的黄瓜?”她又对一辆大车上的一个老妇人喊着。“你以为苏维埃政权撤退了,你就可以胡来了吗?那么天上的上帝呢?你以为他看不见?他全都看得见!……”
没有人理会她的批评,她也不会看不到这一点。她好像是为个人消遣而在打抱不平。邬丽亚非常欣赏她那种沉着无畏的态度,她对这个姑娘立刻产生了信任,就跟她攀谈起来。
“刘巴,我是五一村的共青团员邬丽亚娜·葛洛莫娃。告诉我,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这很平常……”刘勃卡用发光的、大胆的蓝眼睛亲切地望了邬丽亚一眼,欣然回答说,“我们的军队放弃了伏罗希洛夫格勒,是今天一清早就放弃的。各个机关都接到命令立刻撤退……”
“那么共青团区委会呢?”邬丽亚声音沮丧地问。
“你这个秃子,干吗打人家小姑娘?哼,你这个小流氓!瞧我不出去揍你!”刘勃卡对人丛里的一个野孩子尖声叫道。
“共青团区委会吗?”她反问了一句。“共青团区委会照例是打先锋的,一清早就走了……你干吗朝我瞪着眼,姑娘?”她生气地对邬丽亚说。可是她瞅了邬丽亚一眼,懂得她的心理之后,立刻笑着说:“我是说着玩的,说着玩的……事情明摆着,它接到了命令,所以它走了,并不是逃跑的。你明白吗?”
“那么叫我们怎么办呢?”邬丽亚突然满腔怒火,气愤地问。
“你吗,自然也得离开。今天一早就发出了命令。你一早到哪儿去啦?”
“那么你呢?”邬丽亚直截了当地问。
“我吗?……”刘勃卡沉吟了一会,她的聪明的脸上突然露出事不关己的冷漠的神气。“我还要看看。”她回避地说。
“你难道不是团员?”邬丽亚钉着问道。她那双流露出坚强和愤怒的神色的乌黑的大眼睛,和刘勃卡的眯缝着的警觉的眼睛,刹那间遇到一起。
“我不是,”刘勃卡说,她微微把嘴一抿,就扭过身去。
“爸爸!”她叫了一声,开了门,高跟鞋咯登咯登地响着,跑去迎接朝这边走过来的一批人。这些人在人群中间显得很突出,人们都惊骇地、怀着突发的敬意给他们让路。
走在前面的是新一号井井长安德烈·瓦尔柯,他年纪约摸五十上下,身体结实,胡子刮得很干净,脸色像茨冈人那样阴沉黧黑,穿着上衣和靴子;另外一个是全城闻名的著名采煤工葛利高利·伊里奇·谢夫卓夫,他也在那个井里工作。他们后面还有几个矿工和两个军人。再后面,隔开一段路,是一群形形色色的看热闹的人:甚至在生活中最不平常、最艰难的时刻,还是有好多纯粹是好奇的人。
谢夫卓夫和另外几个矿工都穿着工作服,风帽推到脑后。他们的脸上、手上和衣服上全都是煤灰。他们里面有一个人的肩上挂着一卷沉重的电缆,另外一个背着一箱工具,谢夫卓夫手里却拿着一个奇怪的金属仪器,里面戳出几根短短的光电线。
他们一言不发地走着,他们的眼睛好像不敢望着人群里面的人,也不敢互相对视。汗水从他们的涂满煤灰的脸上流下来,留下一道道痕迹。他们的脸显得疲惫万分,好像他们是背负着力不胜任的重担。
邬丽亚突然明白了,为什么街上的人都怀着敬畏的心情预先给他们让路,——他们前面的一段街上都是空的。原来就是他们,亲手炸掉了新一号井,炸掉了顿涅茨矿区引以自豪的矿井。
刘勃卡跑到谢夫卓夫面前,用雪白的小手握住他的青筋突起的黑手,和他并排走着,他也立刻把她的手紧紧握住。
这时,由井长瓦尔柯和谢夫卓夫率领的矿工们都到了门前。他们如释重负地把带的东西——一卷电缆、工具箱和这个奇怪的金属仪器——隔着栅栏随便往里面一扔,就扔在庭园里的花上。事情很明白,先前那样精心培植的花草,也像有着这些花草和其他许多东西的那种生活一样,都已经完结了。
他们扔下这些东西,站了一会,彼此也不对视,仿佛感到有些尴尬。
“好吧,葛利高利·伊里奇,赶快收拾收拾,车子已经准备好了。我先去接别人,然后大伙一块来接你。”瓦尔柯说话的时候,他的眼睛也没有从他的像茨冈那样连在一起的阔眉毛下面抬起来望着谢夫卓夫。
接着,他就带着那几个矿工和军人,慢慢地沿着街走去。
谢夫卓夫仍旧拉着刘勃卡的手站在门前,旁边还有一个干瘦的长腿老矿工,他的被香烟熏黄的口髭和胡子好像被拔过似的,稀稀拉拉。邬丽亚也还站在旁边,她仿佛只有在这里才能解决那个使她苦恼的问题。他们谁也没有去注意她。
“刘波芙·葛利高利耶芙娜①,我又不是没有对你说过。”谢夫卓夫瞅了女儿一眼,生气地说,可是他还握着她的手——
①刘波芙·葛利高利耶芙娜是刘勃卡的本名和父名。父亲对女儿平常只叫名字,这里谢夫卓夫对刘勃卡有不满的意思。
“我已经说过,我不走。”刘勃卡绷着脸回答说。
“别胡闹啦,”谢夫卓夫显然很激动,但是声音仍旧很轻。“你怎么能不走?共青团员……”
刘勃卡的脸马上涨红了。她抬起眼睛望望邬丽亚,但是脸上立刻露出任性的、甚至是撒泼的神气。
“才做了几天的团员,”她说了就把嘴一抿,“我没有做过对不起别人的事。人家也不会来跟我找麻烦……我舍不得离开母亲。”她又低声加了一句。
“她脱团了!”邬丽亚突然惊骇地想道。可是她立刻想起了自己生病的母亲,心里就难受得好像火烧似的。
“啊,葛利高利·伊里奇,”老头说话的声音低沉得可怕,令人奇怪从这样干瘪的身体里怎么会发出这样的声音,“我们分手的时候到了……再见……”他对着低头站在他面前的谢夫卓夫望了一会。
谢夫卓夫默默脱下头上的便帽。他生着淡亚麻色的头发,蓝眼睛,一张俄罗斯中年工匠的瘦脸上满布深深的纵纹。他虽然已经并不年轻,穿着这件不合身的工作服,手上脸上又都是煤灰,但是依然可以感到,他的体格是结实而匀称的,并且具有俄罗斯的古典美。
“你要不要跟我们一块去碰碰运气?啊?康德拉多维奇?”
他问的时候没有望着老头,样子非常局促不安。
“我和我的老伴哪儿也去不成。还是等我们的孩子们随着红军回来解放我们吧。”
“你们家老大怎么样啦?”谢夫卓夫问。
“老大?还提他干吗?”老头阴郁地说,他摆了摆手,面部的表情仿佛要说:“我的丢脸的事你是知道的,何必再问?”他向谢夫卓夫伸出一只瘦骨嶙峋的干枯的手来,伤心地说:
“再见了,葛利高利·伊里奇。”
谢夫卓夫也伸出手来。但是,他们的话好像还没有说完,他们就握着手又站了一会。
“是啊……有什么办法呢……我的老伴,你瞧,还有我女儿,也不走。”谢夫卓夫缓慢地说。他的声音突然中断了。
“我们怎么能把它炸了,啊?康德拉多维奇?……把我们的美人儿……可以说是全国的奶娘……唉!……”他突然从心底发出一声异常轻微的长叹,像水晶般光彩夺目的泪珠,就落到他那被煤灰弄脏的脸上。
老头沙哑地呜咽着,低低地垂下头来。刘勃卡也放声大哭了。
邬丽亚咬着嘴唇,但是抑制不住那使她窒息的、无处泄恨的泪水,急急往五一村跑,往家里跑。
第03章
当郊区的一切都笼罩着这种撤退和匆促疏散的紧张气氛时,靠近城中心的地方,一切倒比较平静下来,似乎比较正常了。街上的职员的队伍和携儿带女的逃难的人们,都已经散去。各个机关的入口处或者院子里,都停着一排排的马车和卡车。有一批刚够办事的人手,在把装着机关财产的木箱和塞满文件的麻袋装到车上。他们在低声谈话,好像故意只谈他们所做的事。从敞开的门窗里传出锤子的敲击声,有时还有打字机的嗒嗒声。办事认真的事务主任们在做最后的财物清单:哪些需要运走,哪些可以不要。要不是远处隆隆的炮轰和震撼大地的爆炸,人们可能以为,这些机关只是从旧址迁往新居呢。
在城中心的高地上,屹立着一座新的、两侧展开的单层大厦,大厦正面遍植幼树。离开城市的人们,无论从哪里都可以看到这座建筑物。这里是区委会和区执行委员会,从去年秋天起,布尔什维克党伏罗希洛夫格勒州委会也在里面办公。
各机关和各企业的代表们不断地走进这座建筑物的大门,又几乎像奔跑似地出来。从敞开的窗口传出不停的电话铃声和对着话筒答复的、有时故意抑制、有时又过分大声的指示。有几辆民用的和军用的小汽车,排成半圆形停在总入口处旁边。最后面的是一辆满是尘土的军用吉普车。它后座上的两个穿着褪了色的军便服的军人——一个没有刮过脸的少校和一个魁梧的年轻中士——不时探出头来张望。在所有的司机们以及这两个军人的脸上和姿态中,都有一种难以觉察的共同的神情:他们在等待着。
这时,在大厦右侧一个大房间里展开的那个场面,以它内在的力量来讲,是足以使古代的大悲剧黯然失色的,如果它的外表不是这样平淡无奇的话。应当立即离开的州和区的领导人的是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用专政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在和要留下的领导人告别。这些留下的人现在要完成疏散工作,等德国人来了之后,他们就要销声匿迹,融化在群众中间,转入地下工作。
除了共同经历的患难之外,再没有别的什么能够使人们这样接近起来。
整个战争时期,从第一天到现在,对这些人说来,已经连成一个紧张得非人力所能忍受的、连续不断的劳动日,只有久经锻炼的、最坚强的性格才能经受得住这样的紧张。
他们把所有最年轻、最强壮的人献给前线。他们把可能遭到掠夺或破坏的最大的企业:几千台车床,几万个工人和几十万家属,运送到东方。但是像变魔术似的,他们马上又找到了新的车床和新的工人,使空阒的矿井和厂房又有了新的生命。
他们使工厂和所有的人们保持着一种时刻准备着的状态,以便一旦需要又可以行动起来,全部迁往东方。同时他们还不停地执行着这样一些职责,假如不这样做,苏维埃国家人民的生活就无法想象:他们供给人们吃,穿,教育儿童,治疗病人,培养出新的工程师、教师、农艺师,维持食堂、商店、戏院、俱乐部、体育馆、澡堂、洗衣房、理发店、民警队和消防队。
他们在全部战争的日子里始终如一地工作着。他们忘记了他们可能有个人的生活:他们的家属都在东方。他们吃、住、睡觉都不在家里,而是在机关和企业里,——不论日夜什么时候都可以在他们的岗位上找到他们。
顿巴斯的土地一片跟着一片地失陷,但是他们越发紧张地在剩下来的土地上工作。他们极度紧张地在顿巴斯最后一部分土地上工作,因为这是最后一部分了。但是直到最后,他们还使人们保持着这种巨大的干劲,来担负起战争压在人民肩上的一切。如果从别人身上已经挤不出精力,他们就一次又一次地从自己的精力和体力中挤。谁也说不出,他们的精力的限度究竟在哪里,因为它们是没有限度的。
最后,连顿巴斯的这一片土地也要放弃的时候来到了。这一次,在几天之中,他们又运走了几千台车床、几万人和几十万吨贵重物品。现在,到了最后一刻,连他们自己也都非走不可了。
他们站在克拉斯诺顿区党委书记的大办公室里,紧紧地挨在一起。长会议桌上的红毡已经拿掉。他们面对面站着,说笑着,互相拍着肩膀,总下不了决心说出告别的话。要离开的人们心头十分沉重、烦乱和痛苦,仿佛有乌鸦在抓他们的心。
州委干部伊凡·费奥多罗维奇·普罗庆柯,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