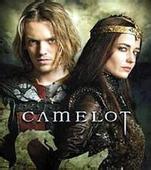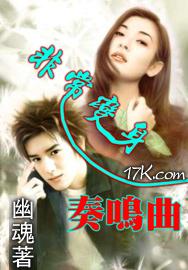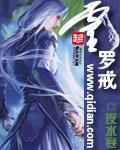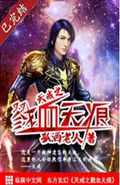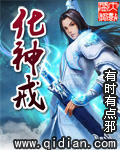非常媒·戒-第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马活,小鸭打鸣老母鸡被派去游泳。
比如说,节目做得好的人,完全有可能派出做行政,做经营。一个人能干,会被认为什么都能干,专业人才很轻易地被同等于通用人才。
实际情况怎么样?你在做节目的时候可能是博士后的水平,让你去做行政、搞经营,则完全可能是小学毕不了业的水平。如果用两条腿比喻湖南广电的节目制作水平和经营管理水平,前者健壮有力,后者小儿麻痹症。
那时,在湖南广电还流行一种文化,叫信文化,也就是跟领导写信,让领导了解自己,给自己提供机会。魏文彬曾在大会上承认,作为领导,他的接触面有限,要选才,也是先在他认识的里面选。为了改变这种情况,他要求大家抛掉那种书生气,主动跟领导交流、沟通。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魏文彬讲出了官场中那一部分想干事又颇有胸怀的人的心里话,有点求贤若渴的意思。如果由领导一个个去了解、去沟通,他也没那样的精力。你如果是个人才的话,你确实就要勇于推销自己,主动去和领导沟通,让领导来了解你。魏文彬的态度与做法,比那些任人唯亲、拉帮结派的人,已经有了段位上的差别。
据说魏文彬说了这个话之后,就有一批自认为是人才的人凑上去了,通过写信的方式谈自己的情况和想法,有些人还真的受到了重用。
这使领导选拔人才的渠道得以拓展,但其弊端同样十分明显,如果这种形式成为一种风气,伤害的可能是更多的人。比如说像苏建华这样的人,干了多少年的实际工作,对自己的优点和缺点还是很清楚的,他在有些方面永远也不会和别人去争,拿不下面子也好,觉得不是自己的长项也好,他就等着你来发现。但他自己心里有杆秤,在有的方面甚至会认死理。他觉得自己比某某强,如果因为某某写了一封信,就占了这个位置,那他会觉得完全不搭调,没有公平性可言。
另外一方面,苏建华对魏文彬的感觉又非常好。他承认自己一度因为对台里不满意而工作很不认真,一天到晚在那儿瞎混。谁愿意瞎混呢?起码是对自己不负责任吧。苏建华偶尔兴致来了也能把工作做得很漂亮,自己感觉还是很有爆发力的。那段时间正好是湖南台酝酿上星,很多节目都停下来了,都做上星的准备,正好碰上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苏建华他们就做奥运会的特别报道,他在那儿挑大梁,肩负着让奥运会特别报道充斥几乎整个时段的任务。苏建华对十几年前的一个情境记忆犹新,他在新闻部二楼碰到了魏文彬,魏文彬说:“小苏啊,你是不是最近到哪儿培训学习了一下?”苏建华说:“没有啊。”魏文彬说:“和以前不一样了啊。”魏文彬很亲切的几句话,让苏建华很感动,就觉得他很有魅力。
这也让我看到了苏建华性情和质朴的一面,我认定他是那种心地善良、易于被人感动、可以当朋友交往的人。我相信很多怀才不遇的朋友,都有过这种被领导感动的经历,他们是多么可爱、又多么容易被领导忽略的一类人呀。
这并不意味着苏建华看问题会一味的感性,相反,他会很理性地就事论事。他给我介绍说,在西方的企业里面也有这种意见箱,直接跟总经理或者老板沟通,这在任何一个公司都是鼓励的。但是绝对不是唯一的选择。基本上一封信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命运,这个就太不靠谱了。因为在选拔人或提拔人的过程中,是要用数据说话的,即便是在电视或者艺术创作很难量化的领域,都要想办法尽量量化。只有量化才能公正。也就是说,相对于那种任人唯亲、拉帮结派,信文化有一定的先进性,但作为一种企业制度来讲,应该还是要有更科学、更公平、更透明的程序,这样,对于后来的竞争者来说,才有一个明确的方向。
和苏建华的谈话使我不得不思考一些深层次的问题。
湖南广电不重视人才吗?
肯定不能这么说。
他们有一整套相对科学、易于操作的人才选拔机制吗?
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这么说。我宁愿这样想,正因为它太需要人才、太知道人才的重要性,在它的领导层产生了一种求贤若渴的无意识集体焦虑。
除了我们前面说的A类人才干B类或C类的活不匹配外,中国很多单位或企业的人才观,其实是有很浓厚的传统文化中人治或江湖义气的色彩的,可以把其看成是它们的一种变相延伸。
比如说,中国的单位或企业长期以来都是用能人来实施管理与控制的,不是不重视人才,而是太重视人才,组织的正常运行完全由人来完成,不像西方社会或世界级公司,更注重制度和流程管理。在中国企业,对人的依赖容易产生(如果不是必然产生的话)诸侯经济。这种掌控方式在短期内非常有效,大家团结在某一个人的周围,齐心协力,所向披靡,在量上获得扩张,与此同时却极容易忽略文化、制度建设,单位或集体的整体素质得不到质的提升,时间一长,企业家的个人野心与全体员工的共同追求很可能会严重脱节,必定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某个单位的头儿一旦跳槽,整个单位可能跟着死翘翘。
在我看来,湖南广电各频道、频道内的各栏目,已经具有诸侯经济的某些特征了,时间短了还可以,时间一长,或者说频道、栏目做大了,反而不行,因为资源共享问题将产生整体不经济。诸侯经济的另一个弊端是,对上可以叫板,内部会有不平,老板将不得不花更大的力气来安抚人心,在跷跷板上玩平衡,否则个别人就会另立门户;最后,员工的招聘、培训、提拔,习惯于因时因事的短期效果或服从于某一个具体任务,每个人没有明确的预期,不知道做什么会得到褒奖与惩罚,所以毫无职业精神,也形成不了归宿感。
在这个问题上,我还想跳出湖南广电走得更远。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个口号喊了多少年了?什么时候真正落到实处过?可能更多的是高高在上的领导的一种姿态,他打心眼儿里根本就没有想过要仰视你,连平视你都做不到,反而更像一种恩赐与施舍。什么时候,拥有知识的人才,不再为亲民的微笑、体恤的话语所感动,而是获得了一种制度保证,使他在经济利益上、话语权上、参政议政上有了与领导平起平坐的机会与可能性,那时,再来谈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吧。
我和苏建华都认为,应该鼓励员工和老板还有管理层直接对话、直接沟通。但是不要走偏了,特别是不要让其成为主要的或唯一的通道。中国很多行政事业单位,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太浓厚的人治色彩。魏文彬确实有他的个人魅力,有他的宏观视野,有他伟大的事业心甚至超强的影响力、号召力。但是,就像美国律法大师罗尔斯曾经说过的,建立在个人开明基础上的威权体制,如同“沙上之高楼”,一旦那个威权人物退位或影响力消退,它所具备的进步性便自然而然地消失了(转引自吴晓波《激荡三十年》)。
很多频道或栏目由盛至衰,频道之间的竞争与矛盾,其原因可能就在这里。
某种事情完全靠长官意志去判断,最后造成的后遗症是非常多的,是非常大的。还是那种中国传统的君主制的搞法。所以,你不能相信、依赖、寄希望于某个人,一定要用制度来规范其中所有的当事方。任何一个人,能力再强的一个人,你都不能完全相信他。
湖南广电每一次改革(或者说内乱?)都会有人出走,在为全国电视事业输送人才方面功不可没。但公正地说,撇开湖南广电在经历每一次的人才流失时更多的人的人心取向问题不谈,它的造血功能确实也得到了最充分的发挥,以致到现在为止,还能基本保持它的活力。
问题是,它本来可以做得更好。
而且,不是每个人都愿意飘来飘去的。
还是会有很多人,把安居乐业当成自己的人生目标与理想。
第三节 湖南广电与达·芬奇
对于正在寻求体制突破的湖南广电来说,我这本书的出版可能不是时候,可能会给它添乱,可能会被一些怀着鬼和天知道的动机想“黑”湖南广电、想“黑”湖南卫视的人拿去当枪使。如果真这样,我会很遗憾。我可以诅咒发誓,这不是我希望看到的。
作为湖南人,我太希望湖南广电健康发展了。即使在我使用一些来自于报刊、网络、在湖南广电看来可能属于“负面”的资讯的时候,也不是为了对它进行诋毁。知道它的毛病而不指出来,这种一团和气的“溺爱”,对湖南广电是没有任何好处的。它在正面报道自己的丰功伟绩时,也应该敞开胸怀,接纳来自于我等的善意挑剔与提醒。
一个讳病忌医的人,在对外保持健康体面的形象时,却让本来可以医治的小痛小病野蛮生长,最后害的只是自己,湖南广电不应该是这样的单位。
小痛小病怎么啦?放眼世界,谁他母亲的没病?
无需过多解释的是,王伟和他的团队成员在跟我倾心交流的过程中,从未对湖南广电抱有过诋毁之心,相反,他们让我觉得他们都是懂得感恩的人,至少不是恩怨不分的人。他们不止一次跟我谈到湖南广电带给他们的巨大的精神、经历方面的财富。
至于我自己,就更没有那种“犯上作乱”的动机了。我喜欢看湖南广电的电视节目。
我喜欢看汪涵、何炅、马可、大兵、李兵、李好主持的风格,当然,我对李湘、谢娜、张丹丹、王欢主持的风格也很喜欢。不过,我会更多地认为湖南广电男性节目主持人更有内涵与个人魅力,多少改变了中国社会“阴盛阳衰”的局面,那是一件很为湖南爷们儿长脸的事。尤其是汪涵,他的睿智与亲和,机灵与内敛,真是不可多得,完全有可能成为“国宝”级主持人。
这当然离不开湖南广电在电视节目上下的工夫和对电视节目主持人的培养。
除此之外,我对湖南广电应该还有小小的感恩,因为在《青瓷》热销湖南的过程中,它甚至还起过很好的促进作用(我跟湖南广电下属单位曾经有过两次合作,一次是“金鹰之声”把《青瓷》改编成广播剧;一次是潇湘电影频道联合湖南省话剧团把《青瓷》改编成话剧、并邀请众多本土电视节目主持人友请出演。我得说这是两次非常愉快的合作经历,他们的专业素养、敬业精神和团队合作精神,给我留下的印象相当深刻),我跟潇湘电影频道的傅湘宁、杨蔚然和黄进,至今仍算私交不浅的朋友。
我知道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需要辩证地对待,为了表明我对湖南广电丝毫没有故意伤害的动机,我特意收集了一些可以给它加分的素材,它同样是构成湖南广电气场的一些重要元素。再说了,“电视湘军”的名头已经叫响,这是谁也否认不了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1993年以来,湖南广电已历经三轮改革,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电视湘军”这一品牌的形成,其实是与我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一脉相承的,只不过,湖南电视人幸运地成了时代的弄潮儿。
有文章为证。
发表于2008年12月《中国记者》杂志、署名湖南卫视的一篇名为“‘电视湘军’的改革发展之路”的文章简单回顾了上述三轮改革,这对我们以后讲的故事提供了一个可感可触的时代背景,故摘要如下:
“1970年9月,湖南电视台诞生。1991年1月15日,湖南有线电视台试播,湖南有了第二家省级台,打破了一台独大的局面。同年11月18日,湖南电视台二台开播。1993年10月18日,湖南广播电视信息台开始试播。而真正打破湖南电视的平静始于湖南经济电视台的建立。
“1996年1月1日,湖南经济电视台正式开播。湖南广电第一轮改革从此风起云涌。湖南经视率先在电视荧屏上掀起栏目包装和频道整体形象设计热潮,并在新闻、综艺、电视剧三大主战场向传统电视理念发起进攻。
“‘经视’咄咄逼人的态势使湖南电视台感到危机。1997年1月1日,湖南电视台上星,在全国电视界率先实施品牌战略和周末战略。湖南卫视推行栏目制片人制和栏目末位淘汰制,并着手对节目进行重新策划和包装改版,同年7月推出了娱乐节目‘快乐大本营’,并把它放在与‘幸运1997’(改版后的‘幸运3721’)同样的时段播出。这两档娱乐节目互相竞争,在全国刮起了一阵‘快乐旋风’。1998年,‘玫瑰之约’新鲜出炉,‘晚间新闻’全新改版,在全国开了讲新闻的先河。紧接着,‘新青年’、‘聚艺堂’、‘音乐不断歌友会’等栏目相继诞生。这一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