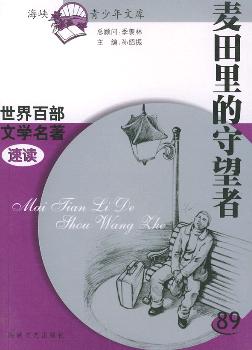守望-第3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想过死的,大衣里的碎碗片,我曾想过用它结束我的生命,可每次当我有这个想法的时候,我都不甘心,为不知道他是否还活着,现在过得好不好而忧心。
我不想见到他,只想知道他是否还安好。
王森开始不再要求我说话,他看着我的眼神从最初的愤怒开始变成了悲伤,他总是悲伤的看着我,一次次掐灭手中的烟,又一次次点燃新的一根。
我坐在床边,看着萧瑟的窗外出了神,不知道什么时候,他走进屋来,将我的身份证、护照,和一张飞上海的机票扔在我继续写作的桌上,脸上是散不开的悲伤和绝望,他说,“夏轻浅,一年零九个月了,你依然像木头一样,我爱你,可我知道,不管我关你多久,你也不会爱上我,这一生不会,下一生也不会。”
他继续点燃手中的烟,烟雾升起,他的脸显得苍老了不少,“你走吧,要死也回去死,回到你心心念念的地方,不要死在这个城市”
他何尝不是一个可怜虫,在爱里没有人同情他,所以他只能这样极端的爱着,爱到毁灭,可他情愿毁掉的是他自己。
护士小姐将我的行李打包好装在一个密码箱里,她将密码箱拖到我面前,满脸悲伤,看着我要走她不知是高兴还是难过,她会伤心,但还是高兴的,毕竟在她看来我终于逃脱了我所谓的牢笼,飞向我梦寐以求的远方了。
而我什么也没有带走,这个房间里的东西,我什么也不想要,除了那个厚厚的笔记本,里面装着一个我不忍去触碰的未完待续的故事。
我坐在飞机上像刚刚从监狱里放出的囚犯,面容憔悴,两眼无神,麻木地睁着两只空洞的眼睛,看着面前经过的一行人,两年的时间,我从上海人间蒸发了,然后到了另一个半球,另一个国家,开始过上了囚犯的生活。
我是这样定义的,没错,那就是囚犯一般的生活,没有自由,没有你的消息,曾想过那样的日子不如死去,但我却固执地坚持着活着,就为了知道你是否还安好。
可物是人非,你应该早就离开上海了吧。
我忘记了怎么说话,我忘记了怎么微笑,我甚至开始害怕见到上海的太阳。
我开始坐在客机里哭,哭得西斯底里,哭声震惊了整个客舱,不时有人探出头来看我。但他们只是看看,有的皱皱眉,有的开始交头接耳,可能几分钟后,就不会有人在意这个陌生的女人为什么会不顾形象地哭泣。所以,有句话说对了,这个世界上没有所谓的感同身受,有的只是冷暖自知,自己的悲伤只有自己懂,自己的绝望,也只有自己明白。
我捂住脸,头发披撒在肩头,眼泪从指间溢出。
经过长久的国际航班,我终于站在了上海国际机场,海风吹过带着熟悉的味道,只是这股熟悉里已经没有了当初的那份美好,我的生活,不知道从哪一刻起开始变得有些支离破碎,开始变得即使我想挽救也挽救不了了。
我站在机场里,竟然不知道该往哪里走,家?没有了吧,朋友?还在这个城市吗?上海啊,我情愿你下雨下雪,也千万不要出太阳。
电话号码吗?我谁的也记不得了,只有那个如它主人的名字一般刻在我心底的号码还在脑海中记忆犹新,可是,不管你在不在这座城市,亦望,我都不想见你。
“小姐?小姐?,请问你要到哪?出租车坐吗?”
我摇摇头,又点点头,然后又摇摇头。
司机师傅很奇怪的看着我,“你在等朋友来接你吗?”
“我不知道……我的朋友是不是都还在这所城市”,我说。是啊?两年了,他们还会在上海吗?如果在,那么还会在原来的地方吗?我不知道,过了一段与世隔绝的地狱般的日子的我,他们还会记得吗?
“那他们以前住哪里?我可以送你过去,或者,你给他们打个电话”
我看着出租车司机,他也很奇怪的看着我。
我拿着师傅递在我手中的手机,却不知道舒扬和余逸的号码。
我不确定舒扬还住不住那里,突然觉得很可悲,原来我是一个这么寡情的人,这么多年过去了,我除了那个人,和那串与他相关的阿拉伯数字,其他的什么也不记得了。
师傅人很好,在上海这么一个繁忙的城市,难得有人那么有耐心的在这里等你慢慢的回忆。
我向司机报了个地址后便上了车,没有行李,所以我走得很轻松。
师傅关上车门后,有些担心地回头看了我一眼,随即转过头去安静的开着车。
“是这里吗?”,师傅突然将车停在一个小区门口,然后转过头来看还在出神的我。
我这才从神游的思绪中缓过来,这是舒扬以前住的地方,但我不确定,过了这么久,她有没有换地方,她和刘峰怎么样了,现在结婚了吗?我不知道,呵,我怎么可能会知道,连亦望我都不知道,舒扬,我又怎么可能会知道。
如果问我恨吗?我想我是恨的,如果可以选择,我情愿在那场车祸中死去,也不愿意这样苟且地活着,一点也不愿意。
“是的,师傅谢谢你”,我付了钱,缓缓开车下来,木讷地站在这里,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要做什么?
出租车离去以后,我又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该做什么?直接走去敲门吗?那万一住在里面的人不是怎么办?
保安室里的大叔将头伸出来看了好几次,坐在他身边的流浪狗也不时的朝我所站立的地方懒懒的看两眼。仿佛我是一个突然出现在这里的外来物,也是,我确实就是一个外来物,在大多数人眼里,我应该早就死了吧。想到这里的时候我不禁开始难过起来,但转念一想,对亦望来说,或者我已经死了会更好。死去的东西,如果在死去那一刻之前是纯洁的,那么她将永远纯洁,可我,显然已经不是了,所以,如果真的能给我一次选择的权利,我情愿死去。
保安室里的大叔见我就这样站在这里足足犹豫了将近半个小时,便走过来问我,“请问姑娘,你找人吗?还是?”
我收了收视线,看了一眼三楼那间窗户死死关住的房间,朝大叔点点头。
“那他是住这里吗?”,大叔见我迟迟不动,想也是我不确定所要找的人是不是住这里。
我点点头,又摇摇头,一如刚刚在机场时的恍惚和迷茫,大叔更加疑惑的看着我,但他并没有多说什么,只是问我,“那你给他打个电话吧,我们这个小区每天都有人搬进搬出的,你的朋友……”,大叔说到这里便没有继续下去,其实我知道他的言下之意,我心里也不是没有想过,可除了舒扬,这座城市,我还能去见谁?余逸吗?不要,我害怕在他面前哭起来,我不要他再抓着我的一个把柄,可笑,这只不过是我逃避熟人的一个借口罢了。
现在的我连面向阳光站立的勇气都没有……
我默默地转身打算离开,想是我的背影实在有些太过孤寂了,所以连大叔都有些不忍,他叫住我,“你还记得他住的房间号吗?或许我可以打电话帮你问问。”
我脚一顿,随即转身,房间号。“3013”我说。
如果不是此刻真的无家可归,我想我是不愿意见到他们的,熟人?在时光里已经变了模样,或者说,消失这么长时间的我已经变得面目全非,我怕他们认不得我,也害怕他们轻易认出我。
我远了大叔几步,背过身去,站在低垂的杨柳枝下,看着河里流动的河水长时间地发呆。
如果说刚刚是害怕人走茶凉的冷清,现在就是害怕物是人非的悲凉,明明很脆弱,很害怕见到熟悉的人,却忍不住想要遇见。
因为一个人实在太孤单了。
“要死也回上海去死”,这是那个人在苏黎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可我却没再对他说过一句话,已经没有必要了,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了。
“轻浅?”一声熟悉的声音带着颤裂在我身后响起,声音里带着几丝不确定和急切,我没有立即回头,因为害怕,声音的主人带着哭腔,我怕她哭,也怕我哭。
声音的主人开始越来越近,身体还在颤抖,可那颗悬着的心却突然安静了下来。
我转身看见了泪流满面的舒扬,她走过来一把拥住我,“死丫头,这两年死哪儿去了?知不知道我们都快担心死你了……我是真的以为你死了,所以,你知道刚刚大叔打电话叫我下来的时候我有多害怕吗?我多怕这只是自己在做梦,等梦醒了,连消息都是假的”
我就这样任舒扬抱着,声音已经沙哑到说不出一句话来,我该说什么好呢?说不要担心我这不好好的吗?可我真的好吗?我是好好的吗?不,一点都不好,我难受,我心里真的很难受,身体在摇摇欲坠,如果不是舒扬狠狠地搂着,或许我早已倒下去了。
那些过往的经历,几百多个失眠的日日夜夜,我过得一点都不好。
原以为在飞机上流干眼泪后,我不会再哭了的,但原来,眼泪是那么不值钱的东西,想流多少都流得出来,就算强忍着,有时候,也徒劳无功。
“舒扬……”我只是叫了一声她的名字,就已经泣不成声了。
大叔见我们哭成一团,转身走进了保安室,那只流浪狗也跟了进去。
“舒扬我累了,我们上去吧”,我伏在她肩上,对她说,她朝我猛点头,然后我们一起进了小区,上了三楼,3013,原来,舒扬还住这里,那么他们呢?
一阵阵的悲凉席卷全身,我不知道,我还能坚持多久,是不是知道了他们都还好,就无憾了,在苏黎世的时候,即使我不完全听得懂苏黎世医生的话,但多多少听得懂一些,他们都说,这种体质,西医没有办法,过多的医治只会产生不良反应,用中医的方式或许会有效,于是,王森请来了一个中医,但是他除了开药方,也只是摇摇头。说,病由心生,心情舒畅,一切自然好了,但是,谁能告诉我,心情舒畅,我要怎样才能心情舒畅,一年多的时间,隔绝了家人,隔绝了朋友,他们甚至都以为我死了。请问,每天带着绝望等死的人,要怎样才能心情舒畅。
晚上,吃过一点点饭后,我便站在窗边,看着上海在秋的色调里,依然一片生机盎然,这就是我一直向往的上海,这就是张爱玲笔下,历经沧桑变幻后的上海,也是我第一次遇见你的上海。
为什么我总是想起你,就这么无缘无故的想起。
刚刚舒扬问我这段时间的经历的时候,我只是一笔带过,我撒了一个慌,一个小说里经常出现的谎言。我告诉她是一对没有子女的夫妇救了我,然后转院到了国外,那段时间我昏迷了三个月,能醒过来已是奇迹,一时之间忘了联系以前的朋友。
我清楚地知道,自己说的这一通话中,除了那昏迷的那几个月是真的,没有哪一句是真的,什么夫妇,什么转院到国外不过是我为了隐藏往事杜撰出来的假象而已。似乎对我来说,过去的这一段时间,除了昏迷的那三个月是有意义的,其他的就全部是噩梦,没有知觉地躺在那里,不知就不会痛。
舒扬虽然没有再说什么,但是显然,她是没有信的,一年多,不是几天也不是几十天,而是几百天,就算在治疗,怎会弄得连行李都不没有,我看见她偷偷地抹眼泪,但也只是看看,我不想告诉任何人那段不堪的日子,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那种等死的感觉。
在苏黎世,看着天上飘落下来的落叶,我都能够想到死亡。
每一片叶子的离开都滋生了我想死的念头。
“现在是秋天了,披件衣服吧”,舒扬从客厅进来,将一件大衣披在我身上,我缓缓地转身,眉毛抬了抬,看着她手中的纸条,上面写着一串号码,有几分熟悉,但是以前的自己从来没有背电话号码的习惯,所以,也想不起来,她手中的号码是谁的。
“你弟的”,舒扬将纸条递到我手中,然后并肩与我站着,她缓缓说道,“你弟弟今年考上了复旦大学,法学专业,他真的很棒,就像你曾经说的那样,只是,他跟你描述中的有些不同,我不知道他是通过什么方式找到我的,他只是安静地来问我你的下落,然后落寞地离开……这很不像一个十八岁的少年”说到这里舒扬突然停了下来,看着单一色的树木,好一会儿后,她才继续说,“轻浅,有时候,你们真的很像,即使我知道你们并没有所谓的血缘关系”
听到小澄,我心开始狠狠地抽了一下,要是他知道,他的姐姐现在变成了这番模样,他会怎样想,记得刚来上海的时候,他打一个长途电话来,就是为了告诉我,他也想来上海。“舒扬,”我犹豫了一下,但还是说了,“能不能先不要告诉小澄,我回来了”。我为难地看着她,舒扬显然有些